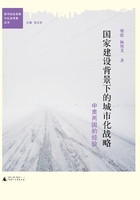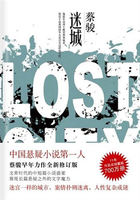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9号哨位]
又是电话。电话铃一响,倪欢欢就望向阵地长侯春茂。按阵地长的分配,他的铺位和阵地长头对头。侯春茂刚从电话上了解清楚,他所管的各哨位已经安置停妥,这一速度令人满意。他把刚放下的耳机又拿了起来,以为是哪个哨长要汇报情况。
“红蝙蝠吗?”连长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
“是的。”侯春茂说,“我是红蝙蝠。”
“我是苍鹰。”连长说。
“你是‘苍蝇’。你还没报名字,我就听出来了。”
“这么说,昆虫专家,世界上真有一种红色的蝙蝠?”
“我现在的专业是打仗,不谈昆虫学。”侯春茂说。三个兵都假装没有听到他在打电话。倪欢欢坐在汪嘉梧的铺上,他的眼睛深处动着两朵蜡烛花,好像战争的精灵跑进了他的眼睛里。汪嘉梧斜视着阵地长。他是从来不对阵地长正眼瞧的,到了这里还如此。想想真可怕,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当然你得首先保证能活满八个月--都要在他的睨视中度过。坐在那一边的马中济哨长张着眼睛的同时也张着嘴。凡是阵地长所在的哨位上,其哨长也都在今天才上阵地。他东望西瞅的,好像在琢磨那些大石头。石洞的穹顶和四壁都是垒垒怪石。侯春茂不了解这三个兵。那个守在洞口的神枪手关存道,侯春茂也不了解。今天,正好是他和他们相识满三个月的日子。三个月前,他在步兵学校。
“……我们这里快成动物世界了。”连长说。
“这是你的倡议啊。”侯春茂说,“好像其他连队都没有用代号。是好是坏都是你带的头。把这块阵地争过来的,是你。让所有的阵地长和哨长都用动物作代号的,也是你。”与此同时,侯春茂想着,他第一天上阵地时,也像马中济一样,曾琢磨过这些狰狞得让人恐慌的石头。
“哈哈。”连长笑了,“你自己取代号‘红蝙蝠’,有什么意思吗?”
“你曾经说我心理阴暗,我想就用蝠蝙作代号吧。前面用 ‘红’作定语,那你就满意了。”
“是这样吗?我还没想到。”
“你承认自己是笨伯了?”侯春茂说。一颗石子从洞颈那儿掉下,“对不起,你等一下。”侯春茂把耳机放在铺上。
“喂喂。”连长说,“喂,红蝙蝠!”
侯春茂向洞颈跑去。他同关存道约好,如果有什么情况,就朝洞颈摔一颗石子下来。“小关!”侯春茂扶着洞颈底部叫。他不想爬出去。爬出去还好办,缩进来就难了。要缩进来的话,必须两只脚在前,中间拐一个弯,转一个身。这个山洞有点特别,近洞口处的一段高突,中间拐弯,刚好能挤进去一个人体,如果叫作阴道更加确切一点儿。对,能不爬出去就不要爬出去。个子大一点儿的,如汪嘉梧,弄不好就卡在洞颈里,成为一个洞塞子。“关存道!”他说。
“没事。”关存道说。也许是他翻身的时候蹬下来一颗石子。
等他回头,发现那三个兵都拿好了枪,一齐望着他。假如真有情况,等我们爬出去,敌军早把洞口占领,接着就可以瓮中捉鳖。“没事。”侯春茂说,“当心点,枪不要走火了。”见鬼吧?在这洞子里捉迷藏还差不多,可这还是阵地长的指挥所。
“想起来了。”侯春茂走向自己的床铺边,从枕头下翻出一包烟,慢慢地撕开封口。听话器连续不断地叫着:“喂,喂,红蝙蝠!喂,二排长!喂,侯春茂,阵地长!……”让连长在那边干吼吧。这是今夜的第四个电话了,已可称之为骚扰电话。全连刚入阵地的第一个晚上,连长非常负责地骚扰他的部下。不会有什么指示、什么命令。让连长在那边等着。侯春茂抽出三支烟。“看来我不大可能是一个合格的阵地长。到现在我才发现,汪嘉梧和马哨长进洞以来还没抽过烟。”他首先把烟递给汪嘉梧,“汪大个,我是不抽烟的,你知道。可是,你这老烟鬼怎么也忘了抽烟?”
汪嘉梧有点害羞似的接下烟。“阵地上不禁烟吗?”
“嗯,回答得非常机智。”侯春茂说。他瞥见,马中济和倪欢欢都望着汪嘉梧,进洞后第一次露出一点自然的笑容。汪嘉梧则颇为自嘲似的微笑着,把烟叼在嘴上。终于松弛下来了。让连长在那边多等一会儿,好得很!“欢欢,你一定不抽这支烟,那只好放在汪嘉梧的‘床头柜’上了。我们的阵地就这个样儿。因为我这阵地长的代号是‘红蝙蝠’,你们可以称这个哨位为‘蝙蝠洞’。”侯春茂重新拿起耳机,“喂,苍蝇,苍蝇,还在听吗?”
“嗨,红蝙蝠老弟,咱们玩笑归玩笑,正经是正经。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知道我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既然上了阵地,有些想法恐怕最好还是藏在口袋里好。再说得难听点,即使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
“领教了。”侯春茂说。
“但愿不要我送你进烈士陵园。”
“我很佩服你的自信。中国有个成语,叫作‘一语成谶’,你就断定我一定死在你前面?”
“那就请你送我好了。”
“一言为定。你到底有什么指示?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啰唆了。”
“夜这么长,就算聊天,不也很好吗?战场电话不付费,你怕什么?唉,你能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你对你负责的阵地上的一切都掌握了?”
“什么也没有掌握。”侯春茂说。
“真的假的?”
“假不了!我可以向你汇报,当那些老大哥在这里的时候,我没有执行你的指示。我没有送好烟,没有送水果糖,也没有送别的。发给我的罐头,我吃了。军工们辛辛苦苦背上阵地的罐头,不再由老大哥们背下去,能使他们下山的时候轻松一点儿。”
“呵。既然你的哨长们都把关系理顺了,也一样。我不是要你个人破费钱财,我是想,能请他们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我们,送几条烟什么的,也算不了啥。多送一条烟,少丢一条命,这很划算。”
“你真的这样关心战士们的生与死?”
“什么意思?”
“下战场的时候再问我吧!”
“怎么,走掉的那个阵地长什么也没有对你说?”
“不是向你报告过了吗?该讲的,他们都讲了。比如,往这个洞里钻进来,别忘了脚在前头。”
“……刚才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有啊!有人一晚上给我打了四个电话。”
“我怕大家睡着。”
“请连座当心操劳过度,这才刚开始。”侯春茂捂住授话器,在三个兵身上望了一遍。“你们睡吧。没有什么敌情。没听到我同连长瞎吹牛皮呢。睡吧睡吧。马哨长,你带个头,好好睡。”看着三个兵各自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他继续打电话,“连长,别糟塌你的唾液了好不好?几个兵都很累!”
“好。再说句多余的话,要同你的兵搞好关系呵,尤其是你所在哨位上的兵。”
“谢谢你提醒……苍蝇,你得通知军工先给我们背一点卫生纸上来。你知道,舌头舔不着屁眼。还有水。水没有了。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水做饭。”
“忍一忍,怎么样?先给他们吃点压缩饼干。”
“你以为还有?全让‘老鼠’背走了。”
“混账!”
“请你说话文明点。”
“我不是骂你。交防之前,双方说好的……刚才真没有什么情况?”
“有的。有人被苍蝇咬伤了,已经妥善处理。”
侯春茂放下耳机,动作又轻又慢。读了四年大学,专攻昆虫学。昆虫学,太冷门了。研究单位不要,就找不到工作。他想到投笔从戎。在步兵学校培训一年,分配到作战部队。人人都叫他“学生官”。“学生官”,多么矛盾的名字,又是学生又是官。要他同他的兵搞好关系,这话说得……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还真的被苍蝇咬了一口。现在,三个兵都在地铺上假寐。他们还没有睡着,也不可能这样就睡着。在这样相对宽敞的石洞里,能睡在地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很多兵睡在烂泥洞里,尽管那烂泥洞里挖出的“床铺”看起来像是火车的卧铺车箱。他是阵地长,理所当然地分配到了这样的幸运。可他不知道,那三个和他同一哨位的兵要过多少天才能体认到这一份幸运。
昆虫学在战场上能不能用上?就在这个黄昏,交防前的那一刻,即将下山的阵地长提醒他,你不要感到奇怪,这战场上照样有蟑螂,有苍蝇。一丝凉风从洞口灌了进来,那种黑暗而潮润的凉风,并不特别凉,感觉上却砭人肌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