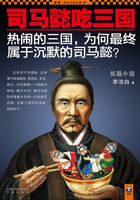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15号哨位]
刚安顿下来的时候听到了枪响。枪声沉闷,经过风的吹拂和雨的摩擦,来到他们的洞口。它在石洞四壁的岩棱上撞得额头出血,眼冒金星,好歹清醒过来,找着一条向地底倾斜的通道,磕磕绊绊地朝下滚动,又被两旁的石尖石角磨损了很多,变得像久卧病榻的一声轻咳,然而它在洞穴底部引起严厉的回响,终于以它不可抗拒的渗透性进入他们的毛细血管。
“是冷枪。”米开广说。
顾家荣还在摊开的背包中找什么,只是身体僵了一小会儿。任宠和蓝文定的眼睛在向米开广询问着什么。任宠另有动作,他扳着一只脚,将脚底朝向蜡烛。蜡烛放在铺边的弹药箱上,烛光把他的脚底照得很清晰,而他的半张脸孔隐在黑暗中,那表情也像脚底似的。米开广把重机枪摆好,使它处在随时可以射击的状态。他发现,那两个兵仍然望着他。
“在这阵地上,冷枪冷炮很多。听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米开广又说。
顾家荣把摊开的棉被揭了起来。洞外响着雨声,沙沙的,好像群蚕吃桑叶。任宠把头伸到蓝文定耳边。蓝文定的脸孔向他扭过去。
“别逗了。”任宠说。
“什么?”米开广问。
“没什么。”蓝文定说。
任宠的那半张被烛光照亮的脸红了红,朝脚底倾下头去。可能他脚上起了血泡,当时没有感觉,现在感觉到疼痛,又不好意思说。
顾家荣跪在铺边上寻思着、回忆着。
“后来,他的副班长硬是抓着他的后衣领把他从烂泥中提了起来。”蓝文定一脸诡秘地说着。
“是吗?”米开广问,“小缪不至于这么窝囊吧?城市兵不像我们这些农村兵,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点小洋相,情有可原吧。”
“问题是四班副。尤清园在那一时间里一定是精神失常,骂了很多难听话。我想你这小子怎么了,要是跑得动,谁他妈的不想一脚跨上山?喂,班长,不,哨长,尤清园这次为什么没有当上哨长,你应当知道一点隐情吧?”
“这关你屁事啊?”米开广说。从现在起,他是名正言顺地班长级别的哨长了。不过,刚才的枪声有点怪怪的,会不会是刚上阵地的兵“枪走火”?从现在起,他居然当起哨长来了。这哨长应该怎么当?上阵地前,他连军队最低级别的副班长也没有当过。像尤清园,当了近两年副班长,老兵油条一个,被从哨长的人选中摒除出去了。连长说:“米开广的心理素质不错。”连长有没有看走眼啊?他米开广所知道的是,为了确定几十个哨位的哨长,连首长连续研究了三天,再报营首长审查批准。要说严肃认真,够他妈的分儿。
米开广相信,蓝文定一上阵地就传播那种小道消息,含有一点和他套近乎的味道。然而,米开广自信,上战场前夕即使把他提升为排长,也不能说明特别器重他。现在,他不过是管三个兵,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们的脚上真的没有起泡吗?”任宠问。
“没有你娇嫩。”蓝文定说,“那龟孙子,是不能当哨长的。”
“别说了。”米开广说。他知道蓝文定的心思。蓝文定的话里还有一种含沙射影的意味,通过抨击尤清园来警告他米开广:在这阵地上,不要像尤清园那样当一个不是好东西的哨长。应当制止蓝文定继续渲染。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个怎么把背包掷掉了,一个又怎么骂。”蓝文定说。他向自己的铺位走去,从黑暗里拿起一盒烟,一边从烟盒抽烟卷一边走回来。他敞着怀,袖子卷得高高的,走到米开广胸前。“我还没问你呢,这个星期在阵地上过得怎么样?”
“还行。”米开广说,接下他的烟,在蓝文定的打火机上吸燃。那打火机金黄锃亮,是镀了黄金的。米开广真想有这样一只打火机。“你坐吧。我给你们倒点开水喝。”米开广说。为什么金子一定是黄色的,难道没有白金、黑金、红金、紫金、彩金吗?
“有水啊?怎么不早说。”
“我忘了。”米开广说。蓝文定去挎包里拿碗,嘴里囔囔着。米开广向洞口摸去,摸着压缩饼干箱。它搁在煤油炉子上,已经凉冰冰的。“你们等一会儿。”他说,“我把水热一下。”
“不要热了。”蓝文定说,“只要是水就行。嗓子里都着火了。我怕不合时宜,才没说出来。”他和任宠一前一后摸过来。任宠的脚已不疼了。
米开广捧起饼干箱。“水不多,一人只能喝半碗。”
“行啊行啊。”蓝文定把碗伸过来,“就用这饼干箱烧水?呵,对,这当然不是在高级宾馆里。”
米开广小心地把水倒进他的碗里去。
顾家荣还在那里摸索。他显然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他心里似乎也不知道到底要寻找什么,或者,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忘掉。该带上阵地的东西,连里在十几天前就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俩开始喝水的时候,顾家荣不再寻觅。好像还在军营里,顾家荣把床单抹得很平,认认真真,但慢慢腾腾。他此刻正在记忆的深水里探摸,就像摸鱼似的,他的动作也和摸鱼没有什么两样。“顾大哥,你在找什么?”蓝文定问。
“我忘了一样东西。”顾家荣说。顾家荣胖胖的,矮墩墩的。顾家荣到前线以后,不愿与人多说话。米开广是不想要顾家荣在他哨位上的,可连长说:“顾家荣就放在你的哨位了。”哪个哨长带哪几个兵,连首长们也是煞费苦心。连里“有”那么几个兵,哪个哨长都不想要。怎么办,把他们遣送回家?第一,部队不允许,没有这样的先例。第二,这会损伤他们的自尊,伤害他们一辈子。指导员说了,你米开广虽然没有当过副班长,但连里对你评价不错。就把顾家荣放在你的哨位上了,怎么样?米开广不能不接受。
米开广把水倒在碗里,给顾家荣送过去。“你忘掉什么了?”他说。
顾家荣没吭气,接下水碗。他肯定没有忘了带东西。假如有什么遗忘,最可能的是人,也就是他本人。你想想,所有的私人物品都不能带上山,他还能忘掉什么?饭碗可以算私物,他带了,还没有从挎包里取出来。再有什么私物,就是写信的钢笔了,可这是允许带上阵地的。
“你说啊,你忘了什么?”
“这与你无关,哨长。”
“我把照相机带上来了!”蓝文定说。
“就是那台傻瓜照相机?”
“没错。”蓝文定说,“我们在哨位上拍一些照片。假如能活着回去,也可以向人吹吹牛,证明我们是上过战场的。”
“你想得太远了吧?”米开广说。
传来一梭子枪声。他们都朝洞口望。听不清有几发子弹。
“又是冷枪?”蓝文定问。
任宠一阵哆嗦。他哆嗦时把碗捧得很紧。
“是的。”米开广说。可是,他怎么能判断出那是敌方的冷枪,还是我方新上阵者的枪走火;是敌人的试探性射击,还是偷袭?在他见习的一星期里,敌军爬到我方阵地袭扰三次,有一次还在这个洞口外边待了一个多小时。今晚有没有偷袭,天晓得。从迹象看,敌军完全知悉我方部队在这几天调防。
以后的日子还不好过呢。
面临死亡,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比如说,抓阄!趁着刚上阵地,做四个纸团,其中一个写“死”字,另外三个写“活”字。谁抓到了“死”,不用怪别人,只怪自己手运不好。以后遇着死的危险,让这握着“死”的兵先上。死了一个,活着的三个再抓阄。要不你怎么说得通,当了哨长要先死。米开广还真有一点烦恼了。早不让他当班长,晚不让他当班长,偏在上阵地之前给他一个“相当于班长”的职务。这下好,给他一个死亡优先权。反正好事轮不到你头上。你要不愿当哨长,那些臭嘴巴就会说你胆小,怕死,没有英雄主义气概,好像真有谁喜欢抢着去死一样……
蓝文定坐到米开广身边,又递上来一支烟。“你好像没烟了是不是?你不是带上来三条好烟吗?”
“理顺关系了。”米开广说。
顾家荣扭过头来望,突然捂住嘴,打了一个假喷嚏。“感冒了。”任宠说。在他头后一米多高处的小石洞里,一条小手臂粗的乌梢蛇已垂下来一尺多长,那对小眼睛像磷火似的闪着光,不过它正在慢慢往洞内缩回去。这时又传来一阵沉闷的、阴郁的、铁黑的枪声。
“‘理顺关系’?”
“休息吧,蓝文定。”米开广说,“我能当哨长,你只能在我手下当哨员,差别就在这里!快点睡觉吧。在今晚这样的恶劣天气上阵地,你还不累吗?”
“你呢?”蓝文定说。
“我值班,守洞。”米开广说,走开了。
“晚上都是你,那怎么行?”
“明天安排你们,”米开广说,“呵,你们三个听好了。现在每个哨位有一部电话。”他解释,连部的电话总机是只有二十门的小总机,但哨位多得多,所以他们的哨位是串联电话。听到电话铃响,可以把耳机拿起来,但要听清了。如果叫“猴子”,那是叫他。他的代号是“猴子”,他们阵地长也就是二排长的代号是“红蝙蝠”,连长是“苍鹰”……“其他哨长和阵地长的代号,今天不说了,说多了记不住。都明白了?”
“明白。”顾家荣和任宠说。
“我不太明白。”蓝文定说。
“这就随便你了。”
石洞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张着杌陧不安的眼睛。那条蛇缩进去,只剩下一个头了,蛇眼如同狡狯的萤火。如果你告诉任宠,说他铺位上方的石壁里至少有六个蛇洞,住着六条蛇,其中两条分别是极毒的银环蛇和眼镜蛇,那这个见了草绳也会抖三抖的新兵娃儿会有什么反应呢?米开广站起来。一股凉风,从洞口进来,拂过脸颊,向洞底吹去。这个石洞其实没有底,他们住在洞的这一头,敌军住在洞那一头。洞是相通的!有时候风从他们这边流过去,有时候风从敌方那边流过来。走过顾家荣的铺位,爬上一道半米高的坡之后,就是近十米深的陡坡,底下是个地雷井。他们刚来,不能同他们说得太多了,不能让他们想一夜,敌军还可能从你的屁股后面爬上来向你开枪投弹。
已经是夤夜了。那三个兵还坐着。就让他们彻夜长坐吧,他们已经到了这地方。以后就这样了,不适应也得适应。米开广有点习惯了,或者自以为有点习惯了。提前上来一星期,强迫自己习惯了一星期。对新来的三个兵,这是上阵地的第一夜,最好能睡着,松弛一下神经。像这样坐着,你望我,我望你,互相感染,唯一的好处,是从心里制造出许多紧张。也是见鬼了,这一夜枪声不断,骚扰得比前几夜都厉害,好像特地欢迎他们上阵地。此刻,雷声听不到了,但雨还在绵绵不绝地下着。雨季提前来了吗?那不见得。米开广在上阵地之前了解过这一带的气候特点,今年的雨季可能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