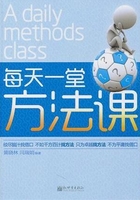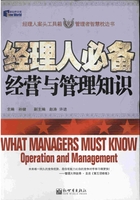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15号哨位]
天眼睁开了一般,在他们洞外,遥遥地有一小弯苍白的月亮从云缝里滑了出来。真有点像一只睡意惺忪的老花眼。
顾家荣注意到,米开广从铺位上坐起来,扭着头在洞内环顾了一下,就把目光望向洞外。“有月亮?”米开广问。
“很淡。”顾家荣说。
米开广披上军衣,套上军裤。系皮带的时候,他脑袋又一次抬起来望出洞口去。“今晚上有点凉啊。”他说。皮带扣发出惊心动魄的撞击声,撞在夜的宁静上。他打了一个哈欠,用双手使劲儿地搓脸颊,就像老猫醒来时用爪擦脸。在里边一点,蓝文定喃喃地说着梦话:“我爱你……”
“这家伙,就想好事儿。”米开广说。
“肚子饿了。”米开广说。“下午三点钟睡下,一直睡到现在。呵,这一觉睡了九个多小时啊?昨天把我们累垮了似的。可惜累得没什么意思。”
“还是救活了一个嘛。”顾家荣说。他把合着的碗揭掉,把下面装鸡蛋粉的碗递给他。“给他留一点。我来烧点开水,等会儿吞一块压缩饼干吧。”
“别点火。我喝碗凉水就行了。”
“你想拉肚子?不到我们洞口,看不到火苗。我们的胆子也太小了。”
米开广把装水的饼干箱搁在石头上。这是洞口左边的一个拐角。下午,顾家荣想到他们醒来要弄吃的,就去洞外捡了几块石头,垒起一个小灶台。这件事过去就该做的。顾家荣把固体燃料放在“锅”底下,划燃火柴。这时米开广放下碗,钻向洞口。顾家荣退后几步去看,米开广钻出洞,消失了。接着钻进来,把一块波纹钢掩上,露出一条缝。“我观察了一下,看是看不到,可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儿。”米开广说。“你想睡就睡吧。”
“不想。”顾家荣说。
火光朦胧地映在洞内的“池塘”里。山洞里的积水刚泄完,一场暴风雨,又灌出一个小水池。那水离顾家荣和蓝文定的坑铺不到两寸,他们就像睡在水上似的。顾家荣忽然看到水里漂着一只死老鼠。他擒着它的尾巴,把它掷到洞外。米开广一直在那里吃着鸡蛋粉,不觉得恶心。
“鸡蛋粉还有吗?”米开广问。
“都在这里了。”
于是米开广放下碗,再用另一只碗合上。火光下,他的嘴唇油晃晃的。“锅”里的水畅畅地响起来。顾家荣在两只搪瓷杯里泡了茶。茶叶很好,是米开广家里寄来的一级花茶。人有一样事儿不用学,那就是享受。米开广掏出两块压缩饼干,给顾家荣一块。顾家荣不要。他的嘴里又苦又干。他只想喝茶。只因等着米开广醒来,顾家荣才没有烧开水。
火熄了,顾家荣去把洞口的波纹钢移开。
折进洞里的月光很淡很淡,不过它也算一种亮光。空气里滞留着固体燃料的怪味。他们捧着茶杯,坐在洞口。米开广的脚一伸就到外面去了。冲锋枪躺在他们的膝前。
这战场,这阵地,现在是世界上最寂静的地方。上阵地后不久,米开广和几个哨长就向连长、指导员提过意见,请他们向上级反映,给各哨位配一只小收音机。报纸不可能天天往阵地上送,配一只小收音机总是可以吧?打这么大的仗,还在乎那么几百只几千只小收音机吗?此事没有下文。后来连长有一个极为勉强的解释,收音机会暴露哨位,敌军可用无线电定位。那若是理由,就应当禁止哨员们在哨位上说话。现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一线阵地上的兵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倒可能在这里,对于作战的兵们来说,战场以外的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可他们仍然知道不少,因为有家信……
一个巨大的影子从顾家荣眼前闪了过去。只看到影子的腰部以下的部分,那条腿足有一抱粗,一步跨出几米远。顾家荣眼睛一眨,那影子消失了。这是一晃而过的幻影。
“你喜欢斗蛐蛐玩吗?”米开广干巴巴地问。
可以听到一种蟋蟀的吟哦,数量不多,或远或近,声调格外凄清。这是唯一能够清晰可辨的夜籁。再就是他们呷茶的咝咝声了。
顾家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这类稚拙的话题,只能激起枯萎的回忆。只要能做到,顾家荣愿意把自己的记忆封存或枪杀。
“安静点儿吧。”顾家荣说,“这样坐着不好吗?”
才一会儿,蓝文定的梦话又传出来。“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家伙。”米开广说,“别人说梦话,很难让人听清。他呢,要么不说……”
那几间茅屋是烧光了。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其实,住在茅屋里也别有一番风味。茅庐、竹林、在竹林中觅食的鸡、丝瓜棚。夜里躺在床上,可以听到竹子的拂动声响。也有蟋蟀的鸣叫,声音和这阵地上的蟋蟀声同样优美。睡不着的话,轻轻拉开门,那吱呀的一声能传得很远。竹影婆娑,答答地滴着后半夜的露珠。也能见到月亮,圆的,半圆的,鹅毛样的,悬在竹林上,天空青幽幽的,衬托着几缕白云……瓦房未必就一定比草房住着舒服。听说杜甫就喜欢住茅庐……
“顾家荣,你有没有谈过恋爱?”米开广问。
顾家荣没有回答,不想回答。在这战场上,谈论恋爱,未免太奢侈了一点儿吧,虽然不能禁止有人想。“你去过成都的杜甫草堂没有?”顾家荣问。
“没去过。”米开广说。“怎么问这个?奇奇怪怪的。”
“我是在想,像我们这种兵,在有生之年,不知还能不能到很想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米开广笑了。他近来很少笑。“有机会去的,包括地狱。”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让人扫兴的话吗?”
“可我问你的你不说。蓝文定说他跟几个女人睡过觉。我是没有资格同他较量,因为我确实没有谈过恋爱。你怎么也让他吹牛?”
“无聊不无聊?他要吹,就让他吹吧。”
米开广讨了个没趣,不说了。顾家荣突然觉得对不起人。可能是童世杰的突然牺牲让他想到了什么。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就这么死在战场上,这可能正是米开广在想的。可是,顾家荣不想谈这个话题。他宁愿静静地坐在这洞口,望望迷蒙的天空、迷蒙的月亮,偶尔呷一口茶。父母感情还好的时候,夏日里,一家人吃过了晚饭,母亲会给老爸端来一杯泡好的茶。在乡下农人当中,老爸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至于奶奶,可能会讲牛郎织女、讲七仙女、讲古老十八代的神怪传说。母亲呢,可以趁机溜走,跟一个恰巧路过的女人去摆谈那些家长里短,在那机耕道上一站一两个小时,也不会腿肚子发酸……
蓝文定披着军衣走到洞口来了。“你们倒会享受啊。唷,月亮出来了?”
“很淡。”顾家荣说。
“‘锅’里还有开水,你吃块压缩饼干吧。”米开广说。
蓝文定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他把上衣套上了,敞着怀,拿碗的左手夹着饼干,右手拿一块木板。把木板放在顾家荣身边,坐下来的时候故意撞一下人。“在这里坐着,望望月亮,喝喝茶,咬点饼干,好!好!神仙过的日子啊。”
“你刚才说什么梦话?”米开广问。
“没有啊。我从来不说梦话!”
“行吧。你是没有说。”
月光亮了一点儿,还是淡。这迷离、清凉、浅淡的月光,给阵地蒙上了一层薄纱。与此同时,那似雾非雾的沆瀣,充盈在天地间,随着夜的深入而在不知不觉中加浓。由此,一切显得恍恍惚惚,形若幻境。往下面望,那静止的滀水,一摊、一汪、一坑、一沟,使这战场犹如露了底的养鱼塘。只不过,替代蚌壳的是插在烂泥里的粪便罐和玻璃瓶,它们身上总有最亮的那么一个点。相比之下,那纹丝不动的绿树嫩草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倒像在象征派画家的画布上枯死了。随着月亮被块云抹去,如同昏眊的老眼那样闭上,世界再度滑入黑暗中。蓝文定打了个寒噤,开始温柔而讨厌地翻腾废话箱。顾家荣忍不住插断他的话。
“看样子,会晴几天了吧?”顾家荣这样想,久雨放晴,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不要给我们发布这种毫无准确性的气象预报。”米开广今晚的情绪显得特别好。“不过,今晚允许你谈谈你的幻想。尤清园,你的幻想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