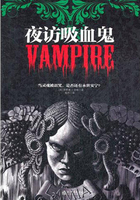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15号哨位]
蓝文定和顾家荣坐在青黑的时间上,既不想睡觉,又没有话说。也许不该说时间,那无思无欲的好像一条无人摇动也无人掌舵的小船,载着半睡半醒、似睡似醒的他们,在麻木的疲倦中向夜的深处飘荡,时间的浪花拍击他们的船板,摇得人昏昏欲梦;只有哨长米开广是清醒的、警觉的,他趴在洞口那里,腋下压着枪支,仿佛伏在小船的船尾,提防着时间的追踪。现在,这青幽幽地泛着微光的时间是他们的敌人,它从四面八方围困他们,扼着他们的脖颈。
啊,时间,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觉倒是不容易说得清楚。洞外在下雨、下雨、下雨,反正总是在下雨。这是老天爷患上了痨病,其典型症状就是没完没了地下雨、咳嗽和抽风。夜雨给他们的直接感觉是皮肤上的光滑,大腿上的胈毛都一根根地立了起来。这雨夜代替了他们的语言,它诉说着--埋在古老地壳中的原始、原生,化解着厚实、沉重、板结的大气层,把虚无填得绝对充实,又把虚无穿透、消蚀、瓦解--淅淅沥沥,絮絮叨叨,绵绵不绝,比人的语言仿佛更有力量。这就是天籁抑或时间的物化?蓝文定不屑于弄懂,也懒得弄懂。现在他想到他们少了一个伙伴(任宠),洞内的空气还有那么一丝儿--极为微弱的一丝儿--燃烧后残留的焦煳气味。当然不只是焦煳,还有那么一种悢悢然的眷念和忳忳然的烦闷……可以付之觖望的理由似乎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重整这个山洞费了他们几天时间。他们每个兵都得到了最实际的好处,又可以一个兵睡一个“铺”了,于是又有了一种然的自足感。这是时间做出的一个友好的表示。它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一个同伴拉出山洞,推进一片散发着药味的白色中,把一切遗产留给继续活着的人们。
洞口发出响声。米开广,他在缩进来,缩到可以转身的地方,他侧起身子,脑袋扭过来,接着屈起双膝,猫一般到了他们面前。
“我听到跳板洞里有说话声。”米开广说,“两个,一男一女。”
“听到了吗?”蓝文定捣了一下顾家荣,“还有女的呢。”
“一说女的,你就来精神了。”顾家荣说。
“怎么想到开这个玩笑?”蓝文定说,“想给我们醒一醒瞌睡吗?我们不会睡着的。”
“狗癞痢的嗓门小一点儿。”米开广说,“这是真的。”
“你能肯定不会听错吗?嘻,大哨长,我可要警告你了。”
“不信你们去听。”
“顾老哥,你去。”
“你鼻子专闻鱼腥味。你去吧。”
使蓝文定吃惊的是真有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在离他们十来米远的跳板洞里。这时候雨又下大了一点儿。他侧耳谛听,而从洞沿流下的雨水竟像小瀑布似的,泻在地上,起泥水点,凉在他的脸上。雨夜浓重的黑暗,好像一堵墙壁,闸在他与跳板洞之间,可他还是听到了这种声音。时间并没有磨去他对这类声音的听觉敏感性,或者在这一瞬间恢复了他的听觉。这类声音好像是从紧闭的缝隙里挤出来的。她,她们,都有这样的声音。蓝文定简直怀疑他和米开广是不是都得了幻听的毛病。他们是很容易患上这种毛病的。他曾有几次听到过她的叫声和笑声。
蓝文定捞一把雨水搓了搓了脸面。过一会儿,她的一声痒嗖嗖的轻笑透过厚实的雨墙传了过来。他往后缩了多半尺,扭头望了望里头的那两位,当然他只能望到两个模糊的影子。
大雨霫霫,越来越急骤,在周遭的山野沟壑里激起回响,幽微,深沉,意味深长。这绝不是蓝文定的幻听,东边,南边,西边,以及阵地背后的北边,确乎有隐隐的滚雷,仿佛从地下、从那一眼深不见底的深井中拱出来,向四面湓涌。自然他很多次地听到过这种声音,阴性的,她的。他没有忘记,并且刹那间记起,他这是在阵地上,然而黑暗中的阵地是干净的,因为你看不到什么,却从声音里看到许多,而那总是眼睛最愿意看到的。阳刚,即便如火山喷发,从未真正战胜过阴柔。米开广碰了碰蓝文定的脚。
“是不是我听错了?”米开广蹲在那里问。
“听是没有听错。”蓝文定说。
“雨下大了。”米开广说。
蓝文定回到铺位上。“要不你去听一听?”他对顾家荣说。
“他们的胆子也真大。”顾家荣说。
米开广走回来,侧身坐在铺边上。“今天晚上,看样子是最安全的了。”米开广说。冲锋枪带了过来,夹在他两腿之间。
“保险关上了吗?当心走火。”顾家荣说。
“跳板里有三个定向雷。”米开广说,“我埋得很隐蔽,上面盖了一层小石子。他们绝对发现不了的。真的,骗你们是这个。”
“我们没说不相信。”顾家荣说。
“引爆线埋得更深。这三个定向雷要是爆炸的话,飞出的钢珠能把整个洞子撒一遍。设置的时候,我看过角度。”
“要我去引爆吗?”蓝文定说。
“你去吧。”顾家荣说。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盯视着蓝文定,正因为看不清他的眼神,蓝文定才感觉到他的盯视。这黑漆漆的盯视把蓝文定按在地上。顾家荣的目光里有唾沫。
哨长把一根指头捺在枪口上。不一会儿他抬起脸来,平视着洞口。他的目光仿佛从洞口射出去,拐了一个弯,探进了那个埋着定向雷的跳板洞。“嘿!”米开广弄出了这么一个声音。洞子外面,雨下得很大。“雨水会淌进跳板洞去的。”米开广说。这时他的手紧握着枪口,好像很用力地往下按着。那滞重、潮湿、鲁钝的气流,似乎带进来一些雨花花。“那‘跳板洞’里面可能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了。”他说,“我就没想通,对方怎么会把女兵派到一线阵地?我军的女兵,那都在战场背后,离前线远远的……”
可是,即使那“跳板洞”里“没有一块干的地方”,对他和她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问题在于,蓝文定怀疑,他和米开广是不是都听错了?突然间,蓝文定抱着很大的疑问。
“喂!我说你的保险到底关上没有?”顾家荣说。
米开广伸下手去,把那保险扳好了。瞧瞧,当哨长的,也会犯这种毛病。那支枪走火,子弹首先洞穿的将是他按在枪口上的手,接着应该是他的下巴,然后呢,从他的囟顶飞出去……这位大哨长,还有一个“猴子”的代号!他还是不穿一点衣服,而蓝文定和顾家荣都披着一件军衣。大雨之夜,清泠泠的风吹进洞来,让人感觉到凉意。在米开广直起身来时,他望了望他们,像要问什么事,可又没有问出口。
“你不要着凉了。”蓝文定提醒米开广,“还是把军衣披上吧?”
“没事。”米开广说,“你们两位,对这夜里的声音要保持高度警惕。”
顾家荣在胸脯上按了一掌。“都吃饱了。一手掌的血。”顾家荣说。
“你怎么搞的?没有感觉到蚊子叮你?”
米开广去看那只手,没得到允许。到底有没有拍死蚊子不得而知。“不知任宠怎么样了?”他就说。
“不是说没什么吗?”顾家荣说。
“那是第二天的电话。我是说转院以后。”
“这下让他‘好’了。”蓝文定说。
“你说什么?”米开广问。
“没什么。”蓝文定说。
“你听他的?”顾家荣说。
“对。做过生意的人……和尤清园是同一类……”米开广说。这时他伸了伸心神不宁的脖子,望向洞口。遮在洞口的雨帘,晃动,甩打,突然绞成一束,又哗地分开,在黑暗中闪亮。顾家荣的目光也望向洞口。“这雨下得……”米开广说。他侧着耳朵倾听,然后站起来,弯腰走向洞口。“水流进来了。”他告诉他俩。他的背部挨着洞壁,右手提着枪,脑袋往前探,好像一种特殊的舞蹈造型。他听了一会儿,踮脚走回来,那只空着的手捋着胸脯。“别以为我又想去听女人的声音。”米开广说,“不是我值班,我就不管了。”
“我没有说你。”顾家荣说。
“我也没有开口。”蓝文定说。
“该让你值班了。”米开广说。
“这么慷慨啊?”蓝文定说。
“你看看手表吧。”米开广说,“警惕性还是要的。”
“好吧,反正也不想睡。”蓝文定接下冲锋枪,走向观察孔,坐了下来,把保险打开。
再没人说话了。他们之间的话题正在逐日减少。有时候,创造一个话题,比什么都难。何况是现在。现在,夜雨淋着他们的感觉和思想。他们沉默着,独自享受沉默的快乐,任凭雨夜的分量在他们周围扩展、膨胀。现在蓝文定坐在这里品味着雨夜的潮湿与漧燥、喧嚣与沉寂,特别是雨声,它挣脱了时间的捆缚,按它自己的本意,倾诉着他们说不出来的意思和感受:那也许存在却又没有终极解释的无限和永恒,以及灵魂--假如真有灵魂的话--都陷在时间中喘息。不知米开广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还在想着雨水会不会淌进那个跳板洞,以及跳板洞里的什么声音。独自坐在观察孔下向外观望黑暗的夜雨,蓝文定恍然大悟。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背后传来问话声,是顾家荣在问。
蓝文定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想回答。如果想听到什么声音,这雨夜里什么声音都有。“猴子哨长”米开广制造的这个玩笑,哎呀,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