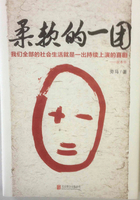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狙击枪手]
淫雨后的第一个大晴天,阳光把关存道晒得昏沉沉的。昨天,连长让六〇炮摧毁敌方一个哨位的洞口工事,以此逼得他们出来修。那正是七百米左右的最佳射程,他准确无误地放倒了一个。今天再用老办法,他们也不会白天出来修工事了。一上午过去,在他的射击范围内,没看到敌方的一个兵影。
这里不是一个很好的狙击步枪枪手的潜伏位置。以一个连的兵力看,本连的防线可以说已经很长,可实际距离又很短。在这样的距离内,找到一个良好的狙击步枪射击位置其实是很难的。在军工背运货物上阵而且也是雨雾朦胧的时段,关存道已先后五次在本连防线内诇察过了。他发现,能确保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又能确保他在杀敌后安全撤离的射击位置少而又少。就伏击位置而言,有的只能用一次,有的可以用两三次,有的需要等到以后再用--始终伏在暗处的狙击枪手最需要给自己留下余地。而他今天选择的位置,就是只能用一次的。这里,有一块面积不会超过五平方米的“平地”,上面长着三四尺长的荒草和差不多同样高度的灌木。为可靠利用这片葳蕤的荆草,他今天穿着掩腕没踝的迷彩军衣。趁山岚尚浓的早晨,他伏着身子,一边推着狙击枪,一边钻入这片灌木荒草。左侧有一块突兀得仿佛摆在地面上的巨石,能允许他在打了一枪以后迅速滚身隐蔽。若阴天或仅有箭头小雨的日子,这个射击位置还不错。可是,这个地方呈约十度角向前倾斜,伏身其上而寻敌射击是很不舒适的。周遭三四十米方圆内,没有一棵碗口粗的树,借荫乘凉不可能。现在,他背上的一些灌木,还像原先的那样缠绕,想要滚身隐蔽并不容易。这片相对孤立的荒草坡也相对的比较惹眼。假若对方的望远镜能像他那样耐心细致地观察,很难保证不会被发现。然而,连长的命令在黎明前夕下来了。关存道不能不执行命令,情急之下就选择了这个位置。现在是午后时分,久雨之后显得格外炽盛的阳光照耀着山山岭岭,好像在吮吸一切可以吮吸的水分或烘烤一切可以烘烤的景物。这片草棘变得像甑子。关存道的额头上流下的汗水,隔一会儿就得抹一下。抹晚了,汗水流进眼里,立即催出泪水。今天他带了一片塑料纸,用来放毛巾,它就在脸边,随时可以拿起来擦。就算这是个好主意,总没有待在荫凉下舒适。他那羡慕、忌妒、生气的目光,好一会儿里都望着待在一旁的灌木丛下的一条蜥蜴。
吃过压缩饼干,他又晕乎乎地举起望远镜。斑驳的山林在镜中摇摇晃晃地滑过,闪烁着然曜光的翠绿,歪斜的损枝落叶的大树,东一个西一个的弹坑,这景象已毫无新鲜感,不能刺激他的视神经。他压下镜头,模糊的绿影急速地向上升,然后一下停住,见到是一床鲜红的毛毯--趁这天气晴朗,敌兵把它铺在石头上晒。接着又见到几床被子,恍若青烟似的水蒸气在那被子上缭绕。一切都颤动着恍恍惚惚的虚光,炫目,飘浮,热气腾腾,散发着困顿的行将消散的气息。镜头向左向下移动,在一片深密的绿荫下,看见了两个人。他稳住望远镜,转动调整距离的螺丝。一会儿看清了,两个赤膊的兵在那树荫下下围棋,粗糙的木板棋枰,一黑一白的棋子;一个兵斜躺在山坡的纤草中,悠缓地吸着香烟,眼望棋枰;另一个指夹一枚黑子,刨着脸颊,正陷入深深的思考。他们头上悬着浓密的树冠和藤萝,有点点阳光落在棋枰上。那里显然很凉爽。棋枰旁边,纤细的小草动摇着,好像有一丝林下小风在那儿吹。往周围观察,没发现他们的哨位,想来那哨位相距不远,但是很隐蔽。再看他们时,执黑棋的那个兵捧着水壶喝水,刚才躺着的一位已经坐起来,擎着一枚白子,久久地放不下去,最后又缩回手。距离约有三百米。太近了。近距离的敌人是不能打的,有规定。这两个兵胆子很大,看上去好像不辨时日但顾弈术的隐士。关存道沮丧地放下望远镜,抚摩一下狙击步枪的枪管。枪管被太阳烤烫了。
他忽然想到汪嘉梧。昨天,他打死一个敌兵不久后就撤进哨位了。活动了一下趴得僵僵的躯体后,他开始擦枪。汪嘉梧阴阳怪气地踅到他身边,仿佛欣赏他擦枪的动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望着他的手。
“帮我擦枪?”关存道说。
“我才不。”汪嘉梧说。
“那就请你走开。待在旁边,你不觉得热吗?”
“好像不。”汪嘉梧说,“你这样打他们,他们变了鬼,要找你的麻烦。”
要是他先不开口,汪嘉梧会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呢?会!汪嘉梧迟早会说。那句话,汪嘉梧可能想了好多天了。昨天他打死的那个兵是和汪嘉梧一样的大个子。即便汪嘉梧不说,他自己也已想过很多次。战场上就这样,敌我双方总有那么一些默契,那么一些无须经过商谈的约定。有些敌人是不需要打的。关存道想过,他这支狙击步枪所射杀的敌兵,未必都是需要射杀的。我们这边也有十来个兵死于对方的狙击步枪和别的冷枪下面了,虽然极大多数不是本连的。而那天夜里的战斗,分明是敌方的一次报复性袭扰。可是,他不想和汪嘉梧争辩,也不想和自己争辩。他不过是一个枪手,一个执行命令的枪手。
“你最好自己去问连长。”关存道想说,但没有说出来。他是个不喜欢说话更不喜欢辩论的枪手。他自己还明白,他可能不会再笑了。
关存道相信迷信。他的祖母和母亲常年茹素,最信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小时候头痛身热,也吃药也打针,可家里人总先求菩萨询问,然后是焚香许愿,祈求早已物故的祖上庇佑。他也信佛,而且不是那种年轻人在空虚时寻求精神寄托的忽冷忽热的信。他是真信。在汪嘉梧一语中“心”以后,他发觉自己擦枪时候的注意力有点儿恍惚。这时间不长--作为一个枪手,他有这种心理上的快速排碍能力--但他毕竟感觉到了。
晚上,他躺在潮湿的已经可以绞出水来的铺位上,联翩想起死在他的狙击步枪下的那些兵。用连长的话说,他的成绩令人骄傲,除掉第一枪打空,此后枪枪命中,已经击毙了二十三个。每一个都被打在要害上,排除了救治的任何可能性。对方没有防备,而他总是趴在一个什么隐蔽处,屏息静气地在望远镜和狙击步枪的瞄准镜里观察好长时间。他们都给他留下了铭心刻骨的、不可磨灭的、永生难忘的印象。这和双方激烈的对射完全不同。在那进攻和反进攻的激烈枪战中,看见一个兵倒下,并不能断定那就是自己的子弹打中的。在那种情况下,你不打死他,他就会打死你,没有思考的时间,活着的一个只有生的激动和胜的喜悦,不会在心头留下其他的痕迹。然而他不同。他想到了这种不同。有时候,他要在两个对象中选择一个,把那打击对象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兵的出现,他们不同的长相、神态和大致上的年龄,子弹打进去的部位,被击中时的刹那反应,倒下去并躺在地上的样子……关存道都一一想了起来。把敌兵击倒后,他还一边望着那在血泊中抽搐、痉挛、僵化的人体--那总要延续很长时间,一边不动感情地替那兵敌想出一生可能有过的经历和家庭状况。每一次就这么想着,想着,他把水壶拿过来,水倒在壶盖里,一盖子一盖子地慢慢喝……
梦中,关存道看见自己跟着老祖母走进寺院。正是寺院的早课时分,噌吰的钟声,节奏单调而强烈的卟卟木鱼声和师父们沉宏的唪经声混和在一起,把什么是庄严和神圣的感觉如同醍醐灌顶那般赋予每一个踏进佛地的人们的心灵。在四大天王的脚下,他觉得自己渺不足道,太小了。他把零花钱其中大多是他当兵的津贴费都投进佛像下的功德箱里。看到有人把伍拾元、壹佰元的新钞票插入箱口,他觉得自己的钱太少了。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目的不明。这是赕佛消灾吗?他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在铁鼎状的香炉边,他帮祖母点燃了香,一炷炷插好。在观世音菩萨的白玉雕像前,他跪在祖母身边,身子伏得很低,听到那个随着他的磕头而一下一下敲响的木鱼声,回响在深邃的殿堂里……
钢盔沉重,像一只小石臼套在头上,压得他头颈疼痛,头皮麻木。可是钢盔不能不戴。关存道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灌木和荒草脚下,有着不少身体灰白色的多脚蚰蜒、壳体很小的蜗牛、色彩斑斓的小甲虫、黑色或黄色的小蚂蚁以及小蚊子。这个时候,这些小虫豸显得非常活跃。他觉得,他身上到处都在发痒。蚂蚁或者什么小虫因为他的无端侵入,好像颇为不满,钻进他的军衣里面四处骚扰。他忍着,再次举起望远镜,一下子就发现一个兵影。他的心怦然一动:该死的,怎么往我的枪口上撞。这是一个暴露的哨位,因为距离挺远,伪装得比较粗疏。那个兵,看着好像小娃娃,正从洞口走出来,穿着白衬衫,红短裤,头发长长的。关存道调整了一下望远镜的焦距。现在看得更清晰了,是个小男兵,年龄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岁,还挂着一脸稚气。关存道在下意识里迅速摸住狙击步枪,把那小兵从望远镜移入步枪的瞄准镜。身影没有在望远镜中清楚,可看不清的只是细部。他放掉望远镜,把瞄准镜的三角符号套在小兵身上--这小兵死定了!“你死定了!”他想。
子弹早就上膛,现在只须扣动扳机。今天有风,风速不稳,约在三四级左右。阵风掠过,大片的树叶翻转,像是泛着白光的黛色波浪,在起伏不一的山坡上推移涌动。这不必担心,他能随时根据风速修正弹道。他运着气,盯住小兵,想打那较为宽阔的胸部或背部。这小兵好像出来拿东西,他拐了一个小弯,从下面往上面的哨位走去。他走路的样子蹦蹦跳跳的,有一股天真的淘气劲儿。关存道想到自己在这个年龄段也喜欢这样爬山,也不知道疲乏,不知道危险的潜伏。枪口跟着小兵的背部缓缓移动,每一秒钟里都能稳稳当当地击中。“我不打死他,他早晚都会被人打死吧?只要留在这个战场上……”关存道这么想着,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扣动扳机。手指上有一点反弹的压力,这压力通过手臂传到心头。“他太小了,太小了!就不能让他多活几年,哪怕只多活几天?”不知不觉中,他感到右手食指很痒。低眼看,一只黄蚊子噆在他的这根指头上,肚子一缩一鼓,正用力嗍吸他的血液。关存道突然松开右手食指,用左手食指捺死蚊子。等他再次望向瞄准镜的时候,那个小兵消失了。关存道吁了一口气,心想:“这个蚊子救了你,这个蚊子用它自己的生命救了你。”他也想到,对面那个小兵是不会知道的,不会知道死神刚才已经抓住他的背。“也是他命不该绝吧?”
天更热了,脑更晕了,脰颈发酸,胸口憋得难受,视线愈来愈眩瞀。什么都在强烈而燊盛的虚光里飘浮。山岗,林木,岩石,一时都失去了根基,时升时浮,左右晃荡,好像发生了地震。背上的感觉,是皮肤被烤焦了。就这么趴着,腘窝处的酸软无力依然很明显。胸口又疼起来,嗓子梗塞,好像堵着一根骨头。于是眼前的大山开始颠倒,他晕了过去。“我中暑了。”关存道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