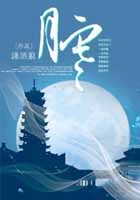[迫击炮班]
戚佐治汗水淋漓,可他喊着冷。董林虎拿下冷敷的毛巾,觉得热乎乎的,在凉水里清了清,又敷在他的额头上。戚佐治的额头很烫,双颧红赤,呼吸急促。不过,他一下子还死不了。董林虎想到那天夜里他打双炮的疯劲儿,就凭这股疯劲,他一下子死不了。随即戚佐治睁开眼睑,结膜充血,红红的一双血眼。董林虎在他头后,他看董林虎,上眼皮翻得很高,瞳孔以上的小半黑眼珠突入上眼皮下面,额头皱起三道深深的抬头纹。他老了,董林虎突然觉得。以前没有看到他有这么深的皱纹。
“你是谁?”戚佐治问。
“你都认不出人了吗?”董林虎问。
“不。”戚佐治说。上眼皮收下去,眨着,在枕头上动了动脑袋。他身上有一股浓重的汗酸臭,董林虎刚才还给他擦过,可是擦不掉,仿佛这汗酸臭不在他的皮肤上而是从骨头里面发出来的。他的腋窝里盛着一汪汗水。
“指导员刚才来过。”董林虎说。
“他说什么没有?”
“他说,如果实在不行,只好把你抬下阵地去。”董林虎灵机一动就这么编。其实指导员对董林虎说:“病得这么厉害,糟糕不糟糕?别人可以病,就他不能病,但他偏病了。”董林虎观察着班长的反应。
“你怎么没有叫醒我?”戚佐治又翻起上眼皮,在额头上弄出三道皱纹。董林虎想笑,这个戚佐治。他的眼睛红得可怕,好像随时都会有鲜血溢出来。这样的红眼只能出现在戚佐治身上。如他们,发烧到50℃,眼睛也不会这么红。董林虎这话不是瞎说。
“我叫过你,可是叫不醒。你刚才说胡话。”
戚佐治翻动身体,毛巾从他额上滑下,然后他趴着,压住一条胳膊,昂起一张惶恐的脸。他的血眼望着董林虎,流露出失去自信的疑惑、慌张与懊。这眼光顿时把董林虎抛入血河中,弄得董林虎从头到脚都是血。“我说胡话了?”他急切地问。他呼吸急促,喉咙那里噗噗噗噗地响,如同抽拉风箱一般,吸进去的不可能不是凉气,吐出来的却像保温瓶里冲出来的热汽。他龇牙咧嘴,惶惶不安。青筋在鬓角上弹跳,很粗,像蓝色的蚯蚓在晒烫的石板上扭动。
“其实你也没有说几句胡话。”董林虎改口说。
“一定说了。”戚佐治的血眼里泛出泪花,“听到我说了什么?指导员,他?”
“都没有听清。你说胡话的时候,嘴里好像含了一颗大核桃。”
戚佐治摇头,把往日的自信都从他的脑袋里摇掉了。董林虎相信,人的自信是装在脑子里的。现在戚佐治班长仅剩一点倔强,好像一头面对屠刀的水牯牛。
“指导员走了以后,我才听清一句。”
“是什么?我说了什么?”
“你是说了一句我能听清楚的胡话。你说,‘你能不能让我亲一亲?’”董林虎看着那块冷敷用的毛巾,“你在发烧的时候想过什么?”
对董林虎的胡诌,戚佐治没有表态。有可能,戚佐治刚才真的那么想过。他躺下去,重新转过身,仰着。董林虎还把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看他闭上眼睛,不想再说话,董林虎躬着腰,从那低矮的坑铺洞里退出来,想到外面透一口空气。洞外撑着两只脚,两只胶鞋都很脏,两条小腿细细的没有什么腿肚子,两只极其宽大的短裤管盖没了膝盖。董林虎在其中一条腿上拍了一下,它让开了。
天放晴,灰色的天空泛着炫目的白光。水坑当中的一些小阜正在变干。羊军成咬着一叶青草,草茎在他嘴边上一上一下地翘动,一条细细的手臂压着横挎的冲锋枪。现在他站岗。
“今天有一个人要死。”羊军成说。
“不会。”董林虎说。
羊军成吐掉草叶。在他慢腾腾地呸吐时,他的眼睛仰望着天空。这介于阴天和晴天之间的天空,白得混浊,白得耀眼,白得空虚。空中没有一点儿云影,也没有一点儿鸟影。“你习惯了吗?”羊军成问。董林虎不知道他在问什么。过了一会儿,羊军成才说:“一天吃两餐饭。”
“不习惯又怎么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饿。可是过了中午,又不感到饿了。”
羊军成只晓得他的肚子。不,他能晓得自己的肚子就好了。董林虎不想和瘦小子羊军成讨论吃饭的习惯,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话题。长这么大,董林虎到今天才发现,人与人之间,有时候,语言不能成为交流的工具。羊军成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和谁谈什么。董林虎只是望着那天空,望东边,望西边,望南边,望北边。其实他也不想望什么。他从来没有琢磨过天空。天空天空,天天都空。
再次钻进班长的坑铺坑洞里时,他仍然仰躺着,手脚伸得笔直,挺尸似的。“今天有一个人要死。”羊军成说的,不是指他戚佐治。要把这位戚佐治拖死不怎么容易。他的体质比董林虎好。董林虎是第一次看见他吃药打针。别看他现在这么憔悴,颧骨高耸,好像被炮弹砍光植被削平岩石的无名高地;脸颊深陷,好像那天夜里在炮座下凹陷的泥坑;头发干枯,好像深秋时节的坟头茅草;手脚干瘦,好像抛弃在乱葬岗中的带皮残肢……专司把生魂带向地狱的无常还不能把他吊走,他家的门楣还不能挂上光荣烈属的横匾,总之“白头送乌头”的时间还没有到--听说他妈的头发早已白光,无一丝黑色。
“天晴了?”戚佐治闭着眼问。
“是的。”
“我对不起你,董林虎。”
董林虎望着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干裂,有一片片的白色皮肤翘了起来。这不像是他的嘴。他的普通话讲得比谁都标准,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这样的政治干部都敬他三分。他和连长同年入伍,连长同他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在连、营首长那里能够听到的话,在他嘴里都能提前听到,词汇有差异,意思一个样。他总能事先猜到连、营首长的意图,于是他有一个“小杨修”的绰号(据说三国时候的杨修总能预先捕捉到曹操的心思,弄得自以为独占智慧的曹操很不高兴)。让全连以至全营士兵想不通的是戚佐治怎么没有得到“拔擢”(连里的文书就喜欢这么说)?也许是他太聪明、太能干了,兵们都这样猜。俗话说,聪明智慧多磨难,这好像应在戚佐治身上了。董林虎看着他的嘴,他的嘴唇很薄。道歉的词语不可能从他的两张这么薄的嘴皮中滑出来。
“原谅我吧,是我让你背着大处分上阵地的……”
董林虎摸摸他的额头,滚烫!于是把冷敷的毛巾翻了一下。“你又说胡话了。”董林虎提醒他。
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机放在坑洞口。董林虎一听就是连长的声音,连长也听出了董林虎的声音。“你班长怎么样?”连长问。“你班长现在能不能起来?”以下的内容董林虎都想到了,连长要用炮。连长只相信全师出名的神炮手。董林虎猜不出的仅仅是射击的密位。戚佐治转过头来望着董林虎,睁着红眼睛。董林虎说了电话内容,戚佐治眼里立即闪耀着明亮的血光。
“你把这开水先喝了。”董林虎去捧罐头盒。水早凉了。
“等会儿。”戚佐治说。董林虎远远地望着他,尽管他们之间只有几尺远,却觉得距离很远。他双手撑起身子,靠着坑洞壁,把两条瘦弱的腿--也是董林虎的想象吧--搬开来。这时他的呼吸粗了,身上冒出一层虚汗。董林虎远远地站着,看他扶着洞壁站起来,看他跨出第一步,看他软绵绵地跪下,然后又扑倒在洞口。“扶我一把。”戚佐治喘息着央求。董林虎把盛着凉水的罐头盒放在班长的枕边石头上,等他回来就可自己喝,不用他人再端。
戚佐治的胳膊滑腻腻的,腋下很黏,皮肤上的热度大概有39℃多。
“我去替你打好了。”董林虎说,“要不我去叫副班长?”
戚佐治拨开董林虎的手,自己扶着洞壁走出去。担心他摔跤,董林虎跟在后面。洞外的白光比刚才强了一点儿。一只麻雀神气活现地停在套着炮衣的炮管顶端,歪着脑袋。羊军成从右边走过来,走了几步又站下,望着董林虎。董林虎向他点下巴。班长扶着洞口,身子没有完全挺直,眯着眼睛,呼呼地喘息。
“别耽误时间了。”董林虎说。
虚汗在戚佐治胳膊上涔涔地流。“你去搬炮弹。”他说。接着他扭过头来,严厉地瞪住董林虎。他的头颤动着,好像装在弹簧上。
“要用炮?”羊军成问。
“你去问连长。”董林虎说。
当董林虎端着炮弹箱出来时,老戚居然在那儿脱炮衣了。
白天打炮不像夜间那么好看。第五发也就是最后一发炮弹出膛时,老戚歪了两歪,软软地倒在地上。“还不过来帮个忙?”董林虎对站在远处的小羊说。但他没有从另外两个哨位钻出来的人跑得快。他们把戚佐治扶到董林虎的背上,董林虎反手抱住班长的大腿,就往洞里背。戚佐治的身体又烫又软,像只没有灌满水的大热水袋。就这样把他背到他老婆那儿,可能会把她吓得晕倒。可惜董林虎只能把他背到前线的山洞口。背着他钻不进洞去。于是几个兵又来帮董林虎抬。董林虎抱住他的双脚,使劲儿往里拉。这时他哼哼着,双目紧闭,脸色灰白,臀部往下沉,两条手臂耷拉到肩膀后面,手背拖着泥土,仿佛被他自己打出的炮弹打伤了。他们生拉硬扯,把他塞进狭窄的坑洞铺位,就如把他从棺材的一头塞进去似的。随后他们用那块做冷敷的毛巾替他擦汗。那汗水有股特别的气味,挺难闻。
“这大白天怎么打起炮来了?”副班长庞海自言自语。
“副官,”董林虎说,“你还是给周医生打个电话,请他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