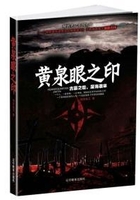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7号哨位]
氧气已经不多,他们都知道,再不挖通,他们将被活活地闷死。现在,连首长和阵地长还不知道他们的泥洞口在炮弹的轰击中垮塌了,电话线也被炸断了。他们和连排首长失去了联系,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尽快挖出一个通气孔。可是卫安挖不动了,每一锹只能挖下一点儿泥石。
“我来。”童世杰说。
给他让位,卫安从稀湿的烂泥上往后爬。这堆烂泥也快把洞口过道堵没了。尤清园跪在泥水里,两手按着地,朝着堵塞的洞口仰着略带冷笑的面孔,嘴张得老大,但舌头没有拖出来,尾巴也没有看到。卫安在尤清园侧前的烂泥上坐下,再不想动弹,而尤清园也不看卫安一眼。
洞里又闷又热又暗,泥壁上粘着、流动着水珠,到处是稀泥烂浆。烂泥的凉意使卫安感到肮脏的舒适。一时间,卫安喘不过气来。倒不是在这个时候还吹牛,卫安比他们三个挖得多,他的力气用尽了。不能挖通洞口,他肯定会最先晕厥。裆下,用急救包的纱布做的阴囊托带粘满了污泥,好像在他两腿之间长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圆形的烂茄子,里面不只是疼,而且奇痒难熬。洞口的掩蔽部炸塌后,因为闷热,他们又把为应战而穿上的军衣脱光了。卫安看到自己身上滚满泥污,就不知脸上还有没有他的皮肤。他想把裆下的托带连同那痛痒难忍的东西一并摘掉,可他双手疲软,好像弄脱的假肢,垂在那里不能移动。还有被蛇咬伤的脚趾,疼起来那神经一拉一拉的。童世杰呼哧呼哧地喘气。他旋动那把发疯的小铁锹,把它深深地插进一个直径不足半尺的小洞里,撬着,旋着,再把它拖出来,往背后摇落泥块。他那从烂泥中露出几小块皮肤的后脖颈和脸颊红得发紫。
“呵。”缪云棠说。接着卫安听到一股水声,闻着一股热烘烘的臭气。尤清园跪在那里解小便。小便不多,好像泡得很酽的红茶,顺着他的膝盖和小腿两侧往后流,而他还像刚才那样跪着,双手按着烂泥,张大嘴巴,望着那个被堵塞的洞口。只有两三岁的裸孩才如此,这浑蛋!马上死了,也要死得像个兵。卫安真想骂他。
可是卫安头晕,只记得自己是哨长,却做不出决定了。他一阵一阵地头晕,每一阵都觉得要昏过去。
缪云棠泪汪汪地望着尤清园。这新兵娃儿有点坚持不住了,一只泥手捂着左胸,脸上的肌肉突突地抽搐。他忽然望着卫安,眼里饱含着询问、哀求和绝望,这眼光似乎表明他在恳求速死,不想这样受折磨。他的想法像他的身体那样赤裸地毫不隐讳,一点羞耻也不顾。卫安怒不可遏,盯住他,狠狠地,只愿自己的目光能比刺刀更锐利。在卫安的逼视下,缪云棠的头低下了,两只泥手在满胸的烂泥上扣出一道道横纹,仿佛要把胸膛往两边扒开。这一切,卫安是在非常暗淡的光线下看到的。尽管缪云棠坐在卫安身边,但卫安几乎看不清缪云棠的脸部细节。烂泥洞内的焗闷感确实每一分钟都在加强。在这当儿,最需要的是冷静和耐心,可卫安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鼓励他的哨员们,也没有说话所需要的足够空气。这时尤清园扭过头去,望着缪云棠。他望了好一会儿,同时他的嘴巴一直老大老大地张开着。当他的目光从缪云棠的身上移开,又望着卫安,眼睛睁着,眼皮一眨也不眨。这一双眼睛睁在满脸的烂泥当中,使卫安感到做噩梦一般的恐惧。从这双眼睛里射出来的已不再是人的目光,简直是坟地里的鬼火。在他的一再盯视下,卫安喘了一口大气。
尤清园开始往前爬,从稀泥和他自己的小便上往童世杰那儿爬去,膝盖打着滑,双手陷进了稀软的泥块中,喉咙里迸出一种别人根本听不懂的声音。童世杰手上的铁锹正在慢下来,但是还在那儿咬牙切齿地使劲。尤清园去夺那把锹,而童世杰把那铁锹抓得很紧,怎么也不放。忽然尤清园低下脸去,张嘴咬童世杰的手臂。童世杰放掉一只手,在尤清园的额头上推,但那锹终于落在尤清园的手上了。尤清园往前挤,把童世杰挤得在泥壁上贴着,两只脚好像也被定住了。于是童世杰的上身往泥壁的一侧倒下去,几乎躺在烂泥上,把那被压住的一只脚往这边抽。与此同时,尤清园的铁锹已捅入由童世杰掏了一尺多深的那个小洞里。整根锹柄都捅了进去,他双手握着柄顶。
连长,指导员,卫安心想。
妈,卫安说。她站在床外,喃喃地祈祷神灵的护佑。他发着高烧。医生已经来替他看过了,但他的体温老是不退……
连长,卫安说;指导员,卫安说。你们不要对我妈说我牺牲了,她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受刺激。我那三个哥都是光棍,就盼着我传宗接代……
“啊,啊!”童世杰说,头往尤清园那儿钻。通了,挖通了!尤清园捅出了一个洞,有拳头那么大。一缕柔弱的白光带着一股空气泄了进来。
尤清园把童世杰的脑袋推开。“来!”他说。“过来!”他在叫缪云棠。
“去。”卫安对小缪说,“到那儿去!”
卫安立即觉得尤清园是他哨位上最好的兵了,在这时还能想到先让新兵吸氧。缪云棠往洞口爬,但爬不动。尤清园伸过手来拉他。第一次拉滑了。两个兵的手上都有太多的稀泥,润滑油似的。
在好长一会儿里,他们四个兵的脑袋挤在拳头大的一个小孔边,张着嘴巴大口呼吸。他们精赤条条,身上都是泥,犹如滚烂泥塘的猪。在这好长的一会儿里,卫安感到腿缝里的痛和痒。人啊,有时候真他妈的难说,哪一样都不能少,哪一样都不能多,猛于虎豹,弱于蚂蚁,还没有蟑螂的生命力。尤清园把那进气孔又捅大了一点儿。撬落的那块泥,落在灌满泥土的编织袋的缝隙里。他们从这小孔里看到一块掉下的波纹钢,它弯着,上面压着编织袋。他们的进气孔正好掏在这波纹钢的弯拱下。这太侥幸了。要不然,他们一定挖不通的。这波纹钢的那边,又不知堆着多少填满泥石的编织袋。那白光是从左边弯过来的。他们太幸运了。再过半个小时甚至几分钟挖不出通气孔,他们死定了。其实这用于防御的烂泥洞,和坟墓差不了太多,经不起炮弹的当顶轰击。在他们的呼吸匀过来以后,童世杰说:“要不是我,今天……”
“让你吹吧,今天。”尤清园说。
“都不错,都勇敢。”卫安说,“最后五分钟,我们坚持过来了。”
“我肚子饿了。”童世杰说,“还给小缪过生日吗?”他忽然想起来。
“过!”尤清园说。小缪的生日是昨天,昨天傍晚,他们正在为他的生日准备炒菜时,晚上要打仗的命令下达了。因为那掩蔽部看来禁不起一两发炮弹的作弄,因此他们把餐具、水、蔬菜都拿进坑洞里了。“把炉子先拿来!”尤清园说。
现在他们又活过来了,并且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尤清园在进气孔下用铁锹拍平稀泥,卫安先把煤油炉子递给他。接着他们用大约不到一碗的水洗了洗手,就开始做饭炒菜。童世杰把要炒的菜从最里面传给卫安,卫安再传给尤清园。菜炒好了,尤清园递给卫安,卫安又给童世杰。卫安的腿缝里又疼又痒,只好坐着,动手不动脚。童世杰一边爬进爬出地传菜,一边用卫生纸夹着压缩饼干大嚼。一支蜡烛插在烂泥上,另一支蜡烛点在过道的拐弯处。缪云棠坐在炉子的这一边拿着一本《古今传奇》杂志,把油烟从那进气孔里扇出去--大军工最近给阵地上送来一批杂志,一个哨位三本。但是,大部分烟子潴留在过道里,涌入坑洞底部。通过进气孔,可以听到外面的雨声。对他们来说,那声音已在另外一个世界。
尤清园的坑铺洞对着缪云棠的坑铺洞,在这个“十字路口”,他们摆了一桌生日宴席。菜放在两只并排的手榴弹箱子上。尤清园和缪云棠各坐在自己的坑铺边,童世杰坐里面,卫安坐外面。做了五个菜,一个汤。这是他们上山以来最丰盛的一桌菜。为了这桌菜,他们筹备了一个星期,哪个青叶子菜可以省下来,等到缪云棠的生日那天再吃;吃的那天应该在天黑以后,点上蜡烛,创造一种温馨的氛围……尤清园撕开一个浴包,一人给一块湿纱布。它刚够他们把手重新擦一遍。然后又用卫生纸擦了擦脸,权当自己的脸已经成了屁股,主要是把嘴巴周围的烂泥擦干净。
以水当酒。不过,有这样的一大碗水,就很不错。多亏老天爷下了雨。假如都靠军工背,那水仍然很紧张,还不好喝。以前,卫安对他们三个哨员一直很苛求,今天大家可放松一点儿。讨厌的是卫安的腿缝里又疼又痒,想把粘满稀泥的阴囊托带去掉,又怕把皮磨破,害得他高兴不起来。
“小缪,”卫安说,“今天是你满十八周岁的生日。夜里我们打仗……”
“不要啰里八唆的。”童世杰说,“我们差点死在他的这个生日里。”
“祝你生日快乐,妈唷!”尤清园说。
小缪咬着嘴唇,眼泪直往下流。
“今天,倒不是因为你生日,我想活下去了。我们还是争取活下去,哪怕将来什么也得不到。”尤清园说。
“对,尤清园,你这张狗嘴今天说了一句人话。”童世杰蹲起来,“我也想活了。小缪,在你的生日,我们一起发誓,坚持着,一起活下去,活下去!来,喝酒!”他一口气把一大碗的开水喝掉了。放下碗,他长叹一声,“可惜不是酒,太可惜了!”
他们是四只泥猪。在他们身上,这会儿只有嘴巴和手是干净的。洞口还堵着,他们都没有说它。只有先把肚子填饱了才能挖洞。
“你的福气不错,小缪。”童世杰一边咀嚼一边说,“我活了二十二年,还没有庆祝过一个生日。”
“你有生日吗?”尤清园说。
“你妈的。”童世杰说。
“我都忘了。”缪云棠说。他消失在坑洞口。再出现的时候,拿着一包红塔山牌香烟。他们三个目瞪口呆--你还有烟?!他们有两天没有抽烟了。“我藏了一包,准备过生日的。”
抽上香烟,他们的话就多了。这时卫安非常后悔,因为他本来可以为缪云棠的这个生日藏下一瓶酒。他有个老乡当大军工,就往他们阵地送货。那老乡让曹靖捎话,如果他想喝酒,就给他捎一瓶来。可是他的胆子太小,怕连长、指导员知道。也在这时,卫安的腿缝里痒得受不了。这就是顾面子的好处。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好阴囊,他的烂了。要是一开始就和他们一样不穿衣服,他也有一个好阴囊。现在他什么都不要,只要让他底下不再痒、不再疼。他得忍着。他不能败坏刚在他们身上出现的兴致。卫安真想同他们解释,刚才挖洞出力太猛,身上发热流汗,现在他底下有多么痒、多么疼,正在流脓水……可是,他不想让他们看出来。刚才快憋死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害怕,可现在他却害怕起来了。他的生殖器可能会烂掉,好像小黄瓜似的枯萎脱落。可能不须等到他下山,他的东西就烂光了。到他有幸活着离开这战场,给他一个女人,他也没有用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挺折磨人。
“我想给三个战友大哥唱一支《生日歌》。”缪云棠说。
“好,太好了。”尤清园说,“我们给你伴奏。”他拿起筷子,一手一根。
“你是应该给我们唱一支歌。”童世杰说,“我们差点儿死在你的生日。可是小老弟,要不是你的生日,我们很可能就被闷死了。唱吧,唱吧!”
缪云棠声未出,泪先流。“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是不在公开场合唱歌的。我怕羞,怯场。今天我献丑了,为了卫哥、尤哥、童哥终于挖出一个通气孔,让我还能过这个十八岁的生日……”
尤清园扭过脸去了,好像流了泪。童世杰说:“废话少说。唱吧。”
在我生日的时候,
我在大山底下爬……
缪云棠的嗓子明显地还带着一点童音。确实,不能说他成熟了。卫生纸擦过的脸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泥痕。他的眼泪流到上嘴唇,变得混浊了。尤清园埋着脑袋敲碗边,他的头发也沾满了稀泥,耳朵、鼻子、额头,都像泥巴捏出来的。童世杰摇头晃脑,他不会唱歌,却跟着瞎哼哼,跟着尤清园用筷子敲碗边。卫安发现自己同样的笨拙,比童世杰好不到哪里去。至少,童世杰还能做出一种摇头晃脑的滑稽相,而他卫安,也许是当班副、班长的当惯了,当出了一小点矜持的“班僚主义”,在表现真情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的场合,连怎么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也退化了。加上底下奇痒奇痛,他身如木头,只会跟着敲碗边。小缪一边流泪,一边继续唱:
呵,爸爸,呵,妈妈,
你们对我说……
他唱得全身发抖。到这个分上,卫安的泪水也没有忍住。每唱完一句,尤清园都加上一句“妈唷”,好像旧戏舞台上的伴唱。他的骂声、小缪的歌声和三个兵的敲碗声,在狭窄低矮的坑洞过道里响着,和烛苗一起颤抖。这些声音不会从那进气孔里传到地面上,它将永远留在这地底下。卫安相信声音是可以渗进泥土中去的,泥土吸收这些声音,就像他们呼吸空气一样。
缪云棠的歌刚唱完,尤清园说:“本来应该我们先唱的。但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俗话:‘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今天我们在战场上,就依照战场规矩了。两位,哨长,童老兵,会唱《祝你生日快乐》吗?不会?真不会?那好,小缪,我就代表他们两个唱。好吗?两位同意吗?那我就唱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什么歌啊?国产的吗?就这么一句话?”童世杰捧起开水杯,大叫一声,“那我也会唱!为小缪的生日,也为我们的第二个生日,干杯!”接着他吼叫似的唱了起来,“好酒!好酒!好酒!……”
这是一首流行歌曲,他只唱这一句,别的也不会唱。于是,他们都端起了那碗开水,都吼唱这一句:“好酒!好酒!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