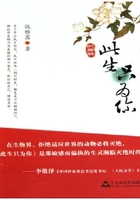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9号哨位]
到9点38分,侯春茂洗好澡了。而在晚饭前,他居然睡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好觉,约有四十分钟。洗澡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长。天然淋浴,战场是一个巨大的“天湢”,太妙了!侯春茂也是带了香皂的。在背包里埋伏几块香皂,感觉不到什么重量,用不上,丢掉也不算可惜。如今到底用上了。打过香皂洗过澡的身体滑滑溜溜的,下雨第一天洗净的军衣也有一股潮而凉的香皂味。这样死去,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陌生的世界,比给他一百枚功勋章更好。这不是他有什么酸葡萄心理,担心得不到勋章而在事先贬低它的价值。他只是说,他不是因为想得到功勋章或得到“英雄”的称谓才上战场的。
“你可以到里面休息一会儿。”侯春茂对马中济哨长说。“打响了再出来。”
马中济放下冲锋枪,一声不响地往底下的洞子里倒钻,好像缩进地底深处去了。这时,侯春茂往“我们这些指挥员才有”的手枪里推上子弹,关上保险,放在洞口的地上。自从拥有这把手枪,在几次实弹射击中,子弹没有一发上过半身靶,全都不翼而飞,不知所“中”。打机枪也是这样,每次都是“吃鸭蛋”。不过,使用半自动步枪,卧姿状态,他是一枪一个准,枪枪十环。连长韩延庆帮他查找原因,发现他的心理素质不太好!侯春茂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是的”。他不愿和连长争辩。有几次,侯春茂很想对连长说,我有你曾经有过的那么多训练时间,你看我能不能在二十米开外用手枪击中你的心脏,说打你的“二尖瓣”,决不会打到“三尖瓣”--连长先生大概连“三尖瓣”在哪里也不知道吧?--眼下的事实是侯春茂确实还没有完全掌握打手枪的要领和所需要的心理素质。不过,也不必担忧。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老话了。有一个倒霉蛋撞在他侯春茂的手枪枪口上,那也说不定。
之所以把马中济支走,一是因为看样子需要他动用一下阵地长也就是排长的官员身份了,二是因为他想一个人坐一会儿。
在别人以为寂寞的独坐中,侯春茂本人并不觉得孤寂。孤独感完全是一种因人而异的感觉。有的人还因为能够孤独而高兴呢,比如我们的先哲推崇“慎独”,比如关存道宁肯“守独”,比如我侯春茂偏向“思独”,比如某个叫花子喜欢在桥洞里“乞独”……最近几天来,侯春茂不大想吃饭,也不大想睡觉,可他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到的声音。他相信他是听到了的。
这便是侯春茂的缺陷,他清楚。曾经有两个女同学爱过他。并非他自作多情,老往好事上联系,梦想拜堂。他原先真切地听到了她俩的心声,正如他后来毫不怀疑听到了她俩心中的变音。她俩相貌平平,人却聪明伶俐。其中一个,只有不满两个月的交往。她是一只没有脑袋的金蝇,而她以为掌握了当今最有意义的真理。把民主自由和爱情牵扯到一起是侯春茂不敢领教的。他慢条斯理地用他的专业知识告诉她,一只雄蜘蛛可以为了一次求爱而甘愿被雌蜘蛛吃掉,他就是这样的雄蜘蛛,可你不要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她说他没有社会责任心,气鼓鼓地把他和她的爱情抛弃了。一个星期后,她约他到某公园细谈。这时她颓丧地穿着那件曾让她非常高傲的紫红色羽绒衣。他说,我们不用谈了,在这个星期里,你两次举起了雌蜘蛛的双腿(这表示拒绝)。她说他侮辱了她--因为她不是雌蜘蛛这类低等动物。现在她在哪里高就,他无暇打听更无意打听。
另一位就在几天后填空了。难怪,填空题是中小学生们的基本作业题。她笑起来,丰润的脸颊直颤动,常使他异想天开地要伸出手去接住可能在她笑时掉落的脸颊。她长得很丰满,数度在游泳池里向他展示那两条肉滚滚的大腿。搂着她跳舞,就像搂着一堆肉似的。他不大在乎女性的胖瘦。兴许,胖女人更像温软厚实的席梦思,而瘦女人可能是折磨男人骨头的竹榻。侯春茂爱的是她不大喜欢说话。在他们互不开口的时候,他们最融洽。可是有一天,她突然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再有两个月,他们就要大学毕业,选择恋爱对象成为选择工作去向的一个重要参酌要素--为了找到合适的饭碗,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大学生活中的恋爱对象必须无情地抛弃!这正应了一首小诗:爱情很有趣,思想更重要;若为饭碗故,一切皆可抛!
“是不是你另外有人了?”她问。这是她低着头温情脉脉地问出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优雅,新颖,深刻,喜欢探讨人类生存问题的本质,路人以为我们正在心无旁骛地准备毕业论文,殊不知我们正在爱河的危岸边徘徊。“你是不是另外有人了?”这问题太愚蠢了。侯春茂对她的智商产生了疑问。连这一点你都要怀疑,你还能和哪个男人谈恋爱?
以后侯春茂再也没有谈过恋爱,直到与欢欢相识。他发觉,除了欢欢,谁都同他说过假话。侯春茂总能在语言的声调底下听到凉飕飕的真实,那真实的虚假或虚假的真实,由不得他,也好像由不得别人。
这两天侯春茂很疲乏,肌肉的活力仅在刚才的洗澡中似乎有所显现。有一天他问欢欢你怕不怕离开你的父母,欢欢挑起眉毛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把一块石子掷进流速不为不快的山溪中。那块石子居然连一朵水花也没有激起来。这时候夕阳正坐于暗绿近于泼墨的山林,林梢顶着蔼蔼暮云,依稀的轻岚浮游在他们的脑袋上空。在他们前头的浅溪里,有三个女性试图不脱鞋子过溪。这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人的三个时期:老年、中年和青年。溪里有几块平时用来蹬踏的黑石。最先跳过去的是那个老妇。接着,头上盘着一圈黑布,脚穿军用胶鞋的中年妇女跳了过去。在这中年妇女过去的时候,那块石头动了。于是后面那个姑娘一时失去跳跃的勇气。由于他们在这边望着,她们显得挺活跃,中年妇女不时向他们投来快活的一瞥,银发缁衣的老妇人把双手挽在衣襟下,姑娘的脸涨得绯红。她们在那里折腾了足有十分钟,最后是老妇人从溪边搬来一块石头,又由中年妇女把它垫在踏脚的黑石上,那姑娘才跳了过去。天黑了下来,侯春茂和欢欢抽着香烟,走向他们临时栖身的简易营房。
在倪欢欢被抬下阵地的那天晚上,侯春茂和马哨长坐在洞口。侯春茂忽然看到欢欢的影子出现在面前,他的一只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把药包递过来。他说:“排长,我请个假。”侯春茂的眼睛问他:“你想去哪里?”他说:“我想回家。”当侯春茂想说“不行”的时候,欢欢的身影消失了。侯春茂看得非常清楚,欢欢确实来了。当时侯春茂看了手表。侯春茂对马中济说:“欢欢牺牲了。”马中济不相信。后来连长在电话上告诉侯春茂,欢欢牺牲在半路上,那正是侯春茂看手表的时间。
连日来,在坐卧无常的冥想里,侯春茂在万籁中听到喧嚣的寂静。那寂静的林啸、风动、雨飘,有时天空裂开一条缝,露出一弯苍白的小月,炮弹制造的水坑亮晶晶的,夜虫在风停雨歇后低吟浅唱,潮闷在深夜里为清凉所稀释……侯春茂感到痛苦的是他追不到欢欢的踪影。欢欢没有死,但侯春茂见不到。欢欢是这空气,是这石洞,是这大地……
好了,现在侯春茂可以勇敢地面对战斗了。他已用香皂洗净了身上的污垢。假如还有什么能让他痛苦的话,就是还要他一遍又一遍地洗澡,并且要他肯定:这就是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