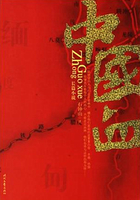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连部]
他吸走了整朵烛苗,山洞没入黑暗。申体心以为蜡烛就这样熄灭了,可是烛苗从烟卷头上滑了出来,凛凛地颤抖。过了一会儿,韩延庆张开的大嘴里才冒出一股浓烟。烛光里,韩延庆脸呈紫色,像上了一层釉彩。他盯视着烛苗,烛苗在他的瞳孔里像两点黑暗旷野里的磷火,阴森森地闪烁。洞外响着令人提心吊胆的雨声,这声音从波纹钢的缝隙里渗透进来,听着有点喑哑。一只早就等在那儿的手接去了韩延庆的蜡烛。
“走吧。”韩延庆说。
“九点半了。”申体心用食指敲一下手表。
“我们可以下到第一枪打响。”
烛光暗淡。洞里只点了一支蜡烛,放在申体心铺边的弹药箱上。烛光潮湿得可以拧出水来。韩延庆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棋盘,仿佛除了象棋以外什么都不想。他的五个小卒都过了河。他把它们摆得端端正正,使“卒”字的上面一点都冲着申体心的这一方,像要督促它们用脑袋来冲撞阵地。申体心也把帅棋拨正,让这位老兄稳坐在中军帐。“走啊。”韩延庆催促。申体心把顶着小卒的炮移到边线,这是一着不能不避让的软棋。
申体心和韩延庆的棋艺不相上下。以前在营房里,为了一争输赢,他们经常在星期六的那天晚上弈棋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可现在是在战场上,再过个把小时,对面那一个营的兵力就将扑上他们的阵地。这个情报到此刻还没有被新的上级来电否定。
“你是不想谈看法了?”韩延庆说。
“谈什么?象棋,战争,还是马上就要展开的战斗?”申体心说。
“嗯?”韩延庆的目光由下向上抬起来,但额上没有抬头纹--到底是年轻人啊。“你任选一点吧。”他又凝视棋盘,“是不是不想谈?”
申体心是不想谈。“等这场战斗结束了再谈吧。”
“如果你想从从容容地谈,那我也不勉强。不过……”他摸着车棋,提到半空中,“打仗不是下棋这样的智力游戏。战斗一旦打响,很多事儿就由不得我们指挥员了。”他把车向前推进了一步,占据申体心的河口,预先保护一个孤立的卒。“以前老是觉得,打仗就是捉对儿厮杀。现在想想真幼稚。”
“这想法不幼稚啊。”申体心说,“你是不是陷入天人交战了?”
“什么?呵,我能相信你的这一看法吗?”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法。”
“原来这样。”韩延庆说,“喂,小文。”他的眼睛仍然望着棋盘。“你多准备一点蜡烛,放在你容易摸到的地方。等会儿一打炮,蜡烛是站不稳的。今晚会打很多炮。”
“我已经准备了。”小文在申体心背后说。
韩延庆的眼珠往小文那边动了动,但目光没离棋盘。“很好。”他说。
申体心确实没有看法可谈,他觉得,从军事指挥员的心理素质上讲,韩延庆还远远谈不上成熟。逼着他申体心在战前时刻这样下棋,于一个戎马倥偬的大将军,不失为一种风格的表现,而对一个驭剑未几的小军官,则难掩其焦虑与不安。甚且,韩延庆受到干扰却不能迅速将其排除。也许他女朋友(还不是未婚妻)信上的一两句话伤了他的心。比如她说:“我讨厌你对战争的那股狂热劲儿……在信上,除了战争,你就不能写点儿别的什么吗?”晚饭前,他们穿上了多日不穿的军衣:一方面,今天有点儿凉;另一方面,等一会儿打起来,很可能需要冲出洞去。你总不能光着身子拿着枪往外冲啊!--申体心不想探究连长女友的那些话。申体心没有研究过战争史,但他可断定,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全体国人无一例外地支持同一场战争。在这边境上倒有一绝,“鸡蛋串着卖”。可你不能用一种思想或一个观点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串起来。那太简单化了。对那些,想都不要去想。职业军人当如是。就此而言,韩延庆毕竟还太年轻了一点儿。
申体心跳了一步马,钳制韩延庆的两个卒。
“又是这种死皮赖脸的战术。”韩延庆说。
“没错,我就这样死皮赖脸了。”申体心穿上胶鞋,披上雨衣。韩延庆埋头在棋盘上,哪儿也不望。小文移开遮挡洞口的波纹钢。申体心最不愿意在山洞里对着空罐头盒便溺,只要有一点点安全的保障,总要跑到洞外去。钢板移开,申体心身边的烛光就开始局促地跳动,而在他脸上,马上有雨风凉爽地吹拂。
外面很黑。申体心能感觉到黑暗在沙沙的雨声里一浪一浪地涌来。雨不是很大。看不到雨丝,只听到无动于衷的飘洒击打声。申体心拉下斗篷,掩住额头,腰猫得很低,并不向远处望,一头钻进雨夜的阴黑中。他雨衣上的黑胶瞥着倒有一点儿微弱的明色。
后面咔的一声,是冲锋枪解除了保险。有人跟出来,在离申体心两米多远的地方站住。黑暗在四周侵浃着他,可这黑暗又是那样空洞而不可靠。他久久解不出小便,回头一瞥,小文站在那儿,雨衣的襟缝中伸出冲锋枪的枪头。小文是怕连首长遭到不测,申体心也仿佛觉得黑暗中眨着一些诡秘的眼睛,可是一股无名火还是在他心中颤动。“你进去吧。”申体心说。他又不是犯人,连解小便的自由都没有。小文走了,仅仅退到洞口下。通信员还会在那里横着警惕的枪口,申体心知道,但他的心里多少觉得宽松了一点儿。
申体心也知道--现在更知道--黑暗能够把遥远的距离缩短,把一切看不到的事物非常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韩延庆就看到,小女孩独自睡在小床上,盖着一条橘黄的毛巾被,而隔壁那张大床却空着……房间里没有人,衣衾随意摊放着,坐灯拧得很暗。狭窄的阳台上,月光迷离而凄清,夜来香悄悄展开素白的花瓣,从那隐秘的花蕊深处吐出一丝撩动人心的幽香……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透过黑暗,韩延庆似乎看到那一营敌军正在雨中集结。风雨在加大,虽然不太明显。密集的小雨点反而使这阵地上的黑暗显得空寂,仿佛把什么有用的东西挤到了空间以外,徒留一个凝固的不生不灭的时间,让人等待,让人准备。
回到洞口时,申体心在小文脸上看到一丝模糊的委屈。也许小文觉得他们这些连队小军官不大好侍候吧?这样伤害小文不止一次了。申体心可以表示一点安慰,但他觉得这很无聊,毫无意义,而且没有保证。
还不到半夜,洞里似乎就涌入了迷茫的白雾。烛苗远远地向申体心展现一点隐约的生机,它像悬在夜的云海上的那盏古寺枯灯。当申体心走进去,这种感觉消失了。他看到连长在棋盘上埋着头,手指夹着才接上的香烟。
“继续下棋?”
“为什么不下?”韩延庆说,“我在想,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战士们钻出山洞追打!”他捺住一个卒子,等申体心坐下。
申体心笑了笑。“前提是你早几天就该下达命令,把那些埋在阵地上的地雷和爆炸性障碍物清除掉!”这话有点挖苦人。可你连这种隐语都不说,就难让连长冷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