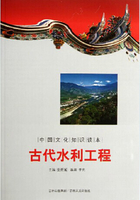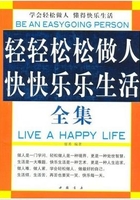[15号哨位]
雨一下大,米开广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好了。他们四个人伏在洞口,米开广最靠前。长袖军衣都穿好了,胶鞋带子都系紧了,钢盔都戴在头上了。在这之前,蓝文定和任宠把家信烧掉了。顾家荣对父母的信原是收一封撕一封,没有什么好烧的。米开广不想烧家信,一来他觉得这过分悲壮,二来他的家信都很短,没有任何不能公之于世的秘密。九点半,他们就这样趴着,几乎每十分钟抽一支烟。这是蓝文定老家寄来的烟。他们身后那个和敌军相通的洞子,米开广在下午下去过,设置了一个雷阵。他们估计了两种可能。假如敌军想从后面掏他们,先得让他们尝尝地雷的滋味。地雷一响,他们也可以对付。如果敌军从前面攻进来,他们就跳雷阵。他们不想在火焰喷射器下挣扎,在很长的时间里化为木炭,宁可用自己埋设的地雷痛痛快快地了结。蓝文定说:“不能这样白死了。我们就做四壮士,好让以后的人拍电影。”米开广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做过生意的人,有些方面就显得脑子灵活一点。
地底下传来隐隐的雷声,余音很长,老觉得它要停了,却总是隆隆地响。天上打雷,地下响雷,不知是不是战场的特点。雨在洞外有滋有味地下着。米开广活了这么些年,还没有这样留心过夜雨。蓝文定说:“我那位也在牢房里的哥们,每个月能保证分到两包烟。这是乙级烟。比较差的烟,他们随便可以买。我每次去看他,都给他带上……”
“别说了。”米开广说。前方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来了。”他提醒。
“真来了?”蓝文定说。
任宠在那里扭了起来,终于在两只手掌当中弄出一声咳嗽。还是顾家荣表现很好,不动也不说。
米开广目测了一下距离,那两个兵影离他们不过八米。他想到这一会儿可能有很多敌人摸了上来,但整个阵地还是只能听到温柔的夜雨声。别的哨位都还没有发现敌军吗?在那么突地一下里,米开广的心从胸腔跳到了耳朵里。他连声叫自己冷静!冷静!冷静!可他的心脏在耳朵里装怪。冲锋枪的保险早就打开了,他的食指碰到扳机,发现这指头麻得厉害。那两个敌兵在向他们靠近,他盯住他俩的脚。现在是七米。现在是六米。现在是五米。看着敌兵出现在鼻尖前,是他的首次体验。打还是不打,要不要开枪?他犹豫不决,因为他想,敌兵还没有发现他们这个哨位。他叫自己冷静,可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耳朵让他的心脏占领了。
五米,简直太近了。在敌兵眼里,他们这洞口大概是一团黑影,和别的黑影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黑影,在这阵地上遍地都是。这两个敌兵,保持五至七步的间距。米开广瞄准了前面的一个。他的枪口朝上。他们这个山洞是前高后低,因此他虽然不大看得清标尺的缺口,却能清晰地见到枪头上的准星和保护准星的圆环。他心里暗暗怀着一种希望,洞前的地雷或爆炸性障碍物会发挥作用,不需要他们开枪。连首长告诫他们,他们是守山洞,机动余地几乎没有,能不开枪就不要开枪,以免暴露位置,被动挨打。可是,敌兵离他们太近了,太近了。敌兵的枪口好像顶着他们的身体。闭着眼睛,米开广也能撩倒一个。他盯着前面那个敌兵继续往右边移动,走出他的射界,消失不见。米开广把敌兵放过去了。
现在米开广的前方只有一个敌兵了。看来他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洞口,在跟着往右移动的同时,往米开广的枪口上翘。敌兵的脸朝着米开广的左方,米开广看得很清楚。在潇潇的雨声里,米开广觉得听到了敌兵的喘息声。他猫着腰,紧握着和米开广一样的冲锋枪。四米,只有四米了,可能四米还不到。这一枪最好别让我来打,如果一定要把他打死的话。米开广忽然记得他是炸伤或至少炸死过两个敌兵的,那晚上他没有看到敌影,他是根据声音引爆炸弹和地雷的。近在咫尺的这个兵,这个人,正在撕扯米开广的心。他的心在耳朵里猛烈地跳动。他暗暗催促敌兵快点儿往右走,走出他的枪口。就在这时,米开广的右边响起一声枪声。听到枪响,眼前的这个敌兵敏捷地成为跪姿--右膝着地,左腿弓步。与此同时,脸和枪口迅速转向他们的洞口。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兵,米开广想到。在敌兵好像要开枪之前,米开广的枪自动打响。真的,他没有想到要开枪,可他的枪自动击发了。他的身体在枪的后座力作用下震动,耳朵被心脏塞满,而且火辣辣的。同时他看到,他打出的第一发子弹就把敌兵击中了,就像打保龄球似的--他虽然没打过保龄球,可在电视上看过,子弹一下就推倒了那个敌兵。他的子弹打出去一梭子,至少有十发子弹,除去第一发,都打向温柔而热情的夜雨。到底打中多少条雨丝,他不得而知,但打中了多条雨丝,是可以断定的。他还看到最后一发子弹,由于受到密集雨丝的阻拦,慢慢地向下坠落,落入一片灌木丛,打歪并且打碎了多片树叶,然后很不甘心地擩入一个小蛇洞,击中一只在蛇洞中觅食的蚂蚁……
在他那样想着时,炮弹下来了。炮弹首先引爆了阵地上的爆炸性障碍物,引起强烈的爆炸声和一声声凄厉的哭叫。这声音好像封存在地狱里,现在炮弹把地狱的大门轰开了,于是这声音一齐释放,地面上只有这种撕心裂胆的声音了。不过他也看到,现在雨下得很大。在炮弹一闪一闪的红光里,粗粗的雨条也一闪一闪的。米开广看到被他击毙的那个敌兵,原来滚到了三十几米外的远处,现在不时被炮弹的气浪所掀动,石子、泥土或者还有弹片纷纷落在他的身上。火药味浓重得令人窒息。山洞好像一只带篷小船,在炮弹的狂风巨浪中颠簸,即使他们趴在舱底,也觉得随时可能滚到船外去,且连这只小船都会随时炸成碎片。耳朵简直疼得受不了。在第一阵炮弹落下时,他从洞口往后退,退到机枪后面。他也是重机枪射手。对此,巨大的爆炸声并没有把他震得忘掉。
洞口落下了一件东西,是炮弹头,它穿透了波纹钢。刹那间米开广觉得他们四个兵都完了,炸塌的洞口会把他们很好地埋起来。他闭上眼睛,准备化为肉酱。然而,几秒钟过去了,炮弹没有爆炸。他睁开眼睛,见它乖乖地躺在那里,好像熟睡的胖娃娃。“是发哑炮!”米开广大叫。兴奋使他全身着火似的发热。无论老天的安排如何,是叫米开广多经受一些时间的磨难还是别的意思,他都乐于接受。去他娘的,老子玩上了,反正小命不值钱,就当爹妈没生我,世上从来没有我这么一个人。
米开广抱住重机枪就吼:“你们往后退,我一个人就够了。我的重机枪一响,就是敌军进洞了,你们就跳!”他没有望哨员们,他只感觉到他们三个往后退。退到最后就是那个地雷阵。实际上他们没有退路。
风雨哗哗地在红光里沸腾。弹片连同泥石向空中迸飞,烟尘滚滚,气浪一阵一阵地涌进洞里。米开广眼睛模糊,觉得整个世界在崩裂、毁坏、坍塌,而他不知怎么地就看到了父母的面孔,他们依然挂着慈祥的笑容。这时候洞前落下几发重炮,把那个由他打死的敌兵像一个稻草捆似的抛起来,随后是无数的泥石,好像那天空的碎片,血红血红地,跟着雨点往下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