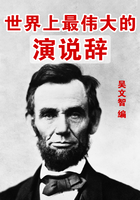[连部]
这样躺着,一动不能动,就像抽了脑脊髓以后必须平躺六个小时,弄得文幼浑身骨头酸痛。汗水呢,又流个不停。醒是早就醒了,可他们在商量这么重要的事,文幼想还是假装睡着好。他感觉到每一颗汗珠是怎样在身上爬,又怎样渗入身下的棉被中。现在他身下的棉被几乎被汗水溻湿了,不仅湿,而且黏,就像睡在胶水上。这时候就听到罐头盒倾倒的声音。
“怎么搞的?”连长说。
文幼的眼皮忍不住动了几下。小苗又闯祸了。“咕咕咕”,白母鸡也在说。
小苗也真是的。文幼想,现在可以起来了,这样躺着全身骨头痛。
苗青在拧那块湿棉被。他也是倒霉透了,怎么把水洒在连长的棉被中间。那只烧开水的空罐头盒放在石子地上,冒着几丝热气。他的脸红得出血,嘴唇一瘪一瘪的。连长勾着头站在电话机旁边,那只话筒上还粘着他的汗。文幼从汗水里滚出来,两只脚又轻又慢地从铺上横下去踏在胶鞋上。指导员扭着脸,也望着。
“你早就醒了吧?”指导员说。不,是他的眼睛在这么说,可文幼觉得他把这句话说出了口。
有人很快就要死了,文幼想。关存道一出手,非要了对方一个兵的命!然后呢,对方非要了我们的一个兵的命……
他很快站起来。走过小苗身边,他捡起了空罐头盒。他瞥见指导员手指上的香烟灰落在自己的铺位上。连长的一只脚踏着弹药箱。
“一排长和三排长都不错。”连长说。
文幼觉得指导员在望着他的光屁股。文幼有点不明白,他们现在都是赤裸裸的没有穿衣服,为什么还这样望着他?不管他们商量什么,文幼都没有听到。他什么也不会同别人去说,哪怕打死他。这是当连部兵的基本要求。文幼自当连部兵的那天起,就得到了这样的告知。大家一样光着身子,就没有什么可瞧的了,对吗?
“那时我就不想要这个人。”连长说。文幼知道他说的是二排长侯春茂。二排长的文化太高了,想法和做法同他们不一样。但文幼想,他不会对别人说。
指导员假咳了两声。连长扭头看后面的小苗。指导员挺起眉毛对连长望了一眼。文幼拿着做饭的压缩饼干箱钻进小壁洞,听见连长说:“不要再拧了。”文幼真想到哪里去弄一只铁锅来。铁锅可以长期做饭。这岩壁上的石洞很小,睡不下一个人,只放着主副食品和一些杂物。这石洞再大一点儿,可能会允许他睡在这里。他感觉到身上的骨头还在酸痛,想活动一下,可这里站也站不直。小石洞,你怎么没有长大一点儿呢?你变成石洞的时候是可以变得大一点儿的呀。这里空气闷热,可能宽人心胸。文幼的汗珠滴在米口袋上,同时觉得解口袋绳的指尖隐隐发麻。绳子还没有解开,口袋就往一边歪。他用膝盖把米袋顶住,它还歪。他把做饭的压缩饼干箱搁好,猛力地推动米袋,又把它猛地拉回来,狠狠地把它扶正,捶了它两拳。如果小壁洞大一点,文幼一定睡到这里面来。“小石洞,我很喜欢你,知道吗?”他心里说。它会懂得他的意思。他能感觉它很想让他在它里面睡。文幼不止十次地想过,最好从哪里去弄一只铁锅来。这只压缩饼干箱再做几天饭就得换一只新的了。
小苗钻进石洞,帮文幼扶住饼干箱。苗青的脸发紫,嘴唇一瘪一瘪的,眼睫毛上挂着汗珠儿。文幼碰了一下他的手。他把饼干箱拿起来,凑近文幼的手。既然他不懂其中的意思,文幼也不想再说。其实文幼早就对苗青说过:“我们做事小心一点儿。”苗青的嘴唇不该这么一瘪一瘪的。文幼现在想到的是,有的人快死了,只是文幼还不知道快要死去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只有一点水了。”小苗说,“淘了米,就没水做饭了。”
我知道,文幼想。可是你的嘴不要这么一瘪一瘪的了。他俩钻出小壁洞,苗青在前,文幼在后。
“是不是没有水了?”连长问,望望水桶。指导员叼着烟蒂,埋头搓着胳膊上的汗垢。这是指导员的习惯,这不是个好习惯。“小苗。”连长说。
“到!”小苗说。
“你到军工班去要一点水来。他们可能还有水,不论多少要一点。”连长说,望着电话机的话筒。那话筒上粘着他的汗珠,一下子干不了。小苗的嘴不再一瘪一瘪的,他的眼里渐渐放出受宠的光彩。“顺便通知他们班长,明天给各哨位送水。从现在开始,阵地解除封闭,但夜间照常。你去吧。”
“是。”小苗说。他拿着空水桶,很快就走了。他跑步的速度比文幼快。文幼想提醒他,最好带上冲锋枪,但连长和指导员没有说,大概不需要吧。
“那就这么定了。”连长说,“明天打第一枪。”
白母鸡的尖嘴巴啄着指导员的掌心。她昨天在这里下了一个蛋。这个蛋飞到空中爆炸,有的人就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