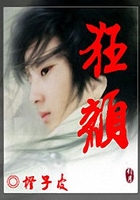[7号哨位]
眼睛移近观察孔,这感觉就像在古墓中窥望人间。如有重炮的炮弹在观察孔上方爆炸,那就不用再挖坟墓了。头上这层山土经不起几发炮弹的轰击,而观察孔背后的空间比一般的群葬墓穴大不了多少。随着夜的加深,洞里冷幽幽、阴森森的,它催人入睡。三天三夜了,全阵地上的人,能够多少睡着一会儿的,会有几个呢?他有点想不通,上阵地见习的那个星期,他每天都睡得好好的;等到自己的哨员上来,他反而睡不着了。是受到新哨员的感染和影响吗,是突然降落的责任让他紧张了吗?现在,卫安真想好好睡它一大觉。就算有一种弹弓能弹开他的眼皮,他也会睡着的,卫安想。
从观察孔望出去,只能望到清冽星光下的那棵冒烟的树。上阵地头一天,他就看到这棵树在冒烟。它横在山坡上,挺粗的那些枝杈可能在树还没被炸倒之前就让弹片卸掉,而今只剩一段树干。它很像一个仰躺的人,但死了,紧贴泥土的背部可能已经在腐烂,那些性喜潮湿阴暗的小虫肯定钻进了它的肌肉,正在里面津津有味地嚼食,可以在这危机重重的寂静里听到小虫啃吃木肉的声音,像狗啃骨头一样,咔吧咔吧地响。要不然,还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呢?一缕青烟从树疙瘩里吐出来,细且淡,像人嘴里舒缓吐出的烟。卫安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再取出一支,叫声“喂”,把它递给童世杰。他们不说话,各用自己的火柴点烟,藏在观察孔下,双手捂住火光。一值班就是半夜,不抽一支烟提一提神,那是做不到的。淡如寒冰的星光下,那缕青烟袅袅而起,下部笔直,由细而粗,开始粗得不大明显,渐往上,烟子出现弯曲,在弯曲的同时呈现膨胀、松散的趋势,分成几小缕以后,又不时汇拢、交叉、拧合,在这过程中继续颤动着上升,顶上显出永远消失前的变淡和散开。有时气流不匀,那缕烟凛凛抖晃。在一阵草木的摇曳声里,它简直就不见了,像被一下子抹去,但风声响过,它忽地摇现,稳定下来,淡淡的,细细的,缥缈在月光里,而月光又是那么凄清、迷离、模糊,好像垂亡老人的目光,处在惺忪的睡意里。你不要不信,任何物体都会有睡意。卫安打了一个哈欠。这哈欠打得呀,嘴巴张得过大,好久合不拢,牙环骨那里一阵酸痛,眼泪流下来一长串。
除了那冒烟的树,观察孔里再也看不到更多的。视界这样狭窄,最好叫它“倾听孔”。事实上,他们也是靠耳朵来观察夜间的敌情。敌人随时可能摸上来,每一个响动里都隐伏着不安与危机。现在他和童世杰值双岗。他们的四只耳朵,不能有一只耳朵睡觉。他把一条电话线拴在童世杰的手腕上,每隔五分钟拉一次,防止童世杰睡着。不叫童世杰值班的时候,他那紧张昂奋的神经得不到抑制,而在观察孔里望久了却什么也望不到,就会不知不觉地睡着。想不通的是几年中轮番来这里的士兵就缩在这样的观察孔后面,出也不出去,望也望不到,打也不能打,守也不能守,究竟都想过些什么?
童世杰坐在弹药箱上睡着了,打起鼾来。几天不能入睡,也该让他睡一会儿了吧?可不行,万一我也睡着了,怎么办?卫安拉胶皮线。一拉,没有反应;再一拉,还是没有反应;猛地一拉,黑乎乎的人影动了一下,鼾声却没有被拉断。这家伙,现在终于睡着了。他也想睡啊。他的警惕性已经瞌睡懵懂,紧绷的神经已经在高强度的紧张里疲软了,就像蹄筋在水里泡得时间久了。可是不行啊不行。这场防御战还得靠耳朵来打。卫安使劲拉了一下胶皮线。人被拉动了,傍着波纹钢,毫无抵拒地倒下,一声不响,倒在地上,发出一个咂嘴声,反而睡得更酣了。所以嘛,除了他这哨长,谁也不想和童世杰值同一个夜班。童世杰想睡就会睡,他不管你那么多,他事后总有话说。你不会胡搅蛮缠,他会。胶皮线拉不断他的睡梦。这已经是第四次。前三次拉了还能醒,这一次,看来要在他的脑袋上想点办法了。
卫安在观察孔上听了一会儿。暂时没有敌情。他放下枪,在塑料桶里舀了一碗凉水。童世杰蜷缩在地上,嘴巴贴着波纹钢,冲锋枪的枪头部分睡在他的大腿上。卫安把他的脸扳过来,对准额头和囟顶,将冷水猛地泼下去。童世杰“啊”了一声,脑袋昂起来,摇落那些水珠,接着到处摸他的枪。等把枪摸着,他问:“在哪里,在哪里?”
“在你的床上!在哪里……”
他望望卫安。在黑暗中,那眼睛睁得比牛眼睛还大。“对不起,哨长。”
“我倒没什么。你会害得大家跟着你死。”
“实在太瞌睡了。”童世杰抹着下巴。可能在瞌睡时,下巴上淌着不少口水。对于他额上的水珠,他倒不怎么在意。他摸着弹药箱,坐了上去。“好想睡啊,眼睛一点也睁不开。”他在那里摸口袋,什么也没有摸着,猫腰走了过来,“再给支香烟,哨长。请你不要生气。嘿嘿,要是你能让我睡一会儿,你就是一位最好的哨长。到时评功评奖,我保证投你一票……”
火柴的红光里,他的眼睛眯得很细。卫安怀疑,上阵地前,他那口袋里的二十元钱不翼而飞,恐怕和童世杰有关。但卫安不想戳穿。戳穿了,饱以老拳?凭拳头,卫安自知不是童世杰的对手,再说了,还须在这战场上共同战斗,向他背后开黑枪,那就死得不明不白了,卫安默默地想。童世杰大口抽烟,拍着脑袋。“头好疼啊。太想睡了……”
“熬一熬。再熬两个小时,到凌晨五点半,我让你睡。”
“好。两个小时,我能坚持。我还不至于那么熊。”童世杰说。他伸头去撞波纹钢,笃,笃,笃!洞顶那么低,他蹲着,只要往上耸一点儿身子,头就撞着波纹钢。笃!他一头撞着。笃!这下更结实。笃,笃,笃!真怕他顶穿了波纹钢,顶穿了罩在头上的山。“叫你睡!”他说着,“看你还睡不睡?”笃!笃!笃!
“别折磨自己了。”卫安说。至少是这一刻,他相信童世杰的表现是真实的,童世杰三天三夜没有睡了,到此刻,瞌睡的魔鬼已经可以轻易俘虏他了。卫安有点后悔,不该用冷水把童世杰泼醒。毕竟,有一个兵醒着值岗,也是够了的。刚上阵地,上级要求值双岗。再过一段时间,还不改作一兵一岗?要不然,仅仅坐岗,就把兵们坐死了。
传来一个罐头盒的滚动声。卫安迷迷瞪瞪地把耳朵贴在观察孔上,听有没有人的脚步声。那些老鼠经常把罐头盒踢得四下滚。在这时,卫安觉得童世杰不吭气了,转颈四望,黑乎乎地就见一尊泥菩萨歪在他的怀里,一刹时躲闪不及,卫安的额头被他重重地撞着,眼前金星飞舞。童世杰倒在卫安身上,立即散了架,手臂掉了,腿断了,躯体变成一捆棉花,瞬间发出呼噜。这呼噜还绝了,一声“呜”,一声“呵”,一声“啊”,一声“哗”,一声“唷”,一声“嘿”,声声不同,一声高于一声,逐渐地,一会儿如同雌猫叫春,一会儿如同野狗嚎寒,一会儿更如鬼哭狼嚎……推他,推不醒;摇他,摇不醒。拴在他手腕上的胶皮线还在,绕住了他的手臂,然而那已不可能把他从睡眠的深渊里拉上来。卫安鼓足睡意沉沉的一点劲,把童世杰掀开。童世杰的脑袋撞在那边的波纹钢上,软酥酥地瘫下去。那鼾声断了片刻,在两个鼾声之间出现一个很像痰塞胸膛、又好像临死前咽气似的咕噜,接着就是连篇的鼾声,连篇的,一声接着一声,一声比一声甜蜜,好像一个醉鬼,倒在烂水田里,正好觉得清凉舒服,就躺在那里了。会不会出丑,会不会从此永远醒不过来,那就不管了。
还观察敌情呢。观察个屁!卫安很想运足全力,在童世杰身上踢几脚,可他的这只脚也睡着了,抬不起来。他发现,他的脚比他的脑袋更贪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