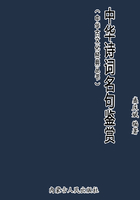提上我那只孤独的红皮箱,走。
……
丛 玫
1986年7月19日凌晨
三
早上八点差十分,新闻研究所第二室的调研员陆亚鸽走进研究所大楼。今天是周六,信息量最疲贻的时候,只是陆亚鸽已养成了准时上班的习惯,每天早早来,花一个小时加上上班后半小时碰头会的时间处理信件。他分管文教卫一摊子,此外,日报理论部专门为他辟了一个《反弹琵琶》的短论专栏,每周两篇。这个专栏开出后,报社每天都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车站码头,常常能听到市民议论《反弹琵琶》短小但攻击性强的话。市委一次开会前,市委书记突然问日报社长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舒:“你们那个《反弹琵琶》专栏笔者亚当,是新华社的还是社会科学院理论所的?”
他在楼梯口碰到满眼血丝的二室主任唐道理。
“亚鸽,文章昨天下午来电话找过你,要你一上班就给她回话。”
“没说什么事?”
“我没问,大概有什么线索。”
文章是本市《青年报》的年轻记者,亚鸽去报社讲课时认识的,以后就常来找亚鸽。去年亚鸽带她写了一系列关于人才封锁的报告文学,还为此打了几个漂亮官司。那些日子,这个城市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刮了一阵亚鸽文章风。
陆亚鸽拨通了《青年报》的电话。
“亚鸽是你?我找了你两天。我手里有一篇被枪毙的稿子。”
“什么内容?”
“N大学那个五岁大学生的事你知道吗?”
“名噪一时。”
“我的材料会告诉你那全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是那孩子是假的还是五岁上大学是假的?”
“问题比这更复杂。有关部门和人士在他身上做了不少文章。这个孩子现在戴着中国神童之最的桂冠,可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超常儿童,并没有上大学。”
“稿子为什么被毙了?”
“团市委书记是N大学原团委书记。他只对我们报社总编辑说了一句话:‘这篇稿子要慎重’,就给慎重掉了。”
陆亚鸽看看腕上的表,八点四十三分:“半小时后,我在‘居逸’等你,带上所有材料。”
繁华的江汉路还在做喧闹的夜生活的最后小憩。街上行人不多。“居逸”酒吧里,几个上晚白班的文职人员在慢条斯理地啜着牛奶可可。亚鸽走进外厅时,文章已经在那里了。
这是一个还没有被社会同化,被大量严格要求千篇一律的报道磨钝棱角的敏捷聪颖的大学生,亚鸽奇怪的是这位年轻纤丽的女同人的采访常常不像其他女性记者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一样,使用微笑和亲热的武器迫使采访对象就范,而是靠犀利的令人猝不及防的连珠炮似的提问,迅疾地划开对方的官样客套或下意识的敌视层,在采访对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触及到实质性问题的核心,这种挑衅性极强的采访,使她获得不少意外的成功,这使得年轻的她得意非常。但这种采访方式也常常使她陷入窘迫的境地,这个时候,她就会十分眼热亚鸽的采访风格:冷静淡泊的洞察力,合作者诚切的语言,鼓励采访对象充分自我表现的眼神,旗指中军之后围点打援,打草惊蛇尔后守株待兔。这在新闻采访学中被称作诱导式和主客交流式,其套路令文章叹为观止。
年轻纤丽的女记者毫不掩饰自己对亚鸽的钦佩,那钦佩中自然还有些别的什么。
亚鸽花二十分钟匆匆浏览了一下文章收集的背景材料和那篇被枪毙掉的稿子。作为一名退役的、有过五年晚报记者生涯的新闻工作者,亚鸽暗暗替文章叫绝。
一篇漂亮的报道。
“怎么样?亚鸽。”
文章从不爱皱眉头,她学不会这种深沉智雍的姿态。这次不知怎么了,看见陆亚鸽锁紧了眉心,她也不由得皱了皱光洁如镜的额头。
咖啡凉了,亚鸽用小勺去搅。
“说话呀,你。”
“起码,我需要一周时间。”
文章笑了,笑得清澈沁甜。
“亚鸽,提一个题外的问题,我觉得你太严格太冷漠。”
陆亚鸽抬头看这位年轻的伙伴。
“你太深奥,连喝咖啡都像个哲人。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你的程序里少了感情的编码。”
他把手伸出去,文章一愣。
“什么?”
“给我。”
“感情?”
“材料。我需要所有原始材料,要不我从哪儿开始干?”
一大包都塞过来。“全在这儿。你得感谢你的合作者,她有一手漂亮的行书。”大红提袋往肩上一甩。“行了,我先走,还有一个约会。我什么时候和你通话?我可不愿和唐道理在电话里聊天了,干巴拉渣的。”燕子式飞到门口,又转过头。“对啦,亚鸽,忘了一件重要事,这个星期天把朵朵借我用用。”
陆亚鸽用眼睛询问。
“到东湖看荷花。我一个人,太孤单。放心,又不是第一次,保证不损坏。明早我来接啊?”
眨一下眼,燕子飞走了。一包材料却实实在在沉睡在茶几上,很安静。
陆亚鸽点上一支烟。
下班时,路过王家巷码头水果摊,陆亚鸽给儿子买了几斤万县产的广柑。儿子喜欢把广柑当球踢,踢软了心,用针扎个小洞,吸奶一样吮得十分起劲。儿子没吃过人奶。“我把球吃了。”他总这么说。但真正的球他却没吃过。他有十二个球,正好一个班。
水果比肉还贵。一斤广柑两块一,最好的那种。陆亚鸽皱了皱眉头。
水果贩子很机灵:“这是地道川柑,剥开一层蜜,甜得很。你称多少?多称优惠!五斤怎么样?就五斤,我少算你的,两块一斤,赔就赔啦,算我交个朋友啦。”
陆亚鸽数出拾块零伍毛,盯着对方说:“我不要两块一斤的。”提着网兜走出好远,还感到背上水果贩子黏糊糊的疑惑。船到了,他得赶这班船过江,没法转回去向水果贩子解释,他给儿子买东西从来不买降价的。
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走完了,剩下几个孩子在跷跷板上心不在焉地玩。朵朵看见陆亚鸽,二话没说,抱起外套就往外走。那个很热心的小老师跟在后面说:“你孩子真逗,中午小朋友都睡了,他不睡,自己爬起来穿衣服,说要去找你。我说爸爸下班后会来接你的。他生气地喊: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他,他是我爸爸呀!”小老师说完不好意思地笑。
陆亚鸽十分抱歉地向老师赔不是,然后大步去追儿子。两个人走出幼儿园,走出好远都没说话。亚鸽偷偷看朵朵,朵朵很严肃地抱着外套在前面走。电影院散场了,人潮拥来,陆亚鸽快步赶上,并排走了一段,不时有人从后面把他们冲开。亚鸽悄悄伸出一个手指头,小心地向儿子靠拢。两个手指头碰上了、勾住了。不大好走,亚鸽得斜着身子。很快发现儿子在踮脚。手指勾成的链条开始摆动,摆出一大一小两条船的涟漪。又走出一段路,两人不约而同相视,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朵朵就把亚鸽的大手扬得很高,高声念:“摇呀摇,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不在家。”
“摇到姥姥家。”
“姥姥出远门儿。”
“外孙没人疼。”
突然站住了,看着天,说:“爸爸,云彩干吗红啦?”
“那是晚霞。”
“什么是晚霞呀?”
“太阳落下去时映红的。”
朵朵并不走,很烦恼地自语道:“太阳玻璃打碎了,云彩衣裳都染红了。”
亚鸽心里一动,悄悄捏紧那只小手。
晚上钻进被窝时朵朵突然问:“爸爸,太阳也脱衣服睡觉吗?”得到肯定答复,不知意味什么地叹了一口气,说声“晚安”,缩进被子里再不出声。
妈妈跟出来,说:“你回来前小文来过电话,说明天一早她来接朵朵去公园,叫给穿得漂亮点。”
“知道了。”
“小周也来过电话,说刚从烟台出差回来。没急事,就为打个电话问我和你爸好。”
“知道了。”
“要说,小文那孩子倒是挺不错的,长得水灵,又有文化,脾气也好。也该二十好几了吧?”
“妈!”
妈妈吓了一跳,“我也没说啥呀。”
“你去睡吧。”
“呃。”
亚鸽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莉迪娅在客厅里恸人地啜泣,不时伴着弟弟吮“滇红”的响亮的声音。大哥在隔壁呵斥小侄算术的粗心:“题上明明告诉你是求和的平均数嘛!”摊开那包材料时,亚鸽突然感到,今晚的时间太多。
想了半天才想起,儿子今晚没有听故事。
四
程前:
知道你会很快再写信给我的,但没想有这么快。如果没错的话,你这封信,是接到我的信后就立刻寄出了,否则像你这样细致的人,绝不会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给我写信。只知道报纸电视上说你如今活动频繁,不知道你会这么性急。显然你又在多愁善感了,那层厚厚的外壳到底没能彻底藏匿住你。这可不是你们搞政治的人该有的。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看我。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怜悯,但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四年前被你说中了的事实,除了证明你的过人预感,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没有。也难怪你能把你的道路设计得如此准确。
我在休息室里胡乱给你写这封信。一小时后,我就要上场去表演据说是今年秋季的流行款式了,那时就没有我了,只有人们挖空心思剪碎又缝合在一起的布料。上午找服装感觉的排演给了我轻松的机会,因为我的那七套服装暴露不多,这样会少些疲劳。可我又需要疲劳,需要身体和思想都疲劳至极,以便在回到我那套空房里后无力思维,立即进入睡眠状态……
无须瞒你,我又回到我那套空空的小屋里去了。这次,连箱子也没提。
前天夜场演出回家,极累地上了三楼。杏子给我开的门。看见杏子那目光我就明白了,我在父亲家寄寓的最后时刻到了。“你别说了,杏子。”我去屋里提我的箱子。杏子冲进来抱住我哭。我强作轻松地拍拍她的脸说:“队里这段时间演出多,要我住到队里去。我今天就是回来取行李的。”杏子说:“姐,不是我。是小榕。何菲菲有好几天不来咱家了,小榕说他要在门厅里搭铺。”我想笑,却笑不出来。我想我是太残酷了,我的介入活活拆散了两对鸳鸯。而上帝制造爱情小屋时早已规定说,你们中间只有两个人能同时进那门去。
那夜杏子说什么也不让我走。爸爸妈妈站在客厅门口,什么话也没说,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妈妈几次转进厨房去看烧在炉子上的水,出来时眼里红肿着。
那晚家里杀了鸡。
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我差点大叫出来:你们要干吗呀!你们还嫌我痛苦得不够吗?!
苏朗去鄂城办事,小榕根本没回家,这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后的一夜。我给爸爸打了洗澡水,给妈妈削了只梨,什么话也没说。我没说,两个老人也没说。我是这家的大女儿,又是这家操心最多的女儿。我已使家里人心碎了。听见妈妈在隔壁房里捂着嘴呜呜哭,我有好几次差点儿忍不住要甩开门冲进黑暗里去……
半夜,杏子钻进我的被窝,紧紧搂住我,脸贴了我的脸,说:“姐,你今后怎么办呀你?”泪水顺着我的两鬓悄悄流下来。我说不出话。我知道杏子幸福太多,她已不忍独自享有那么多幸福。杏子在耳畔轻轻说:“姐,这些天你见过他了吗?”我说:“杏子!”杏子缄默了一会儿,又说:“姐,今天我看见他的评论了,在日报上。”那个署名亚当的评论,那个傻乎乎又固执的男人第一。我的心在撕裂,一滴滴淌着血。突然想到,这些年,他的一个字我也不曾读过。我是太少太少关心他了,这就是我们离异的症结吗?我们结婚四年,大喜大悲过,极热极冷过,他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我至今不知道。我从未走进他的那个世界!在这方面,我竟不如他的书桌、他的读者。
屋外有小雨了,程前,好轻好轻的小雨。
程前,不要说那些激烈的话。你把你的聪明用来证实一个弱女子的窘状,你以你潜在的力量来胁迫一个弱女子诚服,这不公平。是的,我是弱女子,极弱的女子,从来就是。打一开始,你和许多人就把我看成一个天性高傲的小公主。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吗?十一年前,那时我十四岁,你二十岁。爸爸带我去傅诚伯伯家。一进客厅,我看见沙发一角端端正正坐着一名英俊的小军官。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有什么东西刹那间在我的心口撞击了一下,一闪即逝。我看见他的眉毛也急促地跳动了一下。我愣在那里。熟悉的客厅因为那个陌生的英俊小军官的出现而生疏了,而闪烁着光明了。傅伯伯笑着说:“怎么,玫子,不叫胡子伯伯?”我的脸红了,红到耳根。我知道我那时一定粲然如鲜花一样动人。我说:“胡子伯伯好。”爸爸嗔怪说:“这女子,永远是个娃娃。”我气恼,干吗说我是个娃娃?干吗说我永远是个娃娃?傅伯伯笑着说:“艺院附中学生倌,来给胡子伯伯唱支曲儿,胡子伯伯好久没听百灵鸟儿叫了。”我想让自己表现得成熟一些,像个大姑娘,一个真正的大姑娘。我说:“行,我来唱段班托克的《海豹女人》。”我知道那个英俊的小军官一直在注视我。我知道。我才不往那边看呢。他果然注意着我,站起来说:“我来给你伴奏。”走到客厅一角打开钢琴黑盖。我好憋气。我可不想有人伴奏。我不要伴奏,这谁都应该知道。我只要这空间存在我一个人的声音。何况伴奏的还是一个英俊的小军官。但是The Seal Woman开始了。琴声流利舒畅,诱我进入角色,我没办法不唱。我开始唱:海豹女人年轻美貌,常穿一套海豹皮的外套在海上神出鬼没。少年渔民一见倾心,百般求爱,但海豹女人不愿舍弃海上的自由生活。少年渔民趁其不备,偷了她的外套。海豹女人无法入海,只能和少年渔民结婚。七年后,海豹女人终于夺回了外套,乃披衣入海,永不回岸。少年渔民伤心欲绝,紧紧抱住孩子,从此父子相依为命……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幕歌剧。我觉得我就是那海豹女人。我喜欢大海的博大莫测,我渴望大海的自由自在。我唱得从来没有过那么好。傅伯伯和爸爸都鼓掌。英俊的小军官也从琴键上抬起头来鼓掌。傅伯伯说:“玫子再来一曲。”英俊的小军官说:“我再为你伴奏。”我又恼了。我不要伴奏,不要流利和谐和殷勤。我故意不看他说:“那我再来一段上党梆子《西厢记》里的末角腔‘雁儿落’。”我旁无他顾地唱开:“我只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原来是可意种来清蘸。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城倾国貌。”拿眼角偷偷打量小军官,那一个愣在钢琴前,一个琴键也按不下去,窘态万分。我好得意,索性又加了段有唱有做的“得胜令”……一曲甫毕,把傅伯伯和爸爸两双老掌拍红了。掌声却缺了一人,是小军官。我还没够,转头对小军官鞠一躬。我要气他。我说:“谢谢您的合作。”我看见红晕从他的脖颈涌上额头。哈,这回轮到你了,谁让你逞能来着!傅伯伯嘿嘿笑着说:“忘了介绍。这是我外甥程前。程前,叫丛伯伯。”“丛伯伯。”“这是你玫子妹妹。”“你好。”我故意没听见,跑到一边去看热带鱼。我有些沮丧。我不想气他,真的不想。那个小军官,他叫什么?程前?好智慧的名字。那不是我的本意,不是。可我干吗老是跟人过不去。我不是一个好女孩,可我应该是个好女孩。那一刻我好难过好难过。吃晚饭时,阿姨做了我最爱吃的水晶肉,我吃得无章无法,满头大汗,惹得傅伯伯和阿姨哈哈大笑。小军官不笑,偷偷踩我的脚。我拿眼盯他。他小声说:“玫子,吃过饭我带你去玩。”“玩啥?”“去打网球。”“我不去!”“那去游泳?”“我不稀罕!”“爬山怎么样?”“没劲儿!”“那,”他没辙了,垂头丧气地问,“你说干吗?”“我要打网球!”说完我扑哧一声喷出饭来。看见小军官无可奈何的模样,我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那晚在院子里送我们回家时,小军官叹口气说:“玫子,你好骄傲,简直像个公主。”
程前,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看懂我,没有看出我。你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一个骄傲的公主,当成一只无忧无虑的百灵鸟。你们错了。我的躯壳下,只有一旺好轻好飘的火。如今,那火熄灭了。只需一场小雨,我的傲岸的城墙就全垮掉了……
屋外仍在下着小雨,飘飘洒洒,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