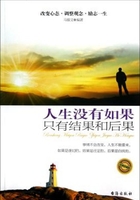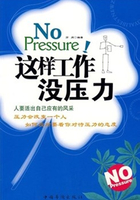马义几乎是同时读到下面这封邮件的。
雨:
刚才我睡着了,半个小时,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妈妈死了。现在清醒之后,我认为更准确也是更切合梦境发展需要——但我硬生生地把它折断了——的说法应该是她突然不见了。梦的翅膀被我潜意识里坍塌的土墙压在数不尽的使人喉咙发干的尘埃中,然而它遗留的恐惧却如颗粒状的幽灵漂浮在这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清晰可见且伸手可触,或许因为房间狭长的缘故,我此刻分明看见它逐渐汇集成长蛇的形状,在空中扭动,疯狂而凶态毕露,最前端,它最靠近我脑袋的位置,是迅速张合并发出咝咝呼吸声——像一个令人生厌的鼻炎患者。
与其说这些随着即将来临的时刻就要遁入无形的东西,虽然你我同知其谵妄的特质,虽然谁也不能担保下一个这样的时刻它是否会卷土重来——其实我确切知道它必然到来,它已经很善于探究我的本性,明了我是多么自相矛盾地欢迎它如期而至。可怕的不是随它席卷而来的恐惧,而是我对这种状态的乐此不疲。偶尔,有那么一些时刻,我甚至为它的迟到而内心不安、焦灼等待。也许我可以改变,但要命的是我却不想。它和黎明前最黑暗深沉、浑浊无边的夜色一起,为我织就了这样一个独特结构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一切总以冬天的韵味在悄悄进行,鹅毛般的落地无声的大雪在每个季节里的每个时刻都铺满街道,尽管梦中的人们依然跟随季节的更替展示着衣装和表情。这个世界里,时间是以在桉树与槭树之间飘落的雪花计数,而不是依梦中某条街道的某个擦得澄亮的橱窗里摆设的具有极大诱惑性的调得精准无比的座钟为准,尽管它背后的穿蓝丝绒的女服务员生动的表情也在瞬息万变。梦里,所有的东西都跑得飞快。
还是来说这个梦吧。我不记得它已经重复多少次了,也许无所谓重复,因为每次它都自动加入了许多新鲜的背景、天色、建筑、人和言语表情,但我似乎刻意摒弃这些,至少是不自觉地淡忘,总是抓住自以为是本质性的东西,像落水者抓住自己的头发试图提起自己一样。不能说我的做法毫无道理,没有这些东西的梦境将不再立体,甚至不再是一个正常而完整的梦,我担心的只是,它们是否真的只属于梦,我的梦。
梦里,我突然回到了久别的乡村里,妈妈去挑水,在我的视野(意识)之外突然不见了(死了)。家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我指的是其外在意义。原先的三层建筑被三家瓜分。他们在客厅里摆上了很长的桌子。其中一个男人笑容可掬地与我打着招呼,我想去门外只有从他们的桌子上翻滚而过。这时,那个男人的母亲进入我的视线里,背景变成热气腾腾的厨房,她像我印象里小时候的妈妈一样问我,晚上你想吃什么。她还看着我爸爸说——随着她语气的目标我爸爸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这下好了,一家人,要做三种不同口味的菜。
一个多么可怕的梦。我不明白,那个男人(即我第一次向你请求决策的对象)和他的母亲何时因何种权威在我的参与和允许之外褫夺我妈妈的地位。而这和我妈妈的消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哪种路径的交叉口因何种原因遭遇以何种目光对视用何种形式抗衡,是以倾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和平方式解决,是彼此自然而然地走上后来的征程,还是一个永远背上对另一个僭越与篡夺的内疚或优越。
好了,曙光开始露头了。还不能称是曙光,灰蒙蒙的天色之下,一切静悄悄的。与梦境中同样静悄悄的死寂不同,这里有着谁也阻挡不了的万千生机,无论它源自邪恶,还是因于向往和平。在这种灰蒙蒙的天色之下,我总是恍惚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几个、十几个世纪之前的城市里。
我终于提到了城市。那么就让我在切实地讨论那个梦之前谈一谈这个复杂而粗糙、油腻而冷淡的词汇吧,而且我宁愿在天光大亮之后旁若无人地谈梦。
现在,这座城市正在苏醒了,已经有一些看上去过于衰老的女清道夫在我的窗外极其温情而冷漠地挠着它的脊背,伺弄着这座城市轻浅的若有若无的梦。这是一座背向我们的城市。它或许从未熟睡,或许是因为面目可憎或者不屑与我们照面,总之,我从未能够揭开时刻蒙在它脸上的面纱,我把这看成作一种不容商量的无情的拒绝。
还是不去说这样空泛的话吧,它们对我们现实问题的解决又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你也有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城市与故乡对称,我夜晚生活在城市里,在白天即将来临的时刻和整个白天,我却徜徉在自制的故乡或者自制的有关故乡的梦境里。这种分裂让我竟有了一种近似自虐的快感。我两个都不属于,却谁也无法阻挡地同时拥有两者。
城市与幸福总是息息相关,要么可以说起是虚假的幸福或不幸。在故乡,我们想不到也没有理由去想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紧密程度。而在城市里,一切都以幸福为衡量指数,这很荒谬,却不可苛责,我们还有更好更直接明了的衡量方式吗?而我们所谓的具体方式却又少得可怜,终结到一点之上,就只剩下情感了。情感像一把急促而有力的锤子把我们钉在城市的脊背上。城市像个庞大的吸尘器毫无所知地把我们的情感连同垃圾、汽车尾气一起吸纳进去,在某一个时刻又玩笑似地吐放出来,而我们就这样善于自我折腾,否定又肯定,并在被城市消化过后的吐放出来并不新鲜的物质中寻找本已或本该去天堂或地狱的情感,以此表明自己的坚贞,尽管这种是自己嘲笑抛弃的,但仍可温慰自己。只是,我们在向谁表明自己的忠贞。
我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像个病态的孩子冬天里百般求得家长允许去雪地里走一走,他看见了许多东西,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回家后只会病情加重。天似乎又暗了下来,我已经习以为常这种夜的反扑了。
说到底,对幸福我已经麻木了——因为我永远弄不明白它肯降临的契机并因此自觉忽略了其意义所在,但我此刻心里的感伤却是真实的,并非波涛汹涌,但清澈见底。
那个男人远非你所想像,如果你这些天对他有所想象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如邮件上一样对我不闻不问。这个城市不大,你甚至可能见过他,并因为他的体征而留有印象。他是独眼龙,右眼在高中时代一次完全出于意气的械斗中报废,当然他曾哄骗我是在一次公众并不熟知的边境小型冲突中受伤,我查过他的资料,洞悉于心,但对此不以为意。甚至我喜欢这种有着某种低级情趣的谎言。至少它能使人放松和愉快。另外,他头发稀少,虽然精于打理,但永远只能在头顶周边做文章。他背驼得很厉害,自己不注意形象时背部的隆肉能和脖子齐平。说了这么多——我承认吧——我对他是有些感情的。城市是一个盛产随便的地方,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我与他开始源于我的随便。
我与他的最终分开,你的忠告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此刻我认为最终的原因在于他的母亲——请原谅,在白天即将来临的时刻,人和正常时段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而关于他的母亲我却不想详谈,源于此刻尚未完全消去的恐惧,它还是按往常习惯在作最后一次持久而猛烈的进攻。如果你在屏幕的另一方看到我,你一眼就会发现我的头发都在颤抖。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做这个梦的原因了,虽然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但请相信一点也不牵强。我在上床睡觉前想着你的一些可能的境遇,不知何故越发为你担心起来。于是就翻床头的书,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我惊呆了,怔在那里。无论这话出自多么偏僻的一位先哲的口,无论它的语境是什么,我长久地呆坐在那里,泪流满面。那一刻,我在想,如果你不把我当作朋友,如果你不是我朋友,或者如果某一天你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城市光秃秃的荒芜一片了。我是因极度惊恐的心情才做那个可怕的梦的。谁也无法让我否认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最后,祝你健康!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