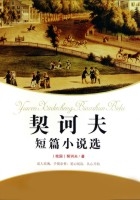城市,这是个已经陈旧却永远翻新的词汇。它似乎像个迟暮的老人,已经没有精力或任何好奇心,总是踯躅于原地以无情、冷漠甚至毫不掩饰其残酷与讥讽的神色旁观风云沧桑,似乎一切都无法令它引以为意了。但其实,它是变动不居的。不说久居的人们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就连永远或暂时离开的人也将带着它赋予的可能毕生再也抹不去的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个良莠不分的包容者,更是个霸道的置一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拒绝于不顾——也引不起它丝毫同情心——的侵略者。它塑造出一代代人相似的性格和见识,并逼使他们自以为这些是本性而骄傲且愚昧地自然流传下去。城市在人之外拥有自身的历史,而人们却因无知或背负沉重包袱的原始欲望而非把这些强加到自己身上。若干年后,当这些人早已匿迹尘土,城市依然屹立。由此可知,人们以城市的主人自居,这种自恋情节多么令人发笑。城市是无视这些的,它从不企图向人们指出其间的虚妄和荒谬,它在清晨与黄昏发自肺腑的叹息可惜无人能领会其中深意,它像一个走过千年已经感到疲倦的智者任由顽皮的孩子在其胸怀中播撒欲望、忧愁狂躁、爱与恨、失足与挣扎。谁是城市的主人。
城市的全貌只有空中才能有所领略。当你在空中经过一个城市,你会由衷感觉它也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结合体。其间,有无数的男女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还闲情逸致地认真而执着地爱恨情仇。然而,它却以各种你可感知的形态拒绝你的进入,你很难属于一个城市,正如一个城市永远也不可能属于你一样。你的城市到底在哪里呢。
进入,一个有着侵略意味却经常因为实在的无奈而有那么点卑躬屈膝的字眼。它似乎和投诚有些关联,因为这种进入毫无例外地附带着对另一个城市的背叛,无论你因何种理由或借口离开它,暂时或永久,这并不重要。已经如你所知,城市并不十分欢迎外来者,它的刁难随时随处可见,或许就从你刚刚擦肩而过的某一个它的居民的眼睛或手势里冒出。它非要玩笑似地却又不失风度地提醒你,你的魂和根不在这里。那么,你的魂和根到底在哪里呢?在刚刚弃之而去的另一座城市吗?
但无论如何,进入都是一个最富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你到达一个城市深处的轨迹,当你从空中、海上、某座桥、某条路离一个城市越来越近,这时担心与惧怕总会少于兴奋与好奇。你甚至期盼自己能在这里获得好运而不仅仅是以领略的心态感受一种全新的生态,你想在这里重新开展事业和爱情,美好的想法纷涌而至,但很快,当你下了飞机、轮船、汽车,踏上第一步这个城市的土地,很快,你就被它淹没了,都来不及或想不起发出一声叫喊。
马义的城市与此大同小异。他承认,自己是带着一种无聊的心态去揣测所谓“朱老公”的城市的。既然是揣测,就无须任何理由,而且恰恰因此才有几分趣味。马义不清楚一座城市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也经常对电视、报纸宣讲的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发展潜力、如何发展、居民守则投以嘲笑和鄙视的眼光,或者干脆置若罔闻。他从不自大到以城市主人自居,甚至他都不认为自己是其居民,他和穿行在墙缝里的蚂蚁其实大同小异。如果他有选择,他宁愿这座城市只不过是几条路和一些高楼架构起来冷冰冰的混凝土似的实体,刚好具备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城市的最粗浅特征,如果他有选择,他宁愿这座城市是一个孤岛。
朱老公的回信倒很及时。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马义打开电脑,就阅读到下面内容:
亲爱的雨:
我才下班。外面夜色很好,静到会使人认为这座城市陷入了几百年也醒不了的睡眠里。
但你依然简短的回信却令我为你担忧起来,当然我的担忧无凭无据,只源于我的习惯,但愿我所臆想的一切并不存在。
我反复翻看你的两封来信,得出一个唐突的结论,你性情大变。至少有一点是不容辩驳的,你不再像以前一样热情。更令你不原谅我的说法是,你冷漠了,对我不关心了。即使你问过我一些问题,但我相信我的直觉,你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关心,就连真正的好奇心也从你身上消失了。信读来更像一个百无聊赖的不寄予任何感情的窥伺者的眼光。
我无法想象是何种遭遇使你这样,再说一遍,我宁愿这些是臆想。你知道,一个夜班工作者难免有这些类似的意识。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对他,我无从说起,原因也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些,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为他隐瞒。他是一个有极大虚荣心的男人。虚荣心这东西,如你所知,放在女人身上有时倒可成为装饰,为一些无知而格外要显得有男人气概的男人们所认同、娇宠。但若被一个男人在某些场合、某些事件上发挥出来,极端点说,那他简直一无是处了,特别是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比如,他经常怂恿我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些聚会,如果席间我得到虚假的赞美,他就显得极为高兴,那神态似乎让他舔我脚趾他都原意——不瞒你说,他还真这么令我恶心地干过一次。而你知道,我其实并不漂亮,而浮于表面的优点也少之有少,另外,不说男人们普遍的喜新厌旧,总有审美疲劳吧,即使溢美之词不仅廉价也是匮乏的。当某一次,他的朋友们不再夸赞我,更多时候是因为出现了某位初次见面的女性或者确实比我有外表优势的女性时,这些男人们苍蝇逐臭似的一转变目标就令他顿生不快,直至回家借题发挥向我大发雷霆,那状态,我倒想到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那时的他就像人家发喜糖却忘了他的存在的小孩。
还有其他许多类似情况,比如买房买车,小到平日穿衣服,不一而足。我无法厚起脸皮说起这个曾经和我如此亲密接触的男人更多的情形。他一直致力于活在显而易见的虚伪与逢迎里,连我的真诚都会令他深恶痛绝。
最后的结果,说来令你发笑,同时也见证了你的明智,这点很是令我欣慰。因为我对他短期的冷淡,他又缠住准备办离婚手续的老婆,耍无赖、要挟,玩浪漫手段,总之,我相信,他会成功的。他老婆既然当初接受他,这次肯定还是逃不了。物以类聚。而且那个女人与他一样,喜欢清晨起床前带着骚味和满嘴的口臭做爱,这点我就无法接受,他居然当初还因此苛责我,真不可理喻。我无法接受,尽管当年我是寝室里最不爱干净的一个,你们经常敦促我、批评我,但只有一个人愿意在学校检查卫生前帮我叠被,想起当年那些青涩而单纯的岁月,想起那时的你我,真令人怀念,又让人伤感。
另外,我不知道你为何突然提起有关城市的问题。很抱歉,也许责任在我,回来后与你疏于联系。毕业后我是去了南方,但不到一年就因为各种原因回来了。好像是一次我推销化妆品与你在街上偶遇——那几年我什么都干过,吃的苦不算少,但似乎也没转化为良性效果,如今仍然只找了一个夜班工作,当然我很乐意在这个时间段上班,真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你所说的城市在凌晨两三点时都具有别具一格甚至不同凡响或者还可以说成是颠覆性的意义。那次你匆忙有事,我也急着去见一个客户,你说手机号最近要换,就给了我你邮箱的地址。
这个城市不大,许多陌生人都会一而再地见到。但此后我们却再没有碰面。你是了解我的,懒得主动和人联系,这与大咧的外表相反。所以,请原谅因我的缘故导致如此长时间的疏于交往。
好了,就此打住。我也该收拾自己,然后睡觉。最后有一个期盼,如果你愿意,下次回信不妨说说你的生活,你的丈夫和孩子(按你以前的计划,他至少两岁了吧),而我,仍将和当年一样,非常乐意做你的听众!
晚安!
你的朱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