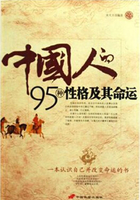并非如你想象,辞职后的马义整日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在棕色沙发与表面已经有几处脱皮如今看不出原色的茶几之间像个白日幽魂般游荡,或者停步去年冬天枯死不知何时又绽出新芽的盆景之间,毫无表情地抬眼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千奇百怪、结构狰狞的房子。一个个并不洁净的窗户企图尽可能多向外人展露其内部世界,以暴露狂的心态向外凸出、侵略着,结果却适得其反,至少在马义看来,这些冰冷而钢化的材料只像一个个诱人的囚笼,圈住了它应该占有和不该占有的东西。马义觉得长时间作如此的凝望使人感觉喉咙里布满了灰尘,像咽炎一样驱之不去。
然后,他转身走到靠墙矗立的紫红色书柜前,逐一审视里面收藏的纪念品,这些东西来自各地,有些还保留着那个死去女人的手温,甚至早已枯朽却散发着尸体气味的吻,马义觉得自己无法想象唐雨曾经亲吻抚摸过它们,并视若珍宝。但这一切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逝去的珍视并未中断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我们不小心淡忘或刻意泯灭。人和物品亦如人对人的感情一样,永远也只可能是阶段性,当某一天翻出陪伴自己度过一段岁月如今束之高阁的物品,其唯一的意义就是作为见证者的身份并未消失,没有什么能长期而彻底地从其之上抹去那段岁月的质感和味道,如果当时确曾有过的话。
不出一周,马义就把这套房子租了出去,住进去的是一对喜气洋洋看上去对未来有理性规划虽然这种理性并不可靠的夫妇或同居者,还是老气横秋会因残阳在西南角仿旧风格的夹角屋檐消失而日益惆怅的老人,马义在所不问,而且觉得区别不大。房子在其本质意义上说,只是一个虚幻无任何实在理由的形式,这种由砖头和钢筋架构起来的东西有时一如宗教,是内心需要时才有价值的信仰。也正因此,马义需要一间独立的房子,一个独立的狭窄的牢笼,而不是更大的牢笼。在一个比走廊宽阔不了多少的狭长的房间里,各种温度都会升高,各种潜意识才会停驻不去,而心灵也只要冲破一层阻墙就可以走出窗外,而不是打开房门,趟过漫长的客厅,因为惧怕、疲惫、不甘、忧郁而在门前、墙壁前、松木椅腿边由于体力和精神的双重不支而委顿余地。
马义在相隔两个街道之外租了一个六层上的小阁楼。需要躬腰经过十几级悬空的木质楼梯才能步入新房间,每次马义都仿佛觉得是去天台,这竟然激起他久违的刺激心理。刺激并不只来源于儿时的梦想,更多的甚至根源于结婚不久就在他胸中发酵却无世俗突破口的愿望,去外面租个单间——黑屋子——他就是这样符合心理需要毫不讳言地称谓。在那些难熬却又似乎瞬息即过的日子,厨房是他唯一的慰藉和安身之所,他一个人静静地在桔红的白炽灯光下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面对休息的锅碗瓢盆发呆,因为只有这里,午夜才无人问津。
黑屋子距离原来的房子不过百步。开始的几天,马义会偶尔慢慢步行到它面前,出神地看它一回,说不上留恋,正如离开与逃避无关一样,人的需求很简单,但生活本身却远比我们了解到和所能说出的要复杂,其一成不变的复杂性在我们企图表达之前就嘲笑或嬉笑着遁于无形了,它们当然会跳跃到另一种表象上,与我们游戏,诱惑我们去捕捉,却总是不容易被看透。马义就出神着站了几分钟,什么也想不出来,甚至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以及它与自己之间存在一种怎样性质的联系。此后,偶尔经过时,他就像路人一样了。
马义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从大学辞职只是一个形式,因为事件的巧合而恰如其分地赋予它一种决绝的含义,外界这样的认识未尝不可,其实远非这么回事。他开始找工作,先去了一家报社负责有关养生栏目的组稿,最后因为工资谈不拢七天后就走人。马义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老女总编在试用期六个月内不给他基本工资。也许如你所知,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总编是个老女人。然后他又去了保险公司、辅导学校,但都坚持不了多久。因为每个地方都是有一些老女人。这一切无可厚非,也无须深谈。
几个月之后,马义开始在一家私人书店帮人打工,老板因为经常去各种场所厮混,所以几乎所有的时间只是马义一个人在管理。书店九点开门,整个白天都很少有人光顾,有时几个背着书包的男生进来一阵乱翻,丢下就走,马义非强求他们把书整理好放回原处。他不在乎有无客人,连老板都不在乎,偶尔老板把车停在门口,进来逛逛,马义也不怎么搭理他,那人也完全像个顾客,手插兜里晃荡一圈立即走人,神情匆忙得就像失望之极赶着去另一家书店抢购一样。马义晚上九点下班,踩着车悠悠地沿着路灯几已熄灭的街道回家。这座城市在夜晚、在马义的心中此时又恢复了几年之前的静谧,但不再深沉,坦坦荡荡而非深不可测。
马义给“朱老公”回复了一封邮件,依然简短。
最近较忙。你可好,与他之间怎样了?上次你说到对他最近的一些做法颇为反感,可否具体谈谈。提不上好的意见,但想听听。另外,如果我猜得没错,你应该也在这个城市。
关上电脑,马义对着黑色的屏幕嘿嘿傻笑,里面有个黑色的影子坐立不安地扭动着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