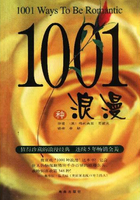大国两口子是打的回来的。他们进屋时,吴桂花和以往一样,把饭菜摆放到桌子上了。这顿饭,三个人吃得都很高兴。尽管开始的时候,大国和郝艳的高兴是装出来的,到后来,他们看到娘今天的确高兴,他们的情绪也渐渐地跟着娘高涨起来。吴桂花破例喝了半杯酒,脸上涌现出多少年少见的红晕。
大国和郝艳呆到晚上的8点半,郝艳让大国自己回去,她要留下来跟娘做伴,吴桂花拒绝了。她说这房子我自已都住多少年了,没啥可害怕的。她硬是把郝艳推出院门,看着他们上了出租车,这才插上大门,回到屋里。
吴桂花坐在炕头上,仔细地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件摆设。这些东西,她用过几十年,可以说,每一样物品上都体温般地留存着她的情感,每一条木纹里都雕刻着她的故事。
吴桂花清楚地记得,摆在炕稍的这对水曲柳箱子是她爹用了半个月的工时才打出来的,是她跟刘士军结婚时,家里唯一的一件家俱。那时他们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一个叫柳条沟地方。那个地方除了满山遍野的柳树,再就没别的可值得炫耀的东西了。她跟刘士军是一个村子的,刘士军比她大三岁。她所以相中刘士军,就因为刘士军的筐子编得好,一捆柳条,到他手里三拧两转的,就出来一个板板正正的筐子。刘士军的这点手艺,在当时还很吃香的,每天都能弄个三块五块的收入。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在吴桂花的撺掇下,刘士军成立一个柳编厂,招几个人在他家里的厢房做业。当时大国刚出生,吴桂花就在家里哄孩子。眼见着家里的筐子越积越多却换不来钱,看着刘士军天天焉头巴脑的样子,吴桂花有些着急。她扔下大国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她在县委工作的一个表叔。她在表叔家软磨硬泡地呆了四天,才通过表叔从外贸局拿到一张订单,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筐子篮子都捣腾出去了。等她回来时,连着急带上火,奶水早没了。大国出生才不到六个月,就因此戒了奶。吴桂花为这个事情,总感觉有些对不住孩子。好再家里从此有了钱,她就可劲地给大国买最好的奶粉。等到大国两三岁时,比别人家吃奶的孩子还高大,吴桂花这才了却一份心事。
在大国七岁那年,围前左右山坡上的柳条让人们割光了,刘土军的柳编厂也就跟着破产了。为了给大国找个好学校念书,他们举家搬迁到县城的郊区。在这里买了块地皮,盖起房子,也就是吴桂花现在住的这四间北京平。
大国去县城的第四小学上学,这所学校是当时这个县城里条件最好的。大国上学的第一天,刘士军在城里的家俱店给大国买了个两头沉的写字台。拉回来时,磕破了点皮。刘士军发现原来这么好看的东西,竟然不是实木的,板材全是锯未子这类的玩艺压成的。这让刘士军的眼睛一亮,他便在城里租了一栋停产的厂房,开始生产纯实木的家俱。
做家俱的原料还来自柳条沟,那里虽然没了柳条,但成材的柳树还是有的是。刘士军本来不会打家俱的,可吴桂花的父亲是出名的老木匠,他来这里给刘士军当监工。没过半年,在这个小城里,刘土军的家俱店便有了相当的名气。吴桂花清楚地记得,那个坐睡两用的沙发,就是这个时候买来的,那时候他们三口人睡在这铺小炕上,她60多岁的老爹就睡在那个沙发上。而那个写字台,大国一直使用到上完高中。由于桌面破皮的那个地方进了水,鼓起了一个大包,就像人身上长了疮,发了炎似的。这期间吴桂花几次提出来要换掉,刘士军却不让,说这个写字台是指导他发财的老师。
这之后的五年里,对于吴桂花来说,应该是最满足也是最开心的。早晨刘士军骑上摩托车载着大国上学,中午他们爷俩在城里的饭店吃,晚上爷俩再一起回来。吴桂花在家里负责购物,收拾屋子,给他们爷俩做饭,再不就是织毛衣看电视了。每天晚上,刘土军都把店里的收入带回来,交给吴桂花保管着,到了一定的数额,再由她存入城郊储蓄所里。吴桂花的工作天天就是花钱和存钱,也因此招来很多羡慕的眼光。她家的东西,什么大衣柜,梳妆台,差不多都是那个时期他们家俱店自己打制的。那时吴桂花只要是说出来想要啥,刘士军毫不打哏地满足她。
大国上中学后,便不再愿意和父亲一起走了。有时候他们也的确走不到一起了。孩子要上早自习,天不亮就得走,而这时刘土军到门市里,也没有生意可做。吴桂花想让刘士军在家多睡一会,便给大国买了一辆山地车,让他跟同学们一起走了。他们的这个县城不大,郊区离市里也就是七八里地,小伙子骑自行车,也就是十来分钟的工夫就到了。
不用经管孩子了,刘土军变得无拘无束起来。在外面喝酒的次数频繁了,几乎天天有饭局。跟朋友打麻将的时间延长了,有时候玩到半夜才回来。吴桂花怕刘士军酒后骑摩托回家不安全,有时就嘱咐他住在公司里。现在刘土军的办公室,可不是当年的那间小屋子了。里外两个大套间,面积有一百五十多平米,外间是业务室,里间是休息室,都装修得跟宫殿似的。从外屋的沙发到里屋的床上,至少能睡五个人。
大国上高中那年的十月份,刘土军突然跟吴桂花摊牌了。说他又有了个女儿,是一个叫兰子的女人给他生的,现在孩子都两周岁了。刘土军当时并没提出跟吴桂花离婚,只是说完后就躲起来了。大约有半个多月,吴桂花找不到他,那个叫兰子的女人也找不到他。
在这半个月里,吴桂花喝过一次安眠片。她是分十几次去五家药店买来的,大约有60多片。她是趁着大国上学后喝上的,喝完后就换上一身新衣服,安静地躺在床上睡觉。当天正赶上那个叫兰子的女人找上门来,想跟刘土军讨个说法,这才救了吴桂花一命。
吴桂花出院后,她首先找到兰子,也看到她与刘土军生的那个女孩。吴桂花打了兰子一个嘴巴,这嘴巴打得很重,兰子的嘴角都流血了。兰子没还手,她坐在地上呜呜地哭,那个孩子也跟着哭。吴桂花说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起,咱们三个人的帐算是两清了。
吴桂花主动提出离婚,她只要走一笔钱。她对刘土军说,把家里的产业留给你吧,你还得养家糊口。你已经对不起我们娘俩了,别再对不起她们娘俩。
当然,吴桂花要走的这笔钱,数目相当可观。她用这笔钱供大国念完大学,帮助大国在城里买上房子,现在手里还剩有十万多块。
大国结婚后,吴桂花又从小平房居住三年多。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并不是她所谓的生活习惯问题,而是这里埋葬着她的一个梦。她像守墓人一样,在日夜地看护着这个梦。这次她义无反顾地闹着搬回来,因为这个梦又开始延续了。
就在上周六,吴桂花去市场买菜。在一个肉摊前,她遇到老谢了。这个人是刘土军家俱店招来的第一批工人,也是吴桂花的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最满意的徒弟。他与吴桂花都有将近二十年没见面了,吴桂花根本就不认识他了。老谢跟吴桂花说了半天话后,吴桂花才多少有点印象。老谢还和从前一样,口口声声地管吴桂花叫嫂子。这个称呼让吴桂花相当反感,她也就没怎么去搭理老谢。两个人唠过几句家常,吴桂花找借口说,今天孙子放假,我得回去给孙子包饺子。就在她转身的时候,老谢发了一句感叹,说看你现在多好,儿孙满堂的,我刘哥没这个福份啊,他现在算是掉到地下了。
吴桂花让老谢的话扯住了,问老谢怎么回事?老谢说刘士军几十天前得了脑血栓,现在还住在医院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以后可能得半身不随了。他说从打刘士军住院后,小兰就没怎么管过,他们的那个孩子在外面念书跟本不知道信。小兰只打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在那儿伺候着,她自己坐在公司里当起大老板,天天有说有笑的。
吴桂花没等听完老谢的话,便匆匆地走了。出了菜市场,她竟一时间分不清楚东西南北了。她站在市场门口,茫然地看着路上汹涌的车辆,分辨好半天,才找到通往双和小区的那条胡同。她拎着一筐子菜,抵着头,眼睛盯着左脚的脚尖。在走到小区门口时,超市的小李跟她打招呼,她就奔着小李过去了。她让小李把菜给她寄存一会,说刚才买肉时找错钱了,她还得回市场一趟。在走出胡同口后,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她告诉司机,说去县医院。
吴桂花到医院后,她向护土打听清楚刘土军的病房。她在走廊上徘徊几分钟,还是移到了病房门口。这是一个单间,透过半开的门缝,她看到刘土军正躺在床上打点滴。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十八九岁,正捧着一本杂志,低着头看着。
吴桂花没敢惊动屋里的人,她只是看一眼就悄悄地走了。出了医院,她又打一辆出租车,把她拉回到胡同口。吴桂花到超市找小李拿回她的菜,小李问她把钱要回来了吗?她说要回来了。说着就赶紧上楼了。
孙子在家里呆了一天,便又回学校去了。孙子是周日晚上走的,吴桂花是周一上午摔着的。她所以从楼梯上故意摔下来,就是为搬回到小平房找个借口。
吴桂花回到小平房的第三天上午,她又去县医院了,这次她拎了点水果。她进屋时,刘士军好像是睡着了。她走到病床前,那个小伙子便看出她是来看刘土军的。小伙子站起来,一边把她手里的东西接过去,一边试探地问,您是我们老板的亲戚吧?吴桂花点点头,小伙子把椅子往前推了推,让她坐下。小伙子说,要不要叫醒我们老板?吴桂花摆了摆手,说让他再睡一会吧。那个小伙子又掏出手机来,说您是我们老板家的啥亲戚,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吴桂花赶紧摆手,说不用了,我没事,在这里等一会吧,等你们老板醒了,我跟他说几句话就走。
吴桂花跟那个小伙子聊了一会刘土军的病情,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护士来测量血压,把刘士军叫醒了。刘士军醒后,并没有马上发现吴桂花,他的眼神呆滞,一心一意地盯着护士。等护士走了,吴桂花才走到刘士军的跟前,他稍微低下头,问刘士军,你还认得我吗?
刘士军注视吴桂花一会,眼睛动了一下,说你咋来了?刘土军的舌头显然是很不受用,这几个字说出来很费力,也不太清楚。吴桂花说,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刘土军便把放在身上的左手抬起来,要来抓吴桂花的手,吓得吴桂花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吴桂花抬起头来,对着那个小伙子说,你出去一下行吗?我有话要跟你们老板说。那个小伙子迟疑一下,还是点点头,退出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