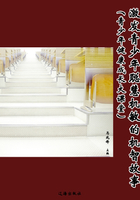吴桂花看着刘土军,她无法把眼前的这个人与以前那个五大三粗的丈夫加以比较。他们从离婚到现在,只见过两面。第一次见面是大国考上大学后,刘士军给大国买了几身衣服和一只皮箱。他是打车去郊区小平房的,只把东西放到院门口,敲了几下门。等吴桂花出来后,他便上车走了,两个人连一句话都没说。那几天正好大国不在家,跟同学一起去北京爬长城去了。等大国回来后,吴桂花没说这些东西是刘土军买来的,她怕大国不肯接受。大国对他父亲的怨恨,好像比他母亲的还要深一些。另一次是大国结婚的那天,他们在凤凰酒店办酒席,刘土军打发他店里的一个小伙计来找吴桂花,说他们老板在楼下找她有事。吴桂花本来不想见刘士军,但又怕他突然闯进来,破坏喜庆的气氛。她跟着小伙计来到楼下的一个房间,与刘士军见过一面。刘士军说他没别的意思,只想上楼悄悄地看一眼儿子和媳妇结婚的场景。吴桂花没同意,刘士军拿出五千块钱来,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吴桂花也没收。但她临走时,答应刘土军,说等录像的光碟刻出来,给他一张。后来刘桂花的确给刘土军一张光碟,是通过刘士军店里的伙计捎给他的。
吴桂花拉了把椅子坐在刘土军的跟前,她一时也不知道要跟刘土军说些什么。她问刘士军还好吧?刘士军先是略微地点了点头,之后又使劲地摇了摇头。刘土军好象是要补充点什么,但他张了几下嘴,没发出声音来。他又一次地把没打点滴的那只左手伸出来,去够吴桂花的手。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就像风中的一枝干树杈。
吴桂花犹豫一下,还是把手递过去了。刘土军像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紧紧地握着。吴桂花感受到那传递过来的颤栗,她的手也随之微微地抖动起来。吴桂花俯下身去,把嘴近可能地贴近刘士军的耳边,她说小兰对你不好吗?刘士军闭着眼睛,没有回答。吴桂花又问,以后你打算咋办?刘士军仍旧不吱声,他的眼角边慢慢地沁出一行泪水来。这是他们结婚这些年来,吴桂花第一次看到刘士军流泪。同时她也感受得到,刘土军抓着她的那只手得越来越紧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吴桂花问刘士军,说等你出院后,乐意跟我回去吗?到郊区的小平房里去。刘士军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他愣愣地瞅着吴桂花,嘴角动了动。刘桂花以为他没听明白,又把声音放大些,重新问了一遍。刘士军又闭上眼睛,在他闭眼的同时,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呜呜的声音。吴桂花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她回头看一眼,见那个陪护的小伙子正扒着门缝在看着他们。吴桂花往后缩了缩身体,刘土军的手从她的手上滑下去,一下子搭拉到床下。吴桂花往前凑近些,她说你好好养病吧,等过几天我来接你。说完,她转身出了病房。
在走廊上,吴桂花把那个小伙子叫过来。她跟那个小伙子要了小兰的手机号码。她怕记不住,又截着一个路过的小护士,借人家的笔,把那个号码写到手背上。临走前,吴桂花掏出一百块钱来递给那个小伙子,说这几天你多费点心,这点钱给你买条烟抽吧。
吴桂兰回到家里,她先把小兰的手机号抄到家里的一本旧挂历上,她怕一会不注意洗手时洗掉了。她想等晚上消停的时候,再给小兰打电话。她躺在炕头上,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又琢磨几遍。包括她跟小兰怎么去谈判,跟儿子和媳妇怎么去沟通,跟左邻右舍又怎样去解释。不知不觉的,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多钟了。吴桂花感觉有些饿,她下地做饭,把早上剩的一碗大米饭再放上两个鸡蛋炒一下。她没往炕上放桌子,这几天她一个吃饭时,都不需要放桌子,只是坐在厨房里的一个小板橙上。
收拾利索厨房,吴桂花看看时间还早,估计小兰还没回家。她就扒在窗台上,看远处的风景。她家的门前是一条公路,是从县城通过来的,置于通往哪里,她还真说不清楚。路的那边就是大片大片的菜地,现在正是青菜生长季节,绿油油的一大片。菜地里有人在干活,那些人走走停停的,与菜地相比较,那些人就像一只虫子爬行在一个大菜叶上。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不再像中午时分那么刺眼,天空没有云彩,太阳显得孤零零的。吴桂花有点莫名其妙的激动,这十多年,她住在儿子的楼房里,根本就没看到过这么好看景色。
太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红了,把西边的半片天空都染成了桔红色。吴桂花看着太阳一点点地滑落下去。她的心里徒然产生出丝丝的紧张。她害怕给小兰打电话,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跟人家说起。现在的情景跟二十年前不同了,那时是别人抢自己的丈夫,而现在人家是合法的夫妻,自己是在去抢别人的丈夫了。她甚至下意识地把左手抬起来,捂在自己的左脸上,她害怕小兰也会像当年她一样,重重地还给她一个嘴巴。
太阳浮在山头那会儿,吴桂花还在认真地盯着。一辆汽车从门前驶过,她一愣神的空儿,太阳便掉到山下去了。她带着一丝失落离开窗台,在屋里转几个圈,在她的感觉里,好像屋里的每个地方,都放着她家的那部红色的电话机。
吴桂花要通小兰的电话时,天已经暗下来了。小兰问她是哪位?吴桂花吱唔了半天,才报出自己的姓名。小兰听后也迟疑一会,问她有事吗?吴桂花听电话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她问小兰在哪儿?小兰说在饭店,公司来个老客户,她们出来吃饭了。吴桂花说那你先忙着吧。等你回家后我再打。小兰没做任何回应,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八点钟多,吴桂花又把电话打到小兰的手机上。小兰接起电话来,一副疲倦的口气说,你找我有事吗?吴桂花竟一时地被她问住了。她嗫嚅了半天,才说有点事,我想跟你谈谈刘士军的事。小兰听后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说刘土军跟你们家还有关系吗?
小兰的这句话,问得吴桂花哑口无言。她真想把电话放下了。她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做着的这件事很荒唐,是在自取其辱。吴桂花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她已经断定刘士军没有任何用处了,或者还可能是她和儿子以后的累赘。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她才敢向小兰提出来。她才认为小兰有可能让给她。那时她甚至在想,就是刘士军现在死了,她也要把他要回来。她所以这样去做,无非是给自己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她想有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丈夫,等她们百年之后,让她的墓前有个完整的墓碑。让以后儿孙来祭奠时,有一个跟别人家儿孙一样的心情。
吴桂花突然很坚决地对着电话大声地说有关系。她的这句话,吓了小兰一跳,她在电话那边啊了一声。小兰也提了些嗓门问,你们还有啥关系?吴桂花一字一板地说,刘士军是大国的父亲,是我孙子的爷爷,现在他病了,我代表他们过问一下不可以吗?
吴桂花的这个理由,是她临时想出来的。她在通电话之前的准备工作中,只想她与刘土军的事了,而忽略了大国和孙子的这一层关系。她现在想起来了,就像捡到一只杀手锏,突然觉得心里有底了,她去过问这件事应该理所应当且理直气壮了。
电话那边好半天没有声息,吴桂花又喂喂地呼叫两次,才听到小兰恨恨地说,你们啥意思?照直说吧,我听着呢。吴桂花鼓足勇气,她说,我们都知道了,你对刘士军不好,我们想把他接回来。
吴桂花的话,像刀子一样,捅得小兰嗷地一下大叫起来。她说这绝对不可能,刘士军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对他啥样跟你们没关系,我们俩是有合法手续的,我们也在一起生活十好几年了,他的财产就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夺走。
吴桂花听到小兰首先提到财产的事,她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些。她赶紧解释,说小兰,你别误会。我们只要刘士军这个人,她的所有财产都归你,我们一根草刺都不要。
小兰听后不再吱声了,吴桂花能听到电话那边喘粗气的声音。吴桂花又接着说,我也只是代表大国表达这么个意思,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好好考虑考虑,再和你女儿商量一下,想好了给我回个准信。这次吴桂花没等小兰再说什么,首先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吴桂花早上不到五点就起来了。他到门前的菜地里买了能够她吃两天的青菜。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守在电话机旁边。就连上厕所的空儿,她都先把窗户打开,把电话放到窗台上。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电话响起来了。吴桂芝跑到跟前,接起来一听,是郝艳打来的。郝艳问她家里还需要啥吗?如果需要啥东西,她和大国一会送过来。吴桂花赶紧说,我这里啥都有,挺好的,我早就吃完饭了,这马上就要睡觉了。以后你们没事别总打电话,电话费挺贵的,挂了吧。
到了第三天晚上,吴桂花也没得到小兰的回话。她终于按纳不住了,再次把电话打到小兰的手机上。两个人客套几句,问些吃饭了没有、身体好不好的闲话后,这次是小兰首先提起刘士军这件事的。小兰说她跟女儿商量过了,孩子不同意,说那样她以后就看不到爸爸了。
吴桂花听后,她呵呵地笑起来,说这有啥难的,咱们咋能让孩子看不到爸爸呢?我这儿离城里也不远,孩子想爸爸了,可以到我这来看啊。我向她保证,随时可以来,来了我给她做好吃的。这点你放心,你也让孩子放心。她毕竟是刘土军的女儿,我能接受刘土军,就能接受她。吴桂花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她和大国毕竟是一个爹的孩子,大国也会接受她的,以后我还打算让他们和亲兄妹一样走动呢。小兰听完吴桂花的表态,一副忧心忡忡的口气说,我再打电话跟孩子商量商量,这孩子死犟死犟的,我怕是她一时半会的转不过弯来。
吴桂花说孩子也是个大姑娘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事你不能硬来,你得把事跟她说开,她应该能理解你的难处的。你才40来岁,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身边守着个活死人过日子,咋说也不是个办法。你不同于我,我这把年纪了,儿子也成家立业了,孙子都上学了,我来照顾刘士军,就算是个营生。
吴桂花的这几句话,把小兰说得呜呜地哭起来。她在那边哭,吴桂花在这边不停地劝。说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也是个苦命人啊!吴桂花越是劝,小兰那边哭得越是伤心。最后小兰竟很真诚地说,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肚量。你要不是嫌弃我,以后就让我管你叫大姐吧。我们也像亲姐妹一样走动。
吴桂花嘴上答应着,说好啊,便把话题转移了。她问起小兰女儿的学习情况。小兰问起大国两口子的工作和生活。这时小兰已经改口管吴桂花叫大姐了。她说大姐,我们明天见个面吧。吴桂花说可以,我去公司找你。小兰说来公司说话不方便,我们去玉洱茶楼吧。那里的环境好,有些事我们好好聊聊。吴桂花说她不知道那个茶楼在哪儿?小兰说在百乐门舞厅的斜对过。吴桂花听后又呵呵地笑起来,小兰问她笑啥?吴桂花说我也不知道百乐门舞厅在哪儿。小兰也笑了,她说你知道县政府吧?吴桂花说差不多,小兰说顺着政府路往下走,大约二百米就到了。小兰说完,跟着又提示一句,说对了,你知道大国他们单位吗?吴桂花说知道。小兰说,那个茶楼就在他们单位的东边。
放下电话,吴桂花长出了一口气。这些年来,她对儿子和孙子一直怀有一份疚愧。她觉得因为自己的失败,让儿子这么多年没有父亲,让孙子从下生那天起,就没叫过爷爷。现在她总算是对他们有个交待了。
吴桂花在炕上坐了一会,看着那些发黄变旧的家俱,她那酸楚的心里又凭添几分苦涩。她不知道自己将以怎样的心情去对待这个曾经的丈夫。她想了一会,突然噗嗤地笑了。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有啥呀,就当他是一个走丢的孩子,现在找回来了,好好地拉巴着吧。想到这,她感觉自己突然很困,她躺下没几分钟的工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