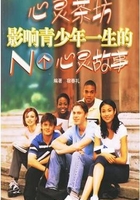听完娘的话,于齐扑哧地笑了。她说娘,你听过孩子都四岁了,还有回娘家要嫁妆的吗?于婶也笑起来,她说我没听说过,估计别人也没听过,可我闺女回来要了,我不给成吗?我给了,不就算是听过了,别人也算是听过了。也兴许哪天你嫂子不高兴时,也回她娘家朝李老疙瘩给我要一台拖拉机来,那样娘可就赚大发了。
于婶说完,娘俩都大声地笑起来。
于明达在当院听到了,他停下手中的杆子,往屋里瞅着。小磊蹲在树下捡李子,等了半天,也没见李子落下来。他抬起头,冲着于明达嚷着,姥爷,李子在树上,你往哪瞅呢。
03
合庄人有这么个习惯,每到夏天的晚上,忙完一天的活计后,爷们娘们就领着大的,抱着小的,陆续地凑合在李二歪家的门前的空地上。
这里原来是生产队的大院,生产队拆散时,正赶上李二家要盖房子,村上就在这儿给他批了块宅基地。生产队的大院有七分多,批给李二家的,只是四分。他本来应该靠着前边盖房子,这样和左邻右舍的房子能排齐。但当时这里有一口水井,全合庄的人都得上这儿挑水吃。他不能把大伙的井包括进他的院子里去,只好可着后边往前割了四分地,门前余下个三分多地的一个广场。院子建起来后,从远处看,这个地方很像汉字的“凹”,李二家就在那个豁口的地方。大伙跟他闹着玩时,都叫他是李二凹。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凹”字读起来太咬嘴,而李二的左腿有点颠脚,走路时,身子又往右边用力,就改成李二歪了。
几年后,富起来的人都在自己的院子里打了井,渐渐地就没人到这里来挑水吃了,这口井就成了李二歪家专用的了。但井在当街,使用起来不方便不说,总有小猪小鸡子掉进去,烂在里面,弄得井水臭哄哄的。李二歪一生气,也在院子里打了口井,用打出来的土,把这口井填上了。
合庄人的这个习惯,从生产队那会就存在着。那时各家得户都没电视,晚上聊天便成了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现在虽说有电视了,人们还是愿意集在一起,他们发现电视里播的事情,跟他们离得太远,从这里听到的事情,才是他们真正要听的。
下午,李老疙瘩回到家里,他就把二柱的事跟家里人通报了。五点多钟,他就经营老伴下地做饭。别人家的烟筒才冒烟,他就吃完了。
李老疙瘩坐在他家门口的石台上,嘴里的旱烟袋烁烁地闪着兴奋的光芒,映着他那张酒精烧红的脸。他在等人,等那些前来聊天的人们。他下午就盘算好了,一定要把谈论的话题引向王俭家。他早已料定,王俭家今天是不会有人来的。按照他的策划,本着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原则,以谈论庄稼开始,以王俭家的庄稼长势不错为发展,引出高潮——二柱没考上大学的事。但他觉得以他的年龄和辈份,是不能先赶到李二歪门前傻呵呵地等着。他得等大伙都集齐后,再闪亮登场。他等到快七点时,远处终于有火亮向这边移动过来,看来这波都是些男人们,按照以往的经验,他知道女人们到达这里,还需要二十分钟。男人们吃完饭,抹抹嘴巴点上一颗烟抬起屁股就走了,女人们得收拾利索碗筷后才能出来。他又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听见有孩子的说话声,他才站起来,把披在身上的外衣往上扯了扯,背着手走过来了。
李老疙瘩打老远就听见葛连在夸他家的那两只种羊,说郝老焉他们家的羊羔子跟王子林他们家的是同一天生的,下生时,大小差不多,现在郝老焉家的比王子林家的沉十来斤,今天多卖七十多块钱。
葛连刚停下来,旁边的李玉媳妇就搭话了,她说你这又是新闻中间插播广告了,你的意思是你的种好呗?说着咯咯地笑起来,旁边的几个老娘们,也跟着咯咯地笑。
葛连手里的火亮忽忽地闪烁两下,他说这事你们还别不服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养羊和种地一样,好种出好苗,谁家都打好几万斤苞米,为啥开春都上种子站买种子,咋不种自己家的?不就是图希人家的品种好吗?
李老疙瘩就是在这时把话茬接过来的,他说葛连说的在理,不管是养羊还是种地,品种好坏确实管事。但话又说回来了,你光看着郝老焉家的羊长肉了,你也没看看人家郝老焉是咋放羊的?种庄稼跟放羊一样,同样是在种子站买的种子,人家王俭家的苞米,去年一亩地打一千八百多斤,你们家的咋才打一千五百斤呢?
李老疙瘩在说头两句话时,葛连听着挺受用的,觉得是在帮着他说话。没想到后几句变味了,有点呛白着他的意思。他便开始反驳,说老李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咱们能跟人家比,人家上多少化肥,咱们才上多少化肥?人家用的是平价的,你能捞着嘛?这种庄稼跟放羊还不一样,老辈子人不是说过“庄稼是朵花,全靠肥当家”,像今年这个雨水,要是铆足了肥,庄稼不噌噌地疯长才怪呢。
李老疙瘩正在琢磨咋样把话题从种庄稼引向读书的空隙间,大伙便七嘴八舌头地把去年县里拨的五吨平价化肥分配的事又翻拾出来了,把王俭又重新地数落一通。说的这些人,多半都是老李家的一些娘们儿,她们都是李老疙瘩的兄弟媳妇或侄媳妇,她们正骂得起劲,李老疙瘩便不好意思插话。他也就没急于去控制局面,他想只要大伙所说的内容不离开王俭,不定那会儿,就能提到二柱的事。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口袋,慢条斯理地装着烟袋。
大伙从化肥聊到庄稼,又从庄稼的长势再扯到化肥上,话题总是在二者之间拉大锯。李老疙瘩在暗中观察着大伙的情绪,老李家的这些人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其它姓氏的几个人则是顺口搭音,随声附和;老王家的几个人表现出充耳不闻,沉默不语。
议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岔股头的。因为在座的各位,除了李老疙瘩和于婶,其余的人还不知道二柱没考上大学的事。于婶自然是不会再说了,下午她把这事告诉李老疙瘩,已经后悔不迭。她打坐到这儿,只是刚才跟着李玉媳妇她们笑过几声,再就一直没发言。李老疙瘩因为素来和王俭不对头,他又不想给人落下个幸灾乐祸的印象,同时顾虑到于婶在场,怕把话传到王俭耳朵里,他张了几次嘴,也只是哼哈地敷衍着。大伙感觉王俭家再聊不出啥新内容了,也就顺马由僵地从庄稼化肥这条线上,跑到当前的物价上去了。
刚到九点,于婶就站起来走了。她心里有些不痛快,下午李老疙瘩在地里提到化肥的事时,她没太往心里去,毕竟是在山上,他们两个人唠嗑。可晚上他又把话题引向化肥的事上来,而且是当着人头百众的,这让于婶感觉到李老疙瘩是故意针对她家的。因为在座的那些人中,包括着老王家的,顶数她家得的平价化肥最多。这一点李老疙瘩是知道的,她也从来没隐瞒过。于婶临走时,冲着大伙说,太困了,回家睡觉去,不听你们在这儿扯老婆舌头了。
李老疙瘩也有些不痛快,虽然人们把王俭骂了一通,但给他的感觉是大家都出了气,而唯有他没有出气一样。再加上于婶扔下的那句话,别人倒没啥反应,但他有些承心。他觉得于婶的那几句话,是在针对他的。他也站起来,扯了扯披在身上的外衣,悻悻地回家去了。
04
第二天早上,李老疙瘩起来得很晚。他老婆都放好桌子了,他还没下地洗脸。她老婆问他咋的了,哪不舒服吗?他说没有,就是晚上没睡好。他老婆说正好儿子放假,让他替你上山放羊去,你在家里再迷瞪一会儿。他朝老婆胡乱地笑了笑,说不用了,让孩子玩几天吧,过几天开学了,就得不着空玩了。
吃过早饭,李老疙瘩见二女儿正在镜子前梳头,便问她那件事考虑的咋样了?得给人家个痛快话,人家还等着听信呢。瑞芹冲着镜子里的爹说,我还没倒出空来想,让他们等着吧,反正他们乐意等。李老疙瘩马上沉下脸来,他说这叫啥话?这也不是国家大事,还用倒出空来想,有吃饭上厕所的工夫就想好了。再说了,这还有啥可想的?人家的那个条件,在咱们这儿方圆百拾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你要是错过这个村,以后怕是真没这个店了。瑞芹回头瞅她爹一眼,说那就先可着惦记的那些人来吧,反正我是没想好,我也不惦记着。瑞芹说着放下梳子,在临出屋时,向身后扔下一句硬梆梆的话,她说,爹,是不是你惦记着呢?是惦记着人家的彩礼吧。李老疙瘩刚想发火,听女儿已经走到当院了。他转过身,从窗户里看见瑞芹拎着筐子出了院门。
在上山的路上,瑞芹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倒不是因为爹说的这件事,而是听爹和娘的口气,他们似乎都急于促成这件事。这让瑞芹的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好像自己是地里的西瓜,已经熟透了,再不卖出去或者被吃掉,就会娄在地里。她也理解老人的心情,知道他们是在为她着急。她也为自己的未来忧虑过,甚至有时候,她都下过这样的决心,等下次不管是谁来提亲,只要爹娘满意,她都答应。可想归想,没过几天,媒人来了,她又变卦了。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家里来串门子的,只要是来人了,她就疑心是来给她当媒人的。从人进屋到离开,她都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一听到有要说起这事的迹象,她就赶紧搭话,把话题差开。她这样防备两年多了,还真见效果,不但来说媒的没有了,就连来串门子的人都少了。但这次属于意外,让她防不胜防。这桩亲事是她姐夫于志军介绍的,是在她毫无警觉下突然说起来的,搞得她措手不及。自从姐夫说过此事这半个月来,瑞芹几乎都不跟他说话了。她对姐夫似乎有一股子怨气,姐夫把她介绍给他们矿长的儿子,而且把那个人说得天花乱坠的,鬼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打算。
瑞芹是上山来摘豆角的,她家的豆角长在高粱地里。这几年,合庄早就没人再种高粱了。李老疙瘩在地头上种这二分地的高粱,就是为了豆角的生长。豆角把蔓子爬在高粱秸上,这样就不用给它搭架子了。这算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李老疙瘩在种地时,基本上都保持着一举两得的原则。西瓜地里间种上些芝麻,黄豆地里带上几棵冬瓜,他耪地时,兜里揣着大萝卜籽,发现哪条笼上缺苗,就在那个地方撒上几粒。到秋天,别看他没大面积地种,但家里是哪样东西也不缺。
瑞芹刚进高粱地,就弄了一身的露水。她发现自己来早了,她本来是想等到九点多再来的,她怕呆在家里,爹说个没完没了。她从地里退出来,拎着筐子在地头上站着。过了十多分钟,东头老葛家的几个娘们往这边来了,瑞芹怕跟她们说话,这些人一说话就没正经的,东扯葫芦西扯瓢的,跟她们在一起说话,稍有个不留心,就会让她们抓着话柄,告诉个满城风雨的。瑞芹有些烦她们,她又钻进到地里头。好再高粱种的稀疏,她每向前走几步,都先用手里的筐子四周撞一撞高粱秸,露水就哗地落下来了,她猫着腰,围前左右地摘起来。
瑞芹刚摘小半筐豆角,她姐姐大芹就来了。
大芹站在地头上喊她的名字,瑞芹答应一声,大芹就寻着声音过来了。她走的这条路线,是刚才瑞芹走过的,已经没有露水了。大芹也挎着个筐子,显然也是来摘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