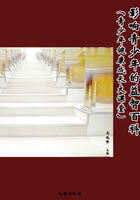赵奎的头刚挨到枕头上,电机的叫声又一次传入耳骨,他觉得根本不像是二梅说的那种错觉。为了验证这种声音的存在,他把枕头扒拉到旁边,把褥子撩起来,让耳朵贴在炕上。他听老人说过,狗就是靠着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才能听清楚远处的声音。果然,从炕上传来的不止是电机的叫声,还能感觉得到电机旋转时的丝丝振动。
赵奎再次坐起来,他穿上棉袄棉裤,从枕头旁拿起手电。他没开灯,他怕把二梅吵醒后,又得骂他神经病了。这半年来,二梅的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骂人,特别是她累的时候。好像只有骂几句,才能解除她的疲劳。
赵奎打开房门,便确定那声音的确存在了。电机安装在门房子里,那熟悉的声音就是从门房子里传出来的。赵奎顾不得关好房门,便向大门口跑去。在跑到院子当中时,被啥东西绊了一下,险些摔倒在地上。他回头用手电晃了晃,见是一只鸡食槽子。自打加工厂开业以来,每天都能从那里打扫出很多粮食和米糠,赵奎便到集上买回五十来只鸡崽子,用木板钉了七八个鸡食槽子。原来这些鸡食槽子成排地摆放在西墙跟下,这两天刮大风,刮得满当院都是了。
在呜呜的北风的间隙里,赵奎听出来了,正在转动的是那台粉碎机。赵奎的这个加工厂里有两台机器,一台是粉碎机,另一台是碾米机。这两台机器虽然电机是一样的,但由于传动用的皮带不同,发出的声响便不一样了。粉碎机用的是三角带传动,发出的声音是嗡嗡的,而碾米机用的是宽皮带传动,发出啪啪的响动。
赵奎从裤袋里把钥匙拽出来,握在手里。自从加工厂开业以来,这把钥匙就没离开过他的身上。赵奎用自行车的气线把钥匙拴在裤腰带上,只需要轻轻地一拽,就能够到门锁了。只是这种方法在方便操作的同时,也有弊端。有时候打开门后,一不注意,钥匙弹回来,就会崩到肚皮上,抽得肚皮很疼。
来到门前,赵奎用手电找到锁孔,把门打开。这次,他又让钥匙抽到肚皮了。但他并没感觉到疼痛,或者说他顾不上去感觉疼痛。他先去把电闸关掉,才到墙边找到屋里电灯的拉绳。拉亮电灯,他疾步走到那台粉碎机旁,伸手摸了摸电机,他的手被烫得倏的一下抽回来了。他又去摸粉碎机的外壳,也有些烫手了。他啪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大声地骂道,咋出你这么个你猪脑袋,这半宿得浪费多少电费?说完,竟气得蹲在地上。赵奎生气时打自己嘴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二梅说从打他们结婚那时,赵奎就这样。
赵奎很在乎每个月的电费,他把节能降耗当成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去抓。赵奎这样做,并不是他有着怎么强的环保意识,也不是他有着什么忧国忧民的思想,他就是心疼钱。上个月,他把六张通红的老头票交给村里电工,心疼得一晌午都没吃饭。按说赵奎的这个加工厂效益不错,不但合庄的人在这里加工,连围前左右村子的人也来这里加工。问题是他收不到多少现款,他在办这个加工厂时,在合庄借了两万多块钱,庄上四分之三的人都是他的债主。
赵奎本来没打算开这个加工厂,他会点瓦工活,这些年一直都跟着建筑队干。今年春天,他去沈阳建筑工地干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从绞手架上摔下来了。他被送进医院,大夫说只是扭伤了腰。在医院住不到半个月,老板给他七千块钱,把他赶回来了。赵奎当时挺高兴,认为这下摔得很值过,一个月得了别人半年的工钱。结果回来后才发现,这腰呆着时和好人一样,但一干起活来,就变成伤腰了,使不上劲,一用点力气就疼。且别说是干庄稼地里的活计了,就是晚上干被窝里的那点活计,他都是咬牙切齿的硬挺。可是一个大老爷们,总在家里呆着也不是个长法子,况且他儿子正在念高中,吃钱的地方多着呢。赵奎天天坐在当街大门口上想来钱的道,他看到每天都有人套着驴车拉着粮食去镇上加工,他的眼睛一亮,觉得合庄的确需要个加工厂。而且加工这个活计,也正适合他,每天就是推拉一下电闸,再有就是收钱了。
主意打定之后,赵奎托人打听一下,办这个加工厂得投资三万多块,而他手头里只有一万多块。赵奎就买上几盒好烟,揣在怀里,挨家挨户地去窜门,把他的想法和困难跟老邻旧居们说了。令他感动的是,乡亲们都很支持他,纷纷解囊相助,有的借给他千头八百的,也有借给他三头两百的。赵奎怕时间长了记不住,还专门设立一本帐。这些人在借给赵奎钱时,都说这些钱不用还了,反正日后得在你那加工,就顶加工费吧。从开业那天起,赵奎设立的那本应付款帐竟然成了往来帐,凡是借给他钱的人来加工,都在顶帐。赵奎所能收到的现款,只是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家和外村子来加工的。这样,他每月收到的现金也只够交电费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够,还得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上卖一些。
赵奎在地上蹲了一会,他先是懊悔自己的大意。他想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二梅知道,这要是知道了,耳根子半个月都不得清净。他知道二梅比他还看重钱,在办这个加工厂时,二梅听说得借两万多块钱的债务,就吓得说啥也不让他办,说这要是赔了,家里就得卖房子卖地了。二梅这半年来,都没舍得买一瓶雪花膏。以前来月事时,她还用两天卫生巾,这段时间连卫生巾都不买了,就用穿过的破背心做几个布垫,来回地换洗着。
赵奎从地上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他越想又越觉着不对劲,自己关门之前怎么会忘记关电机呢?电机又不是电灯,忘记关灯属于正常,因为电灯悄无声息的,而电机这玩艺,叫呼拉欢的吵着,即便是自己的耳朵让电机振得不灵敏了,那二梅的耳朵呢?她能听不见吗?门房子离他们住的正房也就二十多步远。况且,吃过晚饭后,二梅来这里插过大门。加工厂的门口就开在大门左边,想去关大门,就得路过加工厂的门前。
想到这,赵奎突然觉得脊梁沟里嗖嗖地直冒冷气。他下意识地环顾一下窗户,他知道门是没问题的,门是他刚才亲手打开的。窗户上除了顶部那个特意留出来的通风口之外,其余的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赵奎还是不放心,他挨个窗户都推拉了一遍。此时,他多么希望有那个窗户被人打开过,那样置少能证明这事是人干的。
赵奎检查完最后一个窗户,他彻底失望了。他那只按在窗户上的手和触电似的,拿不下来了,他感觉那电流正由手臂涌向全身。他眼睛盯着门口,想跑出去,腿却像陷在泥潭里一样。等他扶着墙一步一停地从屋里移出来时,他看到正房的灯亮了,二梅正从屋里跑过来,边跑边系棉袄上的扣子。
二梅跑到赵奎跟前,她以为赵奎睡毛愣了,上来就推赵奎一把,没想到这一下竟把赵奎推了个跟头。赵奎咣的一下坐到地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二梅吓得叫了一声“妈呀”,赶紧猫下腰把赵奎拉起来。她问赵奎,你不是睡毛愣了?赵奎摇摇头。二梅又问,那你半夜三更的跑到这来干啥?是不是有人进院偷东西?赵奎又摇摇头。二梅扶着赵奎,她感觉到来自丈夫身上的颤料,她回头向加工厂里扫了一眼,没发现有啥不对,便说咱们先回屋吧,看把你冻得,都筛糠了。
他们走出两步,赵奎回头瞅了一眼,二梅也跟着回头瞅一眼。二梅说,还没关灯呢,你先回屋,我去关灯。说着就放开赵奎的胳膊,想往回走。赵奎一把抓住她,小声地说,别去,闹鬼了。
二梅听后,嗷地一声叫起来。叫到半道,便赶忙用手把嘴捂住。从门房子走到正房,二梅回头看有四五次。赵奎感觉来自二梅身上的颤料更明显一些。
两个人回到屋里,二梅把赵奎扶到炕上,把被子给赵奎披上。赵奎说,你把烟给我拿来。二梅从柜上把旱烟口袋递给他。赵奎说给我找烟纸啊。二梅又从柜上把一本儿子用过的作业本递过来。赵奎撕了一张一寸多宽的纸条,平放在左手的掌心上,右手拿起烟口袋,往纸上倒烟未。这个动作赵奎训练至少有二十多年了,以往他摸着黑都成完成。今天他也完成了,只不过倒到炕上的比倒在纸上的还多。赵奎费了很大气力才把这棵纸烟卷好,他又叫二梅,快给我找火。二梅又从柜上把打火机拿过来。赵奎看二梅的样子,好像比自己更紧张。本来烟口袋和打火机就放在那个笔记本上,这三样东西是一个系列的,缺了哪一样都抽不成烟,二梅只要端着笔记本就可以一次性的拿过来的。可她却拿了三次,而且是赵奎每要一样,她拿一样。
赵奎点上烟,抽两口,稳住神后,这才把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跟二梅说了。二梅边听边不住的盯着门口,门帘子每动一下,她就往炕里挪一下身子。等赵奎讲完,二梅早就龟缩到炕里的墙角上了。
这夜,赵奎家的灯一直亮到天明,两口子谁都顾不得心疼那点电费了。他们在研究咋办?最后二梅提意,说明天去镇上找“太阳佛”给看看吧。
天刚亮,赵奎两口子就出发了,他们怕一会来了加工的,就没法走了。二梅骑着自行车载着赵奎,自打赵奎摔着后,每次上集赶店的,都是二梅载着他。七八里的路程,他们不到一刻钟就赶到了。街上除了几家小吃部营业外,其它的铺面都还关着门。二梅说,咱们得买点香再去。赵奎说,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吃口饭吧。
两人进了一家炸油条的铁棚子,要了一斤油条和两杯豆浆。两个人折腾了大半宿,都饿透气了,谁也不看谁一眼,只顾低着头吃自己的。等吃到盘子还剩最后一根油条时,二梅往赵奎跟前推了一下,说你吃吧,我吃饱了。赵奎没客气,他伸手拿起来,刚咬一口,他看二梅在盯着炸油条的人。赵奎把手中的油条撕下一半来递给二梅,二梅的手动了一下,头也跟着摇了一下。赵奎又冲着炸油条的喊,老板,再给来半斤。
吃过饭,两人都觉得心里有底了。他们在街上绕了半圈,看见有一家商店开门了,就赶紧奔过去。赵奎买了一盒香,他让老板给找个方便袋装上。老板找个白色的方便袋递过来。赵奎说没有黑色的吗?老板说没有。赵奎说那给我找张报纸吧?老板瞅赵奎一眼,说报纸也没有。赵奎抬眼看见二梅的围巾,他对二梅说,把围巾给我使一下。二梅不情愿地说,你非得包上干啥?这有啥寒碜的。赵奎瞪她一眼,没吱声。二梅把围巾解下来埔到柜台上,赵奎把香包裹好,出了商店。
赵奎两口子来到“太阳佛”家,那个看香的老太太刚洗完脸。没等赵奎两口子说来意,老太太先开口了。她说我知道你们该来找我了。咋的了,家里出啥事了?赵奎就赶紧把事情经过跟老太太说了一遍。老太太说,你等一会吧,我是“太阳佛”,得等太阳出来了我才能看。说完,就让她儿媳妇给她梳头。
等太阳爬上墙头,赵奎下地把香烧点着,刚插在香炉里,“太阳佛”就有了感应。老太太先是不停地打哈欠,之后开始伸胳膊伸腿。赵奎两口子刚跪下,就听老太太大喊一声,我来了。老太太开始正襟危坐,“太阳佛“问,你家有哪位仙家吗?赵奎赶忙回答说没有。“太阳佛”又问了一遍,赵奎还回答说没有。这时,二梅轻轻碓赵奎一下,她对“太阳佛”说,有。“太阳佛”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都看到有了,你生说没有。你知道是啥仙吗?二梅说知道,是黄仙。太阳佛问黄仙住在哪儿?二梅说,就在我家的柴禾垛里。“太阳佛”再问,说你们得罪过它们吗?二梅想了想,说得罪过吧,前天我去抱柴禾,把他们吓跑了。“太阳佛”听完后,合掌念了几句咒语,然后挥动着胳膊做个砍的动作。“太阳佛”的手再次抬起时,突然向后一仰,咣地一下倒在炕上,好半天才睁开眼睛,对赵奎两口子说,不成啊,这几位黄仙道行很深了,我只能在白天镇住他们,晚上,我管不了,看来只好供起来了。“太阳佛”说完,摸了一把脸,又打了两个哈欠,恢复了常态。并向赵奎两口子抬了抬手,示意他们可以起来了。
赵奎两口子站起来,老太太问他们供起来行吗?二梅点头说行,不行咋着啊!赵奎也跟着点头。老太太便拿过一张黄纸,三下两下折成一个有座子的牌位。老太太的儿媳妇从柜上拿过支碳素笔来,老太太把牌位放在膝盖上,写上“奉供黄仙之神位”几个字,然后把牌位递给二梅,说回去找个肃静的地方供上,初一十五上供品,烧香。老太太又特意嘱咐二梅,说以后你家的那个柴禾垛只能往上添柴禾,不能往下撒柴禾,那是黄仙爷的房子,你动人家的房子,人家能乐意吗?老太太说完,倚到炕头上,眯起眼睛休息了。二梅用头巾包好那个牌位,老太太的儿媳妇收完劳务费,把赵奎两口子送出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