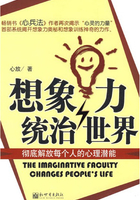赵奎被惊醒后,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便一下子坐起来,从他老婆二梅的脚底下爬到窗台前,把耳朵贴着玻璃上,又听了一会。他还是不相信,就推醒二梅,说你起来听听,我总觉着咱家的电机在叫。二梅翻个身,没好拉气地说,那是你的耳朵有毛病了,这半夜三更的,电机叫啥?电机又不是公鸡。二梅说完,把被子住上拖了拖,蒙住头,接着睡了。赵奎在窗台上扒了一会,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的冷风就像一些虫子,顺着他的前胸爬向后背。赵奎觉得二梅的话有些道理,这阵子,他天天在加工厂里听电机叫,吵得耳朵里像钻着一个苍蝇,总发出嗡嗡的声响。
赵奎摇摇头,用手拽了拽耳朵,感觉那声音的确没了。他爬回到被窝里,撅着屁股,头拱在枕头上,身体被一团温暖立即包围起来。这种姿势和感觉,让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二梅身上的某个地方。他往二梅跟前移了移身子,手贴着褥子摸了一下。二梅把被子裹在身上,靠着他的这边,全都压在身下,连手都塞不进去。赵奎的那一丝冲动就像箭射到盾牌上,咣地一下被挡回来。他侧过身子,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