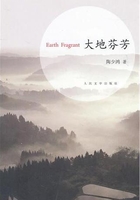他说,姐夫,就等你了。
我迭忙点头,说对不起,中间有一段路正在施工,不太好走。
他从和我握手那一刻起,眼睛就一直在研究着我的眼镜。直到我的手又重新抖动了一下,他才张开那双有力的蚶壳,把我的手放出来。
他说,姐夫,你就这么来了?你咋不把录像机扛来,给他们曝曝光,也给小辉我们俩出出气,看他们以后还敢张狂吧。
我说那可不行,我是来旁听的,不是来采访的。
他嘿嘿地笑了一下,说,那也得吓唬吓唬他们。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说我们这边来记者了。他说完就要往法庭门口走。
我一把拉着了他,说别别别,这事不能说,说出去不好。
他说姐夫你怕他们啥呀?咱们这个记者又不是假的,我在电视上都见过你。
听他一口一个地管我叫姐夫,我猜想这一定是小辉的本家兄弟吧。小辉的老家是农村的,以前我见过他家的一些亲戚,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
我问他,你是?
站在我身边的马艳捅了小辉一下,又指了指那个男的。
据我的妻子马琳说,她妹妹马艳以前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之所以变得少言寡语,跟她念高中时谈恋爱有关。因为光顾着谈对象了,所以没考上大学;因为没考上大学,那个考上大学的对象也跟她吹了。从此,话就一天比一天减少,自打嫁给小辉后,就很难听到她主动说话了。
小辉感觉马艳捅他,这才转过身,指着那个男的对我说,哦,姐夫,这是我的证人。
听完小辉的介绍,我又重新伸出手。不过,这次我伸出去的是双手,证人伸出的是右手。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由刚才的活蚶子一下子变成了死蚬子,两边是白色的壳,中间夹站一块腐黑的肉。
我说,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晌午得跟你多喝几杯。
我所以如此重视这个证人,不仅仅是他决定这场官司的结果。小辉给我打电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起过他,我很敬重他的为人。
二十天前,小辉给我打电话,说他被人打了,现在正在住院。我问他伤得重吗?他说伤得不重,只是脑袋有一块磕出血了,身上有几处蹭破点皮。我问他谁干的?他说一个开铁矿的,姓刘。我问他因为啥?小辉说在那个山上,还有一个开铁矿的,姓李,他雇我的车上山拉矿石。我走在路上,从山上下来一辆拉矿石的四轮子,道太窄,那辆车的刹车又不好使,我们在错车时,四轮子翻到沟里去了。我问伤着人没有,他说没有,车上就一个司机,跳下来了。我半开玩笑问小辉,是不是你把人家撞到沟里去的?他说不是,他说我们俩的车根本就没刮边,是他自己溜到沟里去的。我说那你们怎么打起来了?小辉说那个姓刘的矿主认为这条路是他开出来的,我的车就不应该在这条路上走,他让我赔他的四轮子,我不赔,他们就动手打了我,其实他是把对李矿的怨气撒到我的身上了。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小辉说我打算告他们。我说既然咱们有理,那就找个律师,起诉他们不就完了吗?这还有啥可犹豫的。小辉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姓刘的矿主在这一带有钱有势,他说我告到哪也是白扯,法院的那些人,他在好几年前就都摆平了。
我是个很爱上火的家伙,听了小辉的话,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你明天就去起诉他,我倒要看看,他是怎样把法院的那些人摆平的。小辉听了我的话,虽然嘴上说行,说明天就去请律师,但还是一再地追问,问我在平县法院有没有认识人。我说这样的事情还用找认识人吗?他说得找人啊,我让人家平白无故地打了一顿,要是官司再打输了,以后他在这片就没法呆了。为了给小辉增加底气,我糊弄小辉说,没事,你告吧,到时候我给你找人,我认识你们县的政法委书记。
在小辉挂断电话前,我突然想起来,我问他有目击证人吗?小辉说有,是他早上从劳务市场雇来的一个装车的民工。我说这样的人可靠吗?小辉说这人不错,我在山上挨打时,他就挡在我的前面,还被他们踢了两脚呢。我上医院的时候,就是他把我送去的。他在医院守候我一天,连工钱都没要。小辉还给我讲了那天早上他去劳务市场跟这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小辉说他一眼就相中了这个人了,他和别的民工不一样。别的农民工看见他来了,都一窝风地扑了上来,跟他讲价、砍价,狮子大开口。而这个人却站在很远的地方,扛着一把平板锹,笑呵呵地瞅着。小辉说不用看别的,就看这把平板锹,就知道他是个实诚人。那锹是最大号的那种,和小簸箕似的,溜光锃亮。小辉说现在的民工也都学得很奸滑了,出来干日工的,哪还有扛这种铁锹的。小辉问他多少钱一天,他问小辉想给他多少钱一天,小辉说三十。因为别的民工都要五十,小辉说他给他留着讲价的余地。没想到他把铁锹咣地往地上一戳,说中,但晌午你买饭的时候,得多买一碗,少了我吃不饱。说完竟嘿嘿地自己笑了起来。小辉还想往下说,我就打断了他,我特意地嘱咐小辉,说这个证人的证言很重要,你一定跟他约好,请他出庭作证。
之后小辉又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只是先向我通报诉讼的进展情况。每次在临挂断电话之前,都提醒我给他找认识人。我对此事一直也没放在心上,我觉得,按照小辉的说法,本来应该理直气壮的事,干嘛非要搞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前天晚上,小辉又给我打来电话。这次他竟单刀直入地追问我给他找了人没有?我只好告诉他,说早就给你找了,你们县的政法委赵书记答应过问此事。
小辉听了,接连说了四五声谢谢,说这样他就放心了。
我以为他放心了,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他还不住地追问,说政法委书记怎么说的。
没办法,我只好接着编瞎话。我说政法委的赵书记说,只要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保证你的官司一定能够打赢。
小辉听了,沉默了片刻,他好像对赵书记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试探着问我,咱们要不要给赵书记送点礼?
我说不用,多大个事,赵书记是咱哥们,关系当当地,你就放心吧。
为了转移话题,或者说尽快地把“赵书记”从小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我开始转守为攻。
我问小辉他在住院期间的各种手续和收据是否齐全?
小辉说他朋友的妻子是医院的外科主任,手续和收据都全。
我再一次问到那个证人。
小辉说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他觉得这个人挺直性的,都三十二了,还没成家。他所以没成家,就是因为他母亲。他家里只有他和他母亲两个人,他挺孝顺,他母亲有病,他每天骑自行车上城里来找活干,就是为了给他母亲买药。小辉说这些天他没活的时候,总到医院来看我,我都请他吃了六顿饭了,出庭作证绝对没问题。
我的提问刚停下来,小辉说,姐夫,到开庭那天,你来一趟行吗?
我说我去能干啥,我也不懂法律,也帮不上你啥忙,我去了,也就是个旁听。
小辉说,你是市里电视台的记者,你往这里一站,我们这里的法官可能都认识你,到时候真有个啥情况,你好帮我出面处理一下。
我说不行,我单位最近事特别多,可能是走不开。
小辉说就一天的工夫,你早上开车过来,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听律师说,要是顺利的话,一上午就能完事。
我说主要是我去不去没啥实际的意义。
小辉不吱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