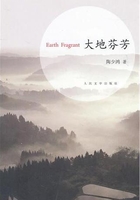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我不记得那次是谁带我去的了。宴会是一个年轻女讲师举办的,她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出版了,于是她就举办了这场开放式宴会,受到邀请的客人都可以带朋友一起去。那天去了将近五十位客人,大多数都是学者。宴会上只有红酒和乳酪,我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就坐在角落里,静静观赏整个宴会的场面。女主人好像叫贝蒂,至于姓什么,我不大记得了,年龄大概二十五岁,看上去不像是位成熟女性,倒更像个学生。她留着一头短发,连耳朵都没遮住,戴着眼镜,门牙有点外凸。从外表判断,她应该是个老烟鬼。她上身穿着一件褐色毛衣,显得有些激动,好像有话要对所有客人说。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请问您是?’我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她,她对我的身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接着问道:‘你练瑜伽吗?’我说:‘我觉得练瑜伽很没意思。’‘你完全错了,’她说,‘瑜伽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早晨和晚上各做半个小时,身心都会得到锻炼,你会感到像能驾驭整个世界一样。试试吧,你会体会到它的妙处的。不需要去买教材,我可以免费给你上几课。你请我吃饭就行了。’
“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她,她看了看,说道:‘好的,我住得不远,就在国王大道那边,那儿有许多挺不错的酒吧和餐馆。我没有名片,把电话就写在你的名片上吧。我通常晚上五点从学校回家,你有空就给我打电话吧。’
“我并不想表现得太迫切,好像我很想接受她的提议似的,所以之后那两天我没有打给她。但我一直想着她,很想进一步了解她,这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第三天晚上我就给她打了电话,邀请她前往我的公寓。她立刻就答应了,还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上瑜伽课,你要负责晚餐。’我急忙出门,买了几瓶陈年波尔多葡萄酒,把客厅收拾好等着她。
“晚上六点半,她如约而至,穿着浅灰色衬衫和黑色长裙。她在我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参观了一遍我的公寓。‘还不错,’她说,‘你一个人住吧。’
“‘嗯,我喜欢一个人住。早晨自己做土司,自己泡咖啡;中午就开一罐西红柿汤;晚上就出去大吃一顿,九点半回家。现在需要我为你倒些好酒吗?’
“‘现在不用,’她回答道,‘先给你上瑜伽课吧。’
“‘行!开始吧。’
“她在地毯上坐下来,深呼吸,做了个莲花式动作,接着是弓式。她把脖子拱起来,看向天花板。她的胸部有点儿小,两个乳头顶着衬衫。‘懂了吗?’她问道。
“‘我腿弯不下去,做不了莲花式,而且我觉得这似乎没什么效果。我以前试过练倒立,可差点把脖子都弄断了,不像我们的总理尼赫鲁,他每天都在做倒立,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对她说。
“‘这动作很简单,而且很有益处,’她说道,‘我做给你看看。’说着便双手支撑着头,慢慢朝上竖起双腿。她的裙子翻下来,遮住了脸,她的腰部到脚趾全露在外面,内裤上还贴着卫生巾。‘现在是生理期,’她解释道,声音从翻过去的裙子下面传来,‘还有几天。真烦人。’
“她慢慢放低身体,深深呼了几口气说:‘我准备尝尝酒了。’她掏出一支烟,接着说:‘我要先抽根烟,有些人可能不抽烟,但他们会酗酒。’我们坐下来,喝了点儿酒。我问她在哪儿教书,她问我做什么工作。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那瓶波多尔葡萄酒也喝得一滴不剩。
“‘我们去哪儿吃晚饭?’我问她。
“‘就在附近吧,那里有家酒吧相当不错,叫世界末日。酒吧间在底楼,餐厅在二楼。’
“她挽着我的手臂去了世界末日。酒吧间人满为患,酒保都认识她,他们互相打了个招呼。我们上楼来到餐厅,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国王大道的景色。服务员送来菜单,她似乎也认识贝蒂。‘今晚想吃点儿什么,女士?’贝蒂扫了一眼菜单,说道:‘你决定吧,把你认为最好的给我们上过来。不过,先来瓶波多尔葡萄酒。’
“她点了根香烟,从鼻孔里吹出烟,然后靠着椅子说:‘这感觉真是棒极了。’服务员拔去瓶塞,往我的酒杯里倒了点儿,让我先尝尝。我抿了一口,在嘴里细细品了品,说道:‘非常好。’她为我们倒满酒,把酒留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我也感觉棒极了,’我说,‘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谢谢,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下对方,’她说。
“‘你可是个大忙人。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吧,我随时恭候。’
“她拿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记下我的电话。‘好的,这次该我主动了,’她说。
“服务员端来了晚餐,有牛排、土豆,还有洋葱面包。‘祝两位好胃口。’她说完就离开了。我已经饿了,红酒更激起了我的食欲。”
贝格打断他,问道:“你吃了牛肉?这不是犯了锡克教的禁忌吗?”
“对,”布塔说道,“我就喜欢违犯禁忌。你肯定从来没吃过新鲜猪肉、猪肉火腿和熏猪肉吧,它们可都是美味啊。如果你有勇气,就尝尝吧。”
“天哪,天哪!”贝格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这都是穆斯林的禁忌啊。你还是继续讲你们的故事吧。晚餐后怎么样了?”
“没发生什么,不过,临别时她吻了我的嘴唇,然后用法语说:‘A bientot,’意思是很快就会再见。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不过我还是一直待在家等她的电话。过了三天,她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空。‘我准备打包把晚餐带过来,是墨西哥菜,这样我们就不用出去吃了。你准备酒,行吗?’我说:‘行。’于是我准备了两瓶意大利红酒,一瓶吉安蒂,一瓶巴罗洛,等她上门。
“她晚上六点半就到了,带着一大盒食物,还背着一个帆布包。我吻了她很久,表示热烈欢迎。她把东西放在地板上,叫我把装晚饭的饭盒放进厨房。‘这要加热才能吃。加热时,我们可以做做瑜伽,然后喝点儿酒。’
“她又做了一遍上次那个倒立姿势,裙子翻下来,遮住了她的脸。这次她没穿内裤,从脚趾尖到腰部,包括那玩意儿和肚脐眼,我全都看到了,我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重新站好,然后坐到我身边,把手放到我两腿中间。她感觉我那地方有了反应,对我说道:‘我知道,你喜欢刚才看到的东西。’接着,她三两下就把衣服脱掉了,我们在沙发上发生了关系。事情结束后,她没穿衣服,赤裸着身体坐在那儿抽烟喝酒。‘你把晚饭热一下,我去洗个澡。’她走进浴室,衣服还摊在沙发上。冲完澡回来,她坐到沙发上,点了根烟,又喝了一些酒。
“晚饭前,我们又亲热了一次。这次我坚持了更长时间,她到了高潮,身体不停地颤抖,还发出呻吟声。之后我们吃了她带来的墨西哥晚餐,她还是没穿衣服。我们喝完了第二瓶酒,似乎都有些醉了,还有些累。她靠着我,我们一起在沙发上躺了很长时间,后来实在困了。桌子都没有收拾,我就带她进了卧室,像她一样把自己的衣服全脱了。她光着身子睡在我怀里。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们又做了一次,她又达到了高潮。我为她准备了早饭,是咖啡和奶油土司。她吃完就去了学校,临走时告诉我说晚上回来。
“这成了我俩的相处模式。那时离我返回印度还有一个月时间。整整一个月,她都和我在一起,一起喝酒,每天都干那事儿。她在屋里喜欢光着身子。她说,穿衣服是为了外出,在家就该什么都不穿。她裸露的身子看起来跟男孩似的,至今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贝格,想象一下,有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整天在你身边走来走去,而且每天倒立两次。我告诉你,贝格,不管是又卷又黑的长发,还是水灵灵的杏仁眼或猩红的嘴唇,甚至连隐在毛丛中的女人阴部,这些男人实现欲望的地方,都比不上从后方看那个浑圆的美妙臀部产生的感觉,太诱人了,”布塔把手掌拢成环状,用来比画自己描述的那种线条,“这可以让本来性无能的男人都产生反应,何况那时我并没有性无能。她那时真是把我全榨干了。”
“你和她后来还有联系吗?”贝格问道。
“联系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和一个教授结了婚,生了几个小孩;再后来又离婚了。我听一个也认识她的朋友说,她后来辞职了,也没再写作,成了全职瑜伽教练。我还听说她来过一次印度,到浦那的几家会所进修瑜伽高级课程。她没和我联系,我和贝蒂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故事很不错,”贝格说,“等周围没仆人时,我要讲给莎吉娜听,她肯定会喜欢这个故事。”
“她一定很看不起我。”布塔说。
“绝对没有,”贝格说道,“她认为你是个生活经历丰富多彩的锡克人。”
在东方,大家认为鞋子代表了耻辱,因为它们穿在最下面,常常沾染了灰尘。在进入神圣的场所之前,大家首先要脱掉脚上的鞋。在印度次大陆,大家在进入亲戚朋友家之前,也要在门外脱掉鞋子。因此,大家发生争吵时,会立即脱下鞋子砸向对方,这就叫做扔鞋子,也就是“鞋击”,是最严重的侮辱方式。如果够不着对方,或是那人被保护得密不透风,那么,就算离得再远,也可以使劲儿将鞋子扔过去,这样做也算是异曲同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有个伊拉克记者就曾经对他这么做过。那个记者抗议美国一口咬定伊拉克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借此对伊拉克进行侵略。美国政府随后承认,他们并没有找到伊拉克犯有这种罪行的证据。
不过,以扔鞋表示抗议,损失可不小,扔鞋之人会失去一双鞋。若扔鞋之人因殴打和攻击他人而受到审讯,扔出的那只鞋就会立即遭到没收,成为证物。他不得不再买一双新鞋,剩下的那只成为纪念品,提醒他记得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2009年4月7日,在德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一位长须飘飘的年轻记者朝部长扔了一只鞋,这位记者名叫贾奈尔?辛格,是一名锡克教徒,在一家名为《觉悟日报》的印地语报社工作。可惜这位老兄不是神射手,没有砸到部长,自己却立即遭到逮捕,也被报社解雇。这完全是自作自受。部长慷慨地原谅了他,说自己深深地感受到了辛格所处阶层承受的痛苦。贾奈尔?辛格一夜之间成了锡克教的英雄。不仅如此,他尽管没有砸到部长先生,但却达到了自己预想的效果。他立即成了印度全国上下谈论的焦点。毫无疑问,这件事也成了“日落俱乐部”的热门话题。
德里的4月是个不伦不类的时节。你不知道冬天和春天有没有结束,也不能确定夏天到来与否。今天可能像腊月那般寒冷刺骨,而明天可能就是炎炎夏日。同样,有一天可能风雨大作,甚至下起冰雹,而接下来的一周,却刮起炎热的沙漠风和沙尘暴。天气不仅仅是在和人类,也是在和大自然做游戏。4月,木棉脱去了果荚,果中的棉絮迸发出来,随风飘落一地。紫铆的花期很短,很快就又长满褐色斗篷叶。珊瑚花也一样。不过,蓝花楹彻底绽放了。一直到月底,在道路两旁和街心转盘,橙色和黄色凤凰树都在尽情盛开,阔叶合欢树也吐蕊开花。
梵文作家跋娑在其作品《爱的魔力世界》中生动地描绘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四月:
看这旖旎多姿的世界,多有魔力!当大地披上夜装,炎热消逝;
晚风轻抚这奇特的世界,渐渐为它吹走额上的炽烈,静静地为它戴上闪耀的星光之链,将勇气洒向这安眠之城的每个角落,让年轻的情侣水乳交融。
贝格想和两位朋友聊聊那次扔鞋事件,他觉得这会激起沙玛和布塔的愤慨,因为这件事牵涉印度教和锡克教二者的矛盾。他作为穆斯林信徒,可以保持中立,只需听他们说话就成。结果正是如此。
“两位老兄,锡克教徒多年前曾遭到屠戮,可那件事和这位部长根本没有关系。请给我讲一讲,是什么原因刺激了那位年轻的锡克族记者先生,促使他他将鞋子扔向部长先生?”
沙玛敏捷地回答道:“锡克人反应迟钝是出了名的,无论什么事,他们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作出反应。他们头脑发热也是出了名的,一旦失去冷静,他们便会狂怒不已,攻击身边一切人和物。我对这条新闻并不惊讶,我对自己说,归根结底,他就是个锡克人。”
布塔觉得自己必须反驳沙玛的话:“专家,你不觉得这位仁兄虽然没砸到内务部长,却砸中了他心中真正的目标吗?国大党推荐了两个曾参与杀害锡克教徒的家伙当候选人,让他们参加议会选举。那位记者这么做,唤醒了大家的良心,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集会。国大党已被迫取消那两人的候选人资格。你还认为这种行为是反应迟钝和不合时宜吗?”
沙玛和布塔一阵唇枪舌剑,过了一会儿,两人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但贝格还没看够热闹,便又开始煽动布塔:“布塔兄,你还要憎恶那些印度教教徒多久呢?为什么不选择原谅和遗忘?”
“我会一直憎恨下去,除非那些罪人受到惩罚!”布塔答道,“你知道吗?在参与对锡克教徒进行迫害的数千人中,只有不到二十人受到法律制裁。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生气。而印度教教徒却还在继续向世界宣告他们热爱和平。给他们一次表现机会,你自己去看看他们究竟有多热爱和平吧!你是个穆斯林,你应该知道的,自从印度独立以来,他们残杀了多少穆斯林?告诉我。”
“成千上万,”贝格承认道,“我们早已习惯了惨遭杀害。他们摧毁巴布里清真寺时,杀了我们几千人;戈特拉车站里,一节火车车厢发生火灾,又夺走了几千位穆斯林的生命。但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习惯了。”
沙玛感觉这两人正在合伙对付自己,便决定迎头痛击他们:“布塔兄,请你告诉我们,宾德兰瓦莱声称每个锡克教徒都应杀掉三十四个印度教教徒的时候,他的信徒在全国各地把印度教教徒拉下公交车射杀的时候,你又有过什么抗议吗?有哪个锡克教领袖说过一句抗议他的话?没有,他们都畏惧他,怕得要死,因为他从来不怕自己的言论遭到排斥。现在他去世了,你敬仰他,将他视为圣人和烈士。”他又转向贝格说道:“你们穆斯林想得到巴基斯坦,不过大部分穆斯林并不住在巴基斯坦,而是住在印度。如果我们做了巴基斯坦人对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所做的事,你们早就全都被赶出这个国家了。我们数量占了国家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可我们的总理和计划委员会主席都是锡克教徒,内阁部长、邦首席部长和各邦领导要么是锡克教徒,要么是穆斯林,而我们得到的只是忘恩负义。我问你,这公平吗?”
沙玛知道自己在这场辩论中占了上风。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可是个婆罗门,而婆罗门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就如沙玛常在演讲中提到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就好比人体一样。婆罗门是头部;手臂和躯干则是刹帝利,包括武士族群的拉齐普特人、马拉地人及锡克人;盆骨和大腿是吠舍,比如商业族群的巴尼亚人和玛瓦瑞人,他们负责国家的经济;首陀罗则是支撑起整个身体的双腿和双脚,他们从事琐碎的工作,担任清洁工、皮匠和尸体搬运工。这是按照他们应有的功能来划分的,这样,种姓制度才不会解体,不会成为过时的垃圾。
但不管怎样,沙玛虽然在精神上赢了两位朋友,但觉得自己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应该安慰安慰他们,毕竟他很珍惜这段友情:“兄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事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重要的事情是要说真话,要不顾一切后果地捍卫真理。布塔,你常引用的那首关于真理的诗是怎么说的?”
引用别人的至理名言是布塔最喜爱的消遣。他清了清嗓子吟道:
真理真好。
当有人为真理而死,
你若不是勇于站上绞架的烈士,
最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