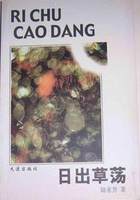时隔两年,当时的情形我已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络绎不绝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在盖茨比家进进出出。大门拉起一条绳子,有个警察守在旁边,挡住想看热闹的人,但附近的小孩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草坪进去,因此游泳池边总是有几个目瞪口呆的孩子。有个气定神闲的人——可能是个侦探——在弯腰视察威尔逊的尸体时,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这句言之凿凿的无心快语奠定了隔日媒体的报道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是噩梦——荒诞不经、琐碎无聊、兴致勃勃、无中生有。当米迦勒斯供认威尔逊怀疑他太太红杏出墙的证词曝光之后,我原本以为这个事件很快会演变成桃色新闻——但凯瑟琳非但没有胡说八道,居然还守口如瓶。她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她那双眼睛在修整过的眉毛之下坚定地看着警察局派来的法医,发誓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又说她姐姐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情。她说得连自己都信了,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仿佛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污蔑。所以威尔逊被说成是“因悲哀而行为失常”,于是这件案子变成了最简单的命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让我失望的是,站在盖茨比那边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告惨剧的消息开始,但凡有关于他的猜测或者具体问题,人们都会跑来问我。起初我既诧异又困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到他无声无息,安然地躺在他的房子里,我渐渐明白了:大家都来找我,是因为没有别的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完全没有兴趣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们发现他的尸体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黛熙打电话。但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出门了,而且还带着许多行李。
“没说去哪里吗?”
“没有。”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替他找个人。我真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安慰他说:“我会替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我会给你找个人——”
梅耶·沃夫希姆的名字并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地址,我打电话到查号台,但等我拿到号码,时间早就过了五点,那边没人接电话。
“你能再帮我接通吗?”
“我已经接通三次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那边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突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开始还以为是顺道来访的宾客,随即发现其实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是,当他们掀起那块薄布,惊恐地看着盖茨比,我仿佛听到他的抗议:
“喂,老兄,你得帮我找个人啊。你要努力去找。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有人开始问我问题,但我脱身走到楼上去,匆匆翻查他的书桌那些没上锁的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过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达恩·科迪的照片,象征着那早已被遗忘的风云岁月,从墙上望下来。
隔日清早,我派管家到纽约送信给沃夫希姆,我在信里向他打听消息,也敦促他赶紧坐火车过来。其实我在写信时就觉得这个请求是多余的。我原本以为他看到报纸肯定就会动身,也以为中午之前肯定能收到黛熙的电报——但电报和沃夫希姆先生都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除了越来越多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当看完管家带回来的沃夫希姆的回信,有种愤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要和盖茨比联合起来,鄙夷地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
这是有生以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人的疯狂行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现在没法过来,因为手头有非常重要的生意要处理,不能让这件事给耽误了。如果稍后有需要效劳的地方,请让埃德加送信告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悲伤得难以自持。
你真诚的朋友
梅耶·沃夫希姆
然后他又用潦草的笔迹补充:
葬礼的事情请让我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响起,总机说是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我以为黛熙终于打过来了。但话筒里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很轻,很遥远。
“我是斯拉格……”
“请讲,”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太让人意外了,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
“帕克那小子出事了,”他语速很快地说,“他把债券摆上柜台的时候被抓个正着。他们之前五分钟刚刚收到纽约的通告,上面写着那些号码。喂,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乡下地方……”
“喂!”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头,“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随即传来一声惊叫……然后在匆促的咒骂声中,电话被挂断了。
我想应该是在第三天,有封署名亨利·盖兹的电报从明尼苏达州某个小城发过来。上面只说发报人已经动身赶来,丧事等他到了之后再办。
那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表情沉重的老人,看上去非常无奈和消沉,身上裹着阿尔斯特长外套,尽管九月的天气依然很暖和。他的眼睛不断露出惊奇的神色;我从他手上接过布袋和雨伞后,他就不断地轻抚他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他把外套脱掉。我看他站不稳的样子,于是扶他到音乐室,让他坐下,同时让佣人去弄点吃的。但他不肯吃东西,手里拿着玻璃杯直发抖,牛奶都洒出来了。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消息,”他说,“芝加哥的报纸全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我立刻就出发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样找到你。”
他的眼神很茫然,不停地扫视着这个房间。
“那人是个疯子,”他说,“那人肯定是个疯子。”
“你想喝点咖啡吗?”我问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没事,卡……卡……”
“卡拉威。”
“唉,我没事。他们把小詹放哪了?”
我把他带到客厅,他的儿子就躺在那里,然后留下他一个人。有几个小男孩爬上台阶,正在往客厅里面看;我告诉他们来的人是谁,他们这才一步两回头地走开。
不久之后,盖兹先生打开房门走出来,他的嘴巴是张开的,脸上有点红,泪珠滚滚而下。他已经到了不再为死亡感到错愕的年纪,这时他第一次环顾四周,看到门厅如此宽敞豪华,门厅之后是连绵不绝的大房间,他的悲哀开始混进些许敬畏的骄傲。我扶着他走进楼上的卧室,在他脱下外套和马甲时,我告诉他所有安排已经推迟,等他来决定。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觉得你可能想把尸体运到西部。”
他摇摇头。
“小詹向来更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发迹的。你是我家孩子的朋友吗,卡……卡……?”
“我们是好朋友。”
“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你知道的。他只是个年轻人,但他的脑力很好。”
他边说边戳着自己的脑袋,我点头表示同意。
“如果他能活下去,他会变成了不起的人。像詹姆斯·希尔[96]那样的大人物。他会帮助建设这个国家的。”
“你说得对,”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去弄那绣花的床罩,想把它拉掉,然后硬邦邦地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那晚有个明显很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不肯说出他的名字,非要先问我是谁。
“我是卡拉威先生,”我说。
“啊!”他如释重负地说,“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如释重负,因为看来盖茨比墓前将会多一个朋友。我不希望葬礼变成报纸上的新闻,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所以我亲自打过电话给几个人。他们很难找到。
“葬礼定在明天,”我说,“下午三点,在这座房子。我希望你能通知其他感兴趣的人。”
“我会的啦,”他赶紧接口说,“当然,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见到的话,我会通知的。”
他的口气让我起疑。
“你自己肯定会来的吧?”
“嗯,我会争取的。我打电话来是想……”
“且慢,”我打断他的话,“你就答应来吧,怎么样?”
“哎呀,其实——实际上,我目前和几个朋友在格林威治[97],他们相当希望我明天陪他们。其实明天他们会去野炊。当然,我会尽量争取来的。”
我忍不住发出了“哼!”的声音,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接下来很紧张地说: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留了一双鞋在那边。我在想,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让管家把它们寄给我。你知道吗,那双是网球鞋,没有它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地址是……”
我没有听到他下面的话,因为我把听筒挂掉了。
在那之后,我真替盖茨比感到不值——某位接到我电话的绅士竟然含沙射影地表示盖茨比死有余辜。然而这是我的错,因为以前有些人经常借盖茨比的酒壮胆,然后恶毒地咒骂盖茨比,而他是骂得最恶毒的人之一,我本来不应该打给他的。
举行葬礼那天早晨,我去纽约城里找沃夫希姆;用其他方法我根本联系不到他。根据负责开电梯那男孩的指引,我推开那扇挂着“卍控股公司”[98]招牌的门,刚开始里面好像没人在。可是当我喊了几声“喂”也没人应答之后,隔板后面传出几句争执的声音,然后有个美貌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间的门口,乌黑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看着我。
“里面没有人,”她说,“沃夫希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半句显然是假话,因为里面已经有人开始跑调地用口哨吹起了“玫瑰经”。
“请跟他说卡拉威先生求见。”
“我又不能让他从芝加哥回来,对吧?”
这时门后有人大喊:“斯泰娜!”,那毫无疑问就是沃夫希姆的声音。
“请在前台留下你的名字,”她匆匆地说,“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
“但我知道他就在这里。”
她向我踏上一步,双手叉腰,做出很生气的样子。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她气势汹汹说,“我们他妈的已经受够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起了盖茨比的名字。
“啊!”她又从头到脚打量我,“你能……请问你贵姓?”
她消失了。片刻之后,沃夫希姆肃穆地站在走廊里,两只手都伸出来。他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用虔敬的口吻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很伤心,并递给我一根雪茄。
“我的记忆回到了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个刚从部队退役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了在战争中得到的军功章。他当时非常穷,整天穿着军装,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走进第四十三街的维恩布伦纳撞球厅,想找点活干。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吃过东西。‘走吧,我带你去吃午饭,’我说。他半个小时内吃掉了四块钱的饭菜。”
“他做生意是你提携的吧?”我问。
“何止提携!他是我一手栽培的。”
“哦。”
“他原本身无分文,是我从阴沟里硬把他栽培起来的。我立刻看出来他是个长相英俊、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跟我说他念过牛津之后,我就知道他值得好好培养。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他以前在那里地位很高。他刚出道就北上奥尔巴尼[99]帮我的客户解决了某些难题。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么亲密无间,”——他伸出两根胖手指——“总是在一起。”
我在想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是否也是他们联手干的。
“现在他去世了,”我隔了片刻之后说,“你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下午应该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倒是想去。”
“好啊,那就去啊。”
他含泪摇摇头,鼻毛随之轻轻地抖动。
“我不能去——我不能受这件事牵连,”他说。
“不会牵连到你的。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反正我不想受人命案子牵连。我要置身事外。年轻时我倒不是这样的——那时如果我的朋友死了,不管是怎么死的,我都会陪他们到最后。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但我不骗你——我会陪他们走完痛苦的人生路。”
我明白他决定不去也是有理由的,所以站了起来。
“你念过大学,对吧?”他突然问。
刹那间我以为他准备要跟我搞“光系”,但他只是点点头,跟我握手道别。
“我们要明白,讲交情要在人活着的时候讲,人死就没有交情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自己的原则是,人死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天变黑了;等我回到西卵已经飘起毛毛细雨。换好衣服之后,我走到隔壁,发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越来越为他儿子和他儿子的产业感到自豪,这时他有东西要给我看。
“小詹给我寄了这张照片,”他用颤抖的手指递过他的钱包,“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