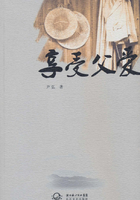拉贝次仁留一头长发,像女人一样被在肩上。有关他留长发的缘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拉贝次仁是画画的,大小也算是个艺术家——时下的艺术家不都留着长发吗?另外一种说法有点耸人听闻,说拉贝次仁的头上长了一对椅角,留长发是为了掩盖那对异物!
长了犄角的拉贝次仁当然已不在他的画室里,他在青海湖西岸的一个叫铁卜加的牧民大队里当上了大队副队长,时间也随之推移到了1970年左右。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拉贝次仁坐在大队办公室里念念有词,忽然想起昨天他派郭哇活佛去看守大队刚刚买来的两只种公羊,考虑到这个阶级敌人会不会坚守岗位的问题,他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他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径直往门外走去。
两只种公羊被关在离大队不远的露天羊圈里,郭哇活佛理所当然在羊圈门口坐着。昨天,副队长拉贝次仁来找他,站在离这个阶级敌人有十几米远的地方大声对他说:“老头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大队为抓革命促生产,买来两只公羊,要有人看守,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这是大队对你的信任,你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啦索、啦索!”郭哇活佛受宠若惊,即刻用先前别人在他面前经常表现出的举动点头称是,并伸出舌头表示敬畏。
郭哇活佛是铁卜加寺寺主。铁卜加寺有着300多年的历史。郭哇活佛的前几世经过苦心经营,才使这座格鲁派寺院在安多和康区有了些名气。谁曾想到了郭哇活佛这一世,寺院变
得残破不堪不说,并且让以前的忠实信徒,现在的革命小将们一夜之间砸成了平地。现在,这座寺院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被人们称作老头儿的郭哇活佛,而郭哇活佛此时却看守着两只种公羊。
拉贝次仁走近关着种公羊的羊圈时,远远看见郭哇活佛身披一床绵被抖抖地站在羊圈门口,脸上是早已准备好了的虔诚敬畏的微笑,微微低着头,等候着副队长拉贝次仁的检阅。
拉贝次仁到羊圈门口,几乎看都没看郭哇活佛一眼,径直往羊圈里瞅了瞅。他看见两只种公羊正在悠闲自得地啃吃着燕麦草,便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打击和批评郭哇活佛的几句“革命语言”咽到了肚子里。
拉贝次仁在羊圈门口踱了几个来回,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一本正经地在上面写了点什么,便头也不回地返身走了。
拉贝次仁返身走去时,我的另外一篇小说正在敞开大门等待着他。这篇小说是我前几年写的,小说的题目叫《信徒》。
拉贝次仁刚刚走入我的小说,我就安排他睡在一张铺着狗皮褥子的木板床上,并且让他做起梦来。当然,此时已是深夜,夜空中布置着一片繁星。
拉贝次仁迈着电影慢镜头一样的步子,正在追赶公社书记家在省城上学的玉卓拉姆姑娘。玉卓拉姆在拉贝次仁眼里可真是个美丽的拉姆(仙女)。去年,他到公社书记家汇报工作时,见过玉卓拉姆一次,那天,玉卓拉姆还给他倒了一碗茶。
玉卓拉姆嘻嘻哈哈笑着,同样用电影慢镜头般的步伐在前面奔跑。拉贝次仁紧追不舍,但怎么追也追不上。忽然,一阵狂风刮过,一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却只是在一瞬,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而此时,玉卓拉姆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张牙舞爪、手持铁链的恶魔。拉贝次仁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那恶魔便冲着他走过来,圆睁一双杏仁般的眼睛,恶狠狠地把铁链套在了拉贝次仁的脖子上。
“放开我!放开我!”拉贝次仁从意外和恐怖中定下神来之后,便开始大声喊叫。但此时,他却感到身体失去了重心,无力的双脚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地面,他就像一片枯叶,顺着那个恶魔指定的方向轻飘飘坠落着,一直向一个无底深渊坠落下去。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拉贝次仁再次睁开眼睛时,无休止的坠落早已结束,他正一丝不挂地躺在一片沙砾之中。在他身前身后,无数戴着手铐脚镣的罪人赤裸着全身,正在吃力地背着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啊?”拉贝次仁站起身来。惊愕地向四周看去。
“这是地狱!”有人在他的身后说。
“……”拉贝次仁一惊,急忙转过身去。
一位身着华丽藏袍、肩宽体胖、红光满面的人迎着他走了过来。
“您是……”拉贝次仁对来者肃然起敬。
“我是郎达玛。是拉龙多吉的一支箭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因为我是人间藏地的国王,在这里不需要受苦役。”来人说着。忽然想起什么,又说,“听说人间把我称作教敌是不?”
拉贝次仁一听,即刻吓出一身冷汗,颤巍巍跪倒在地上,磕起头来。
“免礼、免礼!”郎达玛哈哈大笑着,又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不知道,”拉贝次仁说,“有个恶魔莫名奇妙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不会是莫名其妙,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过什么事儿?”
“我……我是铁卜加大队副队长……”拉贝次仁忽然想起什么来,“哦,对了,许多人暗地里叫我郎达玛,说我是郎达玛转世。”
“是吗?有意思!”郎达玛说,“说说看,人们怎么会对你叫我的名字?”
“……主要是,主要是我头上也像您一样长了一对犄角。还有,我把铁卜加寺院收藏的好多长条藏文经书放了一把火给烧了。”拉贝次仁说到这里来了精神,“您知道,那些经书全是些毒草,是宣扬宗教迷信的坏书!”
“你都烧了哪些书?”郎达玛饶有兴趣地问道。
“……不知道,反正很多,反正都是坏书!”
“你究竟烧了哪些书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郎达玛吃惊地张大了嘴,眼睛直直地盯着拉贝次仁,半晌后才说:“真该下地狱!”
以上这些内容都在我的小说《信徒》中写到过,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从此,拉贝次仁永远地睡着了。而事实是,拉贝次仁被自己的恶梦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