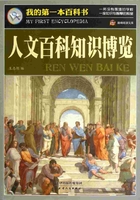在监狱的第一个晚上的睡眠就像是用水泡过的,早没了弹性,一碰就会断。断断续续地一截粘着一截,尽头处又是一声凛冽的哨子声。该起床了。天还黑着,监狱里的睡眠两头都是黑的,中间那短短一截则是实心的,像用金属铸成的,还来不及反应就倏忽不见了。所有的铁门都打开了,昨晚那些躲在门后的目光这时候纷纷恢复了人形,从走廊里流出去,流进了车间。叶庄明也掺在这人群里跟着进了车间,他们做的是流水线零件,犯人们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始了一天的劳动。狱警把叶庄明交给一个犯人,让他教他怎么操作机器。叶庄明把脸凑过去看机器的时候,教他的男人忽然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昨晚睡着了没?叶庄明心里一阵巨大的惊恐,刚要抬起头来,就听那男人在他耳边低声说,看机器。他只好接着低下头,不敢抬起。狱警就在他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走来走去。两个人默默地操作了一会机器,那男人突然在他耳边又低低说了一句话,你跟我好吧,不要让老大知道,他看上你了,他不在这个车间,你只跟我在车间里好一会就行。
叶庄明胃里一阵抽搐恶心,车间里巨大的机器声从他的胸口上往过碾,似乎要在他身体中心掏出一个洞来,他的五脏六腑,他的血液全从那个洞里往出涌。他蹲在地上开始呕吐。狱警过来把他带了出去,给他一杯热水喝,他两只手抱着那只装热水的杯子坐在值班室的木椅上,他急于想发一会呆,他需要发一会呆,好把自己晾在这段空闲的时间上面。可是,杯子里的水还没喝完的时候,狱警就向他走来了,他又把他交到了那个男人手里。那个站在车床旁的男人像一只布好了蛛网的蜘蛛正等着他。
于是这一整天,那个男人不时趁操作机器的空隙去摸他的手。油腻,粗糙,就是只男人的手。他被这只男人的手摸着的时候,忽然感觉被他摸着的那只手似乎从他身体上独立出来了,他站在高高的空中看着自己那只手,笨拙,僵硬,像是从他身上落下去的一片落叶。与他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一天时间都是从车间波涛汹涌的机器声里漂流过来的。天黑时终于漂到了对岸,收工了,于是早晨的场景又被倒着放了一遍,人群又倒流回了宿舍。铁门关上了,哐当一声,与世隔绝的凛冽。任由这铁门后自生自灭出一个妖冶的小世界。一天中最恐惧的时候还是到了,时间缩回了核心,最深不见底的那点核心。
叶庄明刚进去,铁门就被从外面锁上了。其他五个男人已经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到,白天那个教自己操作机器的男人也在这间屋子里。他们已经在等着他。他逃不掉的。他抵着那扇门,就像站在悬崖边一样绝望地和他们对峙着。这时候,他们中间一个年轻点的男人忽然端着一杯水向他走了过来,把水递给他,说,老大给你的。在一大片黑压压的男人的目光里,叶庄明战战兢兢地喝了一口,水居然是甜的,加了糖。他横下心来,闭着眼睛一口气把一杯水都喝下去了,然后向自己的床走去。床上,自己的被子已经被人铺好了,整齐得像一床陷阱。也是老大让铺的?心惊肉跳地钻进去了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一床被子。
又熄灯了,一熄灯,他的全部恐惧就像被推到了悬崖的尽头,只差那一跳了,反正已经是到底了,那恐惧反而轻了些,从他身上蒸发出去了一些。屋子里飘满了恐惧的神经末梢,像蛇的芯子触着人的脸。他躺着的位置正好能看到铁窗里的月亮,比昨天长大了一点,斜斜地别在那里。这时,一个人影走了过来把月亮挡住了。影子薄薄地贴在黑暗里,像一层魂魄。他知道,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大开始在黑暗中显形了。老大开始和他说话了,多大了。
二十三。
怎么进来的。
把人打成重伤了。
几年?
五年。
这时候他的眼睛渐渐开始适应黑暗了,这影子就着窗外那点嫩黄的月光也渐渐长出了眉目,从眉目里又长出了目光。就是这点模糊的目光让叶庄明在那一瞬间知道了这面具般的影子后面,站着的是哪个男人了,他对上号了。老大就是这五个男人里看起来最没有表情的那个,不是最高的,不是最凶狠的,甚至有点白净,他白天里一直没有表情,看什么都是隔了几万里看过来的样子。在男人的丛林里,可以称王的那个都是最不露声色的。影子后面那点明灭的目光与他静静对视着,让他有点不寒而栗。但是,老大没有再说什么,却伸手给他拉了拉被子,然后就离开了。他最后这个动作像盆炭火的余烬在被子里久久烤着叶庄明。叶庄明没有再动那被子,他一动不动地就那样躺着。这个时候他才突然觉得,在这间宿舍里,只要铁门一关上,他其实就是个女人,被当成了老大的女人。
现在,他要开始接受老大对他的种种照顾和示好了。原来,男人追求男人用的也不过是这些手段。在一个满是男人的密闭的空间里,是不是一定会有男人演变成女人的角色才会平衡这种奇怪的生态。现在,轮到他了?他再次响起了那个狱警的话,你这长相不该在这种满是男人的地方。
可是,谁让你来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