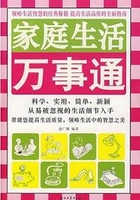四月桃花水,草长蝴蝶飞。
虽然肚子还是很饿,但清明一过,心情一下子好起来,门外的小路、田野还有池塘,一夜之间醒了,各种颜色的野花打打闹闹的就亮了出来,蚂蚱蜻蜓在草丛里花朵间跳来飞去,夜里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安静了,叽叽咕咕,呱呱嘎嘎。如果你听到呱呱两声后突然一下安静下来,那肯定是水蛇把某只刚学会展现身段的青蛙一口吞了下去。不过,安静的时间总是那么的短,一会儿,又是一片不管不顾的咕咕嘎嘎声。这种季节,恋爱是必要的,一入夜,全村的猫就一齐“呜呜哇哇”叫起来,弄得到处都是动静,老鼠们不好意思了,躲得一只不剩,不少年轻人也不回家睡了,整夜猫在江堤下,他们说,我们看星星呢!
月英的肚子比冬天时凸多了,都快和奶子一样高了。潮州的脸色不是太好,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有时走着走着就撞到墙上去。
听说,月英下个月要嫁人了。
雨已经下过好几场,春雷也在某天夜里炸过了,地上的所有活物都变得润滋滋的。
母鸡的屁股明显大起来,越来越像电影里的大领导,走起路来空气和灰尘直往边上闪。它的块头比我见过的所有母鸡都大而且高,神色傲慢,很威风。就叫它杨排风吧我说。弟弟说,好啊好啊。他经常缠着我给他讲故事,他知道杨排风很威风,一根烧火棍除了能捅火蒸馒头,还能撑起大宋朝的半边天。
杨排风越来越不听我们的话,到处乱跑,除了四处扒蚯蚓啄蚂蚱,有时还愣在老猫他们家厨房的窗外,脖子伸得长长的,小眼睛水汪汪。后来,它扒草根时的心情越来越好,一边扒,一边咯咯咯轻声唱着歌。奇怪的是,它见到小石子和蚯蚓时总是匆匆忙忙地先把石子吞下去再去啄蚯蚓。它特别喜欢吃石灰石,就像弟弟喜欢吃水果糖。我跟爸爸说了,爸爸点点头:嗯,是时候了。
自从我家的公鸡死了后,潮州他们就把他们家的公鸡母鸡关在了厨房里。听他们说,他们家的公鸡长得又肥又壮,都会踩母鸡了,可惜他们家母鸡还太小,老给踩得咕咕嘎嘎乱叫,有次还飞到了锅上,要不是锅盖盖着,他们就吃鸡汤饭了。他们讨论这事时,眼睛直往我们家杨排风的屁股瞟,那眼神,嘿,不说!
那天,潮州带着老婆、月英、大龙和小龙到山上拔猫婆坟头的草,顺便摘了桃金娘把嘴唇和手指吃成酱紫色。他们在野花丛里吃得正开心呢,老猫死了,死前在家里闹出很大的动静。不过,这只有他的小孙子三龙知道。那天上午九点多,日头刚在苦楝树上站稳了,老猫突然想吃鸡肉,一见到公鸡两眼珠子“唰”对在了一起。他拐杖也不要了,举着菜刀就追公鸡。公鸡一看形势不对,开始满厨房飞,把能扇翻的东西一个不剩通通扇翻了,吓得母鸡躲进了灶眼里,屁股都烧秃了。潮州他们推开门时,公鸡不飞了,腰上竖着一把菜刀,歪在血水里使劲蹬胖腿,气泡一个接一个贴着刀口挤出来,噗,噗,噗。老猫趴在地上,气也不喘了,眼睛瞪得大大的,都是眼白。三龙猫在桌底噙着大拇指喵喵的哭:阿公杀公鸡,阿公杀公鸡……
老猫要上山了,队长螃蜞来叫爸爸去帮忙扛棺材。爸爸说,不,死的又不是人,是只猫。说完拔脚就走,头也不回。傍晚,他回来了,抱着一只大公鸡。那家伙大秃头,脖长腿长胸脯宽,身上除了翅膀和尾巴,其它地方都不长毛,立起来像一个感叹号,比老猫家墙上贴的仙鹤还神气。爸爸竟然一身的酒气。
是斗鸡,爸爸说,你四眼伯家的,他家的母鸡丢了。
四眼伯我当然认识,他住在崎沟村,崎沟村离我家有十几里地,路上还要翻过两座很高很大的山。四眼伯光棍一条,也睡在队间里。那年炮轰金门,爸爸让人用步枪押到了崎岭农场,在那儿认识了他。爸爸说,那时四眼伯的眼镜还有两条腿。不过,等我见到他时,他的眼镜是一条腿也没有了,连镜片也只有一片是完整的,就用麻线捆在脑袋上。他很少来我们家,而且只在高音喇叭讲话懒洋洋的日子才可能来。我知道他原来有老婆,而且还有过一个儿子,可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按他的说法是:“比十年前的咸菜还老!”他很早以前在南京,教人家造飞机,南京离白水远,两千多里地,会下雪。他跟我说过,飞机俩翅膀,不过不长毛。因为他我还知道了一个名词:离婚。离婚就是女大人和男大人不在一口锅里吃饭了,而且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顺便,我还记住了一个单句:断绝一切关系。
我想,四眼伯家的阿姨有头脑,不像我妈妈。我妈是个数学天才,天才就是死脑筋。当初我爸被逮起来时本来没她什么事,人家组织上都说了,只要你跟他划清界限,组织还是要重用你的。可我妈就是转不过脑筋来,傻兮兮的跟着我爸来到了我们村。她说,她至少证明了她可以和我爸过一辈子。可是,她害惨了我姐——我姐原来是个天天吃包子的城里娃呀,这下不仅要饿肚子,更要命的是才十来岁就成了一架劳动工具。我姐也是个天才,当然死脑筋,竟然不去偷不去抢不去坑蒙拐骗,死心塌地做一个地道农民,她难道不知道正经农民都是属牛的吗!
这只斗鸡太神气了!比主席还神气。我想都没想就叫它:吕布!在我的印象里,要找出一个比吕布更神气的家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