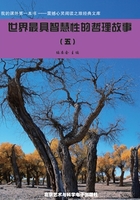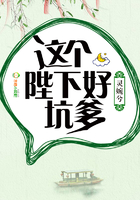这天大娘没有给她们端粥是因为二娘。大娘一直在外面说话。百灵看看西窗,窗台空空的,二娘不在。百灵有点怕见二娘。二娘早上欢喜趴在窗口看着百灵梳洗、扎小辫子,啧啧的说,“百灵生得好看来。”二娘自己没有孩子,看别人的孩子怎么都好。
二娘清早哭过一次,百灵听见的,呜呜咽咽的声音像大伯用竹箫吹出来的。大伯吹箫的时候不说话,吹完了,甩着箫里的口水,问百灵要不要学,百灵总是摇头,“不要。不要。”再问,她就要逃了。
二娘不哭了,人也就不见了。二娘丢到地下的锅,舀水的铜勺子,大娘拾了起来,整齐的摆在灶台上。
百灵跪到椅子上捧起粥碗。好像没有二娘哭这一回事,大家都管自己呼噜噜的吃粥。没有二娘说“百灵白粥也吃得这样香来。”百灵并没有觉得高兴。二娘在百灵的睡梦里一直在说“你不要我住,我走就是了。”
大娘跟妈妈说二娘的丈夫生病死了,二娘不喜欢跟丈夫前面那个老婆生的儿子媳妇一起住,她老是跟大娘告状,说白天儿子上班了儿媳妇就把菜橱锁起来,中午只给她一碗白饭吃。
“二娘回去会饿死的。”百灵拉妈妈的胳膊,让她把二娘叫回来。
大家都笑,“这孩子,真傻。”
大娘好像觉得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揪着心口上的一片衣服,一个劲的说,“冤枉,真是冤枉。她作成这样不是让你们看我的笑话嘛。不是比骂我还让我难过死嘛。”
妈妈唔了一声,过了一会才说,“二娘心里不好吧。大娘不要怪她吧。”
大娘拎着篮子走了。
母亲挟着她的花布拎包也走了。
屋里的人一个个全都出了天井走了,好像有一只手在拽着他们。
百灵跟到门口,碎石铺的小路从她的脚尖一直斜着伸向大街。她看着,有些惘然,二娘走到哪里去了呢?
大娘还得在菜场兜几圈才回得来。
百灵回到荷花缸边,她猫着腰,绕着荷花缸走了半圈,一转身,往后屋钻去。
后屋说起来算一间屋子,其实比露天好不了多少,又是紧靠后门和厨房,大娘的二儿子一家对住在这里充满了怨言的。他们另外盖了房子搬走了,后屋便成了堆放柴草的地方,大娘的大儿子又高兴又妒忌。一下雨,后屋更是满屋子翻腾着柴草受潮的霉味。
百灵却喜欢,后屋没人欢喜去,稻草金黄,桑皮条、芦粟杆青绿,把她遮掩得很好。后屋经常有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在看上去什么也没有的柴草下面。是可以用来做伴的。
刚生的老鼠就指头那么点大,五六个抱成一团,浑身透着粉红,皮薄得很,怕用手指戳一下就戳穿了肚肠。
百灵舍不得用手碰,伸手也是为了把爬开的推推拢。这些还跑不快的家伙一旦让烧饭的大娘看见,难免不死在烧火钳下,肚皮碰肚皮的串成一大串,夹到门前的河滩旁边扔掉。
但是等到它们长出油亮的黑毛,嘴尖也冒出很让百灵嫌恶的胡子,它们就会毫不留恋地丢了旧窝,跑得踪影也没了。
蚂蟥是另一样时不时会从后屋爬出来的东西,像大娘针线箩里的黄丝线。百灵很怕蚂蟥。因为大娘说蚂蟥吸血。百灵究竟不知道蚂蟥怎么吸的,始终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她可不敢把蚂蟥放到自己胳膊上试,像画皮里的书生那样被吸干血死掉想想都很恐怖的。
大娘的烧火钳挑着蚂蟥,一只手拨开门栓开了后门。后门口铺着砖,草迷迷瞪瞪顺着砖缝长,一直长到后屋的墙上窗上。大娘放下蚂蟥。大娘自己不进来,就站在那儿叫,“百灵,百灵哪,快舀勺盐来。”
百灵找到盐罐,小心的挖了一勺。挖得太多大娘要说,“你以为盐不要钱啊。”挖少了又说“这一点哪够,真是做鬼也不大。”百灵要是生气,把盐勺子随便往哪儿一扔,大娘又会说,“这儿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等你长大了嫁了人,去了婆家,想怎么撒野就怎么撒野。”
百灵舍不得走开,看着大娘把盐洒到蚂蟥身上。那是用不了多久的,蚂蟥身上的黄颜色就开始稀薄,像被水冲淡了一样慢慢的淡下去。大娘走开了,百灵还守着蚂蟥。蚂蟥淡到最后便断了,断成两截,三截。大娘铲着锅里的菜,时不时举起锅铲尝咸淡,一边说别看这些断绳头似的蚂蟥,要是让它们掉到没盐的地方,碰巧又水分充足,便会变成更多的蚂蟥。这样的情形百灵一次也没看见过,蚂蟥到了大娘手里从来没有不死的。
妈妈早上离家前便不耐烦的叫百灵不要去后屋。
“后屋脏。记住了没有?”
百灵点点头。便有几天不去,在大娘那把旧得红紫发亮的春凳上躺躺,用手捞荷花缸里的红虫玩。
正好家里来了客,妈妈说是大娘的三儿子和他女朋友,这两个人天天出门有时也顺手带上她还买了块手帕给她。
那天早上说好带她去后山找野莓子的,却一直没有起来。她等的无趣看见二娘过来便问二娘他们还不起来在屋子里做什么。二娘当然也不知道,叫她自己去看。
那门的缝是很宽的,她看了出来,二娘还在门口,问她看没看见他们在屋里做什么。
她想了想,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明明打起来了,又好像高兴的要命。”
二娘忍着笑,又问他们是怎么打的,她正在学,大娘的三儿子一阵风似的跑出来。她一时僵在那儿,只觉得那双平日总是很欢喜的看着她的眼睛简直像冰一样冷冷的锥着她把她锥得浑身都是洞了才不见了。
她回到屋里,坐在床沿上,她觉得一定要想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