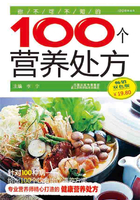那天在深圳旧天堂书店,我指着整整一架子诗集和诗歌研究著作对程益中说: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却摆放最少人买的书,这才是好书店的标志。他说:“怪不得深圳要成为文学之城了。”什么?!文学之城,还有这等美事?!
真的不是笑话,深圳真的在大张旗鼓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文学之城”的奖状。想起十七八年前曾在某省作协一份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一位读者倡议举办广东文学节。我很震惊这么酷的倡议竟赫然登在报纸上:该文学狂人建议派出一千名作家在天河体育中心与十万市民会面!请参照如今恒大中超主场的火爆场面,想象一下这一魔幻现实主义的壮景吧:人称“天体”的天河体育中心,十万市民涌入球场,追着一千名作家要签名,最后作家们唯有提着裤子抱头鼠窜,否则就得裸奔了。
那年头文人发明了一个词叫“下海”,用以表达对被商业大潮淹死的恐惧,以及对金钱的垂涎。作协关起门来开会,一边强调如何不怕下海,顺应改革顺应潮流搞创收,一边又信誓旦旦要守在岸上写作,那感觉就跟要守活寡一样,把五千年文明的贞操死死捂住。记得有位作家一会儿坦承写不写都无所谓,一会儿又宣称一定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写下去。是啊,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那年头我记得还见过铁凝和洪峰,都是当时的当红作家。两个人的命运后来天差地别,铁凝成了中国作协主席,洪峰则因作协不发给他钱而上街抗议,后来跑到云南隐居,又不幸被打。且不管作协不发工资的具体是非,我们还是得先问问:作协的存在价值和功能究竟是什么,纳税人是否需要养一帮作家以及无数倍于作家的作协机关工作人员,来为自己创作文学?去年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大会,新华社的报道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开头:“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伟大的人民期盼伟大的文艺作品。”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伟大的人民期盼伟大的文艺作品,是否需要作协和文联这样的中介?买房子找老婆找保姆是需要中介的,但谁说爱好文学非得找个中介公司?如果人民不需要作协中介,那么作协存在的唯一功能只能是:附属于、服务于国家机器,或者说成为国家文学机器,作协体制下的作家则充当润滑剂,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天经地义。
而深圳作协把润滑剂提升到东方神油的境界。
我问程益中,深圳都有什么大作家?他说:李兰妮啊。
恕我孤陋寡闻有所不知,一搜这名字,果然搜出有关文学之城的大新闻:
在政府批示下,深圳文联和作协正在加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文学之城”的工作。已经取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有:英国的爱丁堡、爱尔兰的都柏林、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美国的艾奥瓦和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五个城市,深圳意欲成为第六个。深圳市作协主席李兰妮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文学”,更应该看它的市民对文学的参与热情,看这个城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活力,看文学对城市人的影响。深圳是全国最庞大的外来移民和打工者聚集地,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写作群体,“会员作家的数量相当于一个省的数量”。市作协提交的申请理由中介绍,从目前当选的城市特征来看,“基本没有一座文学之城靠的是文学大师和文学巨著的多寡,而更多着眼于城市的文学特色”,而“深圳显然是当代中国文学特色最鲜明的、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写作者最密集、文学生态最完整的文学沃土”。
如果说向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必须师出有名,好歹得拿出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么这文学之城听上去就像光天化日讲鬼故事。李主席当然还知道自己这号作家拿不出手,只好喊出四宗最:最鲜明、最活跃、最密集、最完整。作协养的就是这样善于写行政口号的作家。
在深圳街头千万别随便扔垃圾,很容易就砸中某个作家。
深圳曾莫名其妙地拿了一个“世界花园城市”的头衔,花园绿化是摆在那儿一目了然的,那么文学之城该如何排兵布阵呢?是否首先得组织一个浩大的翻译工程,先把深圳文学翻译成各国语言?要不然就在体育场组织成千上万的作家进行一场文学大赛,像科考一样当场作文,最鲜明最活跃最密集最完整地让联合国考察团一睹文学之城的盛况?
把文化建设当成卫生评比,当成申办运动会,当成体育竞赛,把文化事业行政化乃至军事化,围绕着军功章进行动员和指挥,这是公权以市民的名义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令人想到深圳还有一个市民中心,一个建筑不伦不类的广场和剧院,一个缺少市民的市民中心,硬件不错却缺乏人味儿,更要命的是大多时候闲置没用,很少有演出。幸好“文学之城”毕竟只是个虚幻的东西,不过一旦真的忽悠到这块牌匾,不知是否也会造个世界文学公园什么的。
作为一个历史短暂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急于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以获得身份认同,从官方意识形态到民间社会,都有这种可以理解的文化心理焦虑甚至自卑。被联合国封为“设计之都”算是实至名归(深圳在设计方面算是国内先驱,但我不认为它在设计领域有什么国际地位),但自封为“图书馆之城”和“钢琴之城”,就大有往胸前一根接一根插笔之嫌,而申请“文学之城”,就是把笔直接插在脑门上了。
从化可以搞“温泉之城”,增城可以搞“荔枝之城”,顺德也不妨搞一搞“双皮奶之城”,但深圳宣称自己是“钢琴之城”就莫明其妙,是因为钢琴卖得多,还是因为李云迪出自深圳?——但这哥们不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香港精英人才了么?周笔畅和陈楚生也出自深圳,何不雅俗并举,也弄个“超女之都”“快男之城”玩玩呢?
假如其他城市也能向深圳看齐,纷纷打造小提琴之城中提琴之城大提琴之城小号之城大号之城长号之城萨克斯之城贝斯之城吉他之城二胡之城三弦之城古琴之城唢呐之城古筝之城扬琴之城,那么中国城市文艺复兴指日可待。
2006年,深圳市政府曾提出要建成“全球先锋城市”。当二三线城市都在哭着喊着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全球先锋城市”这一提法显得新鲜炫酷多了,并且官方还给出了一个建成全球先锋城市的时间——2030年——比王家卫提前了十六年,比波拉尼奥(小说家,《2666》的作者)提前了六百三十六年。《南方都市报》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当即在深圳策划了一个“先锋城市”论坛。我有幸参与论坛,却深感所谓“十大先锋城市”之类评选实在无聊透顶,先锋人士也不能免俗地成为鲁迅所诟病之“十景病”的新病人。但在评选深圳的“十大城市先锋切片”的时候,大家又纷纷推举深圳当时轰动一时的警方将妓女戴上口罩游街的事件,觉得此举很先锋,而我指出深圳才女妞妞的电影《时差八小时》是一部先锋电影。
由此可见,建设“和谐城市”比建设“先锋城市”更为迫切。否则去年深圳不会在大运会之前清理那么多流动人口。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深圳作协在申请文学之城的时候拿外来移民和打工者作为招牌(所谓移民文化打工文学),但所谓“深圳作家”又该具备什么认证?他需要出示作协会员证,但无疑还需要出示深圳身份证吧?如果没有深圳户口,是否还得向联合国出示他的深圳暂住证呢?
当然深圳作协可以扶植打工文学,让有文学创作才能的打工者获得深圳户口,也可以请外地作家加入深圳作协落户深圳,这样一来就跟全运会城运会各大城市引进外援无异了。于是,文化更进一步沦为竞赛。往往一提到举国体制大家就批评体育界,然而吾国处处都是举国体制,文化上更是举国体制。深圳似乎一心想夺文学全运会的金牌,想走出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都柏林作为文学之城,自然以乔伊斯为最大骄傲,然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却充满了对故乡以及老乡的讽刺和批判。
记得有一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人群踩踏惨剧,次日各报纷纷作头版头条报道。深圳有家报纸特立独行,其头版头条刚好是:《深圳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大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文化气概。
当然是自由和宽容,而不是口号和奖章,才能造就完整的文学生态。让公民社会自由生长,才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先锋城市理当践行的。比如旧天堂书店以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就代表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
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或许一个劫匪都比作家了解得更多。2007年我在深圳追捕过一个特立独行的劫匪。我目睹那哥们抢了一个女孩的包,便和几个朋友追过去,明明相距不到百米,劫匪居然立马没影,四下搜了几分钟才发现劫匪爬到树上去了,但被发现后他纵身一跃跳上立交天桥逃遁,等我们跑上天桥,已经又没影了,这令我恼羞成怒。好在几分钟后警察押着他过来了,他不幸撞上巡逻的警察。
他被判三年徒刑。但我们应该感谢他活生生地演示了一个城市的牢笼和战场,以及逃亡路线。高尚小区林立,却以近乎全封闭的方式捍卫中产阶级,割裂了社区与街道的联系,尽可能阻止陌生人之间的流动和接触——更不用说交流。于是高尚社区变成中产阶级的堡垒,而街道变成流民的战壕——壁垒森严的社区把人烟稀少的街道让给了劫匪。而这位老兄深谙这座城市的地理:高架桥和树林如此紧密地挨在一起,一座在大自然中硬生生拔地而起的城市,这是深圳特有的景观,先有树林,后建高架桥。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白领之都,也是最大的打工者之都。而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劫匪就这样揭示了深圳这个联合国候选文学之城的精神地理学:中产阶级和流民之间的分裂。作家们,请学习这敏锐的现实主义,请学习这诗意的逃逸,这树上的劫匪犹如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纵身一跃,把像我这样笨拙的作家抛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