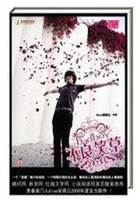后来有一天早晨,亦微去海边晨跑,远远看见他倒在街心,身体皱成小小的一堆,风卷起他深棕色的衣角,一飞一飞。她就有一点害怕,没有走过去看,但她疑心他是死了。
果然,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但她还记得他的脸,很劲,像个公爵。
出乎意料的是,清容得知程森的消息时,却并不太吃惊。
她脸上可曾有片刻的抽搐么,事后亦微拼命回忆,却也无论如何不能确定之。
其时正午,恰逢清容收工,只见她心平气和地转去化妆间大致把妆卸了,带着一脸一颈卸妆液茶之清味走出来,碰一碰亦微的腰,说,"走,街角有家麻辣香锅味道绝赞,我们去吃。"
就是这样?如果当他落难,而她已无动于衷?亦微深感自己跟钟采采,咸吃萝卜淡操心,端地多事。却也留神观察清容,疑心她这样漠然是装出来的,左看右看倒也不像,除非她演技真有那么好。这样亦微松一口气,本也不是专为看清容失态来的,她能表现得这么淡,必是心头的劫火已经烧得不那么炽烈了吧。
谁知喝了一点酒清容却来同她说,"亦微,其实我都知道。程森酒吧里头那些个不见光的勾当,以及后来他搭上荷兰人那条线,在郊区签长约租了一院房子,开始自己种,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明白他是在保护我,怕我担心,不愿意我晓得这些,于是我也就顺着他,假作不知。这一整件事里,他是藏奸,我是装傻,我们互相都隐瞒了点什么,也都瞒得很好。亦微,那时我是真爱他,明知他是人渣也爱,因为当初我爱上他并不在于他是人渣或者不是。对于我,亦微,他不是好人或者坏人,他只是程森。"
听到这里,亦微忽想起去年冬天,程森跟她讲的,"我是那些最好的东西的对立面",又赫然想到中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德尔图良,曾对上帝说,我只信你,不需要论证。这样她就一骇,呵,深爱令人变成信徒。
那一天清容脸上还有淡淡哥特式的残妆未曾卸净,眼睫冥黑如鸦翅,肤白如雪,很有点像午夜伦敦街头的吸血鬼走到东方的灯影里来。见亦微只默默点头却说不出话,清容接着道:"现在他被抓,我的确是有点吃惊,但也不至于那么吃惊-结局是一直摆在那里的,来的时间早晚而已。他从一开始就把我推得那么远,是铁了心要我离开他的黑暗面,这个道理我若不明白倒也罢了,我却懂了,从此也不能再假装不懂。现在看起来,我跟他纠缠这么些年,热烈过,封冻过,如今,竟也只剩凭吊。回忆最好了,回忆里谁也伤不到谁,现实中呢,两个人各自活着,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