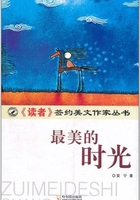亦微亲眼目睹唐清容面孔上浮起一层云影般的祭奠之色,呀,他还活着,她却已经在追悼他了。
这时邻桌的客人当中有两个姑娘认出了清容,大大方方走过来问她要签名,于是她住了口,含笑签了,再抬头时,亦微也没好再把这话题继续下去。
等到两个人走到了街面上,枯枝间呼啸有风,低温中亦微轻轻仰脸跟清容道了再见,又上前去抱一抱她。清容却在她耳边道:"也许刚才我说的那些全是借口,我不过是仍在恨程森。是的我恨他,亦微,我恨他把别的女人带去我们的床上。不,我不会帮他",说完,惨艳的白色日光中,清容嘴角痉挛般抽了抽,不知道是不是在笑。
如此,过了一个礼拜,程森被捕的消息见了报,也上了电视,审理时判了个无期。这件事沸腾几日,接着就平息了。呵,天大的事也一样,地震,海啸,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上,寻常百姓还是要把日子过下去的。
这一冬,倒是亦微跟钟采采恢复了邦交值得记上一笔。
采采如今在美院附近租住一间工作室,空间很大,离亦微承友他们不远,两边不时往来走动。她开始进行大尺寸的创作,最小的也有两米见方,从前的那套两居室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她。
亦微看着她这些日子的作品,发现采采目前的风格正日趋写实,尤其近期,已经不大采用意象化的表现手法。她的画,粉气变少,质地变重,扎实,瘦硬,几乎像拳头,亦微诧异于这种转变,直觉它背后应该有个故事在,却也没好意思开口问,毕竟只不过是臆测。
有时采采也画些小品,傅存光从日本带了几支仙鹤的羽毛给她,她剪一剪,做成羽毛笔,蘸了水色来画画,都是花草,多用金色棕色,蓬勃中见颓败,送给亦微跟承友,一人一幅。
她仍在跟傅存光的画廊合作,签了五年的长约,但当然她跟傅存光的关系不止于此。
这天存光不知上哪儿找了一管颜料给采采,让她试一试。她就兑了松节油在调色板上扫两笔,金灿灿的,很干很艳,直扎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