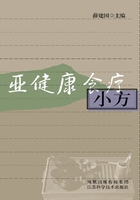画廊装潢走极简风,举重若轻地,四面墙漆成白色,白如春光之明媚,亦微愉悦地眯起眼睛。迎面一墙蓬勃的花事,色彩很艳,玫瑰有血,鸢尾之间深蓝有风,每一幅都有近一人高,却不是油画,大胆用了粉彩。亦微且看且叹,真厉害,粉彩那么容易脏,却也画得如此干净。这样洁净的艳丽感,太难得了。
一转脸,左面墙上,江亦微却看见了旧相识,女子侧立的轮廓,胸腔中有荆棘有刺。
曾经无数次她看过这一张线稿,相像过它完成时的全貌,此际见了,却也没有惊奇,心中只是想"哦,是这样",这幅油画像是天生如此,不经历修改,甚至,不经历过程。
但亦微其时已不及细看,只不欲跟钟采采照面,游目四望,画廊里人不多,并没有采采。
亦微心下一宽,随即又想此地不宜久留,遂抽身朝外走。
不料,外面花径上恰恰过来一双男女。乍暖还寒气候,那女郎却已赫然裸着细洁小腿,穿黑色洋装,腰间一朵白茶花,裙角飞扬,蝶一般靠近,见了她便叫"江亦微",一面疾步走上前来,带同迪奥那一款黑毒冶艳的香氛,又随手抹下头上系的风巾摘了墨镜,她的双唇,如东瀛艺伎般搽决绝的血红-钟采采,始终是江亦微所知最艳丽的女子。
对于这样的狭路相逢,两人显然都很错愕,彼此对望,脸上都有点讪讪的。
到底采采反应快些,介绍了她的男伴给亦微认识,"这间画廊的主人,傅先生"。
那男人也颇上道,立刻伸手过来,自报家门道:"傅存光。"亦微瞧过去,见是个瘦瘦高高的男人,戴眼镜,穿西装,气质却练达,斯文而不迂腐,伸出手来与她握时,亦微留意到他右手虎口有个纹身,过后想来想去,竟觉那是个"寿"字。她想这人真奇突,怕死到这个地步,而且不介意给别人知道。
略站一站,那男人就进到画廊里头去,十分得体,留采采跟亦微在外面吸烟。
这时采采才偏头向亦微道:"亦微,我是不是做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