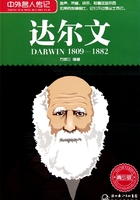哑鼓重新回到安倪的生活中时,她已经拥有很多条鱼纹尾了。光这样倒还算了,最痛苦的是,她有过不低于十次的机会,去攀附死神冰冷的双翼。她脑子越来越乱,白天乱,晚上更乱,天气再好,她都会在突然间产生一种被针刺了一下的感觉。偶尔,她也会在纷乱中回想一下过去,这个时候哑鼓纯美的笑容就踉踉跄跄地闪现了,可是,它越来越空灵,幻象似的。谁叫安倪的感情经历那么丰饶呢?在哑鼓之前、之后,有太多的男性从她的生活中穿行过去,还都挺隆重的,没有哪段情简单得可以一言以蔽之。哑鼓对安倪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没什么。真要为那一段情找点特色的话,那无非就是:那段情的发生、延续,得益于安倪的生活因此获得了一条茁壮而且对她有益的线索。因有那条线索存在,安倪在那一年里活得相对自如了一些。在那一年稍晚些的时候,她得以获得某种力量去和那两个准女友绝交,对那个叫那木的准白痴持续的敲门声置之不理,继而幸福地跟他一刀两断。
当然也有后遗症出现过。有一个时候,促成安倪与银淑莲、意米结识的那个文学论坛里出现了一个诋毁安倪的帖子。这篇不足一千字的帖子遣词造句上有些粗糙,还有不下十个错别字,一看就是一挥而就的。但它的粗暴程度却叫安倪咂舌。这位网名为“轰炸2000”的网友在帖子里大揭“某女作家”的所谓“老底”。他或她(它?)“揭秘”说,某位女作家是个性瘾者,因为上了性的瘾,早两年,她就变成了一个艾滋病患者。得了艾滋病本不值得痛恨,可恨的是,这位女作家明知身患这种世纪绝症却还是“狗改不了吃屎”,仍大肆搜捕男人,并且慢慢在心里树立了成为一个超级传染源的邪恶目标。帖子没点安倪的名,但它详细地罗列了这位女作家的诸多特征:近年居住在上海、写作十余年、常发表她作品的那几本冷门文学期刊的名字、某篇代表作的主要内容……不用深究,人们就能推断出,这位女作家,就是安倪。这帖子发出不到两分钟,就有人跟帖让安倪的大名亮了相。紧接着,就是完全针对安倪的抨击、谩骂、诅咒和控诉了。等安倪自己在帖子发出第二日看到它时,它已被一家大型综合网站如获至宝地从浩瀚帖海中捡起来张贴到了这网站的首页。接着下来,几个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大大小小的网站再转载、再加工后转载,很快安倪就被世人瞩目了,成为那几日最具轰动效应的网络红人。
喔唷!安倪从未料及,她会以这样一个方式获得盛名。她还以为她会一辈子只能被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呢。说心里话,她还真的不喜欢做一个被太多人知道的人,因为在她看来,那本身就是件特别恐怖的事,她归根究底还是最喜欢波澜不惊的宁静生活。安倪很恐惧。开始,她还挺镇定的,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瞪着滚滚涌出的无数关乎她的帖子,看西洋镜似的,有种置身事外感,不怎么上心。有一个夜里,她连着做了几个被射杀的梦,惊醒过来后吓得浑身打战,接下来几天,恐惧便稳固地占有了她。她什么也干不了,只能一个人待在房子里思索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这个帖子的来历。有一日,她还发了不高不低的烧,浑身酸痛,昏头昏脑地到处找水喝,差点误喝掉一碗白醋。银淑莲是帖子出现后第一个打电话给安倪的人。她颇为体贴地询问安倪有没有什么事,要不要她过来帮她渡过这个难关。以安倪的敏锐,马上从银淑莲的语气中悟出了一丝线索。银淑莲不会就是那个匿名发帖人吧?想一想啊,就银淑莲的嫌疑最大。为什么?首先,她不是个有道德感的人;其次,她一个月前刚对安倪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责问。当然了,正是这场责问,导致安倪痛下与她绝交的决心。银淑莲那次责问的主题是:安倪为什么要到处说她的坏话?这责问是叫安倪心虚的,的确,她跟意米说过银淑莲的坏话。但是安倪不想跟银淑莲辩解。太不想了,她不想费这个劲。又怎么样吧?说到底她又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胡编乱造,你银淑莲有胆量做文坛垃圾就没胆量听一两句难听话吗?要混文坛,没这种便宜事。需补充说明的是,那阵子银淑莲真让人不可小觑,她花了三个星期写了个长篇,竟然真的很快在文坛闹出了点小动静,还有不少小有来头的人挺像那么回事儿地捧她的臭脚呢,真不知道这个连风韵犹存都谈不上的女人,是怎么跟这些人拉上关系的?银淑莲还真一下子小小发达了一下子。她有本事攀着这次的小发达,抓获更多的小发达,最终大大地发达。安倪相信,她有这个能力。安倪恨的是意米。这个嘴巴漏风或喜欢故意让嘴巴漏风的女孩,不靠谱。
意米也来了电话。她倒坦率,承认有一次不小心把安倪抨击银淑莲的话说给了别人听,用以佐证她对银女人的某个更深入的论断。但是天地良心,意米发誓说,她真的是无意识地传播了安倪的话的。意米一步到位地断定发帖者是银淑莲,而她决断的语气倒让安倪觉得她亦有可能是嫌疑人之一。她想起同样是早前与意米绝交的情形。也是在电话里,她突然失控了,直陈意米的自以为是,并告诫她如果不改掉这个性格的话,她可能到头来只能一事无成,只能是:用一辈子去换取一个大大的笑话。当时意米差点要疯掉,对安倪恶语相向,大骂安倪是坏女人。而安倪没听她发泄完,就自行把电话挂了。现在,安倪还是武断地挂掉了意米的电话。那是在深夜,安倪深深地体悟着文人心的乖张、偏狭,她又将这种体悟推而广之,深察着世道人心总体上的叵测面貌、人世的不易。而这些,正是促成她变成一个隐在病人的导火索,抑郁症、自闭症、强迫症、分裂症、交往障碍……她不开心,持续地不开心,进而发现,自己病得更加显明了。
排名第三的嫌疑人是哑鼓的母亲。有件事要说明,安倪后来在戒毒所里完成的那篇小说,多少有想象的成分。至于哪些部分属于真相,哪些是想象出来的,她自己后来也搞不大清楚了。这起网络纷争正好诞生于她跟哑鼓中断交往的一个月后。没这个可能吗?哑鼓的母亲,一个如梦初醒后难免变成攻击狂的女人,蛮横地对安倪造了一次世纪大谣。可能,可能得很呢。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在风中,不易知,微微可知,扑朔迷离,呸!
哑鼓在网上看到了安倪的事,在某几天里,持续不断地给安倪打电话、发短信。安倪这边自己都快抑郁得死掉了,哪有心思跟他交谈,再说了,她已经对这孩子没什么感觉啦,屏蔽他吧,永远,一直到永远,把这个世界上不该与她产生线索的人全都屏蔽掉,就这样。安倪一边决绝地抵抗着一切,一边发现着自己的脆弱。她有一天差点哭了,这把她吓了一大跳。她怎么可以哭?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她退掉了租房,该扔的东西扔掉,该烧的烧,然后戴着一副大墨镜回老家生活去了。在D省的那个小县城,她可以在什么都不去理会、什么都装作不知道的情况下,也能活得不那么痛苦。她父母在那里有权有势,足以为她提供丰富的物质。物质带来的即时娱乐,促使她对这个世界故作不知。就这样吧,走!快走!离开这个、那个,这些、那些是非之地。
就是这样,在2000年冬天刚刚来到的时候,一个叫安倪的冷门女作家、幽闭女人,从那些知道她的文坛人、伪文坛人、非文坛人的视野里消失了。这消失来得突兀,让安倪深深地洞悉,她其实是个挺缺乏技能与这个世界抗衡的人。
安倪真正吸上毒,是2009年春天的事。而一如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在那一年之前的八九年里,她是一个一步步向毒品走去的女人。这个逻辑顺序的第一步,即是多年来困扰她的那些隐在的心理病,第二步则是因无力对抗那些病所产生的沮丧感,使她不下十次产生自杀之意,而第三步,是她为了摆脱缠绕她的自杀欲,去寻找解救自己的方式,她后来找到了,却是吸毒。
在开初挺长一段时间里,安倪在D省那个小县城整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她的心不在这里。到底在哪里,她自己也搞不明白。仿佛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已经落实不了她的思绪。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身在尘世,心却遨游在天上。在宇宙某个不能被世人感知的某处,有她。她游荡在那里,充当虚无的实体。她也跟亲戚、朋友来往,跟父母、兄妹和平共处,只是她几乎不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面对面谈心。通常她就笑,笑着,坐在他们面前,很安静的样子,让他们误以为她很稳定、妥当。有的时候,她一个人开着车子出去,停在郊外某处路边,看着荒草、河流、尘烟,长时间地感受内心的空茫、稍纵即逝的思维失控。唯独夜晚时光里的痛苦是绝对性的,纠缠着她,夜复一夜。她还是那样,揣测白天出现的每一张笑脸背后可能隐藏的危情,风吹过草尖时微小的震颤所指涉的隐喻,这样的思索在一夜的末尾通常会演变成惊惧的高潮,这个时候,也是她自感最难熬过去的时间段落。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她挺神经质的,每天凌晨时分都很恐慌。恐慌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无穷尽的失落,进至绝望。渐渐就有一些凌晨里,她生出一种新的担心。“我该不会,不会是要得精神病了吧?”天才们最容易获得精神病的青睐,而她,悄悄揣想自己,常觉得自己身上是具有一些天才性的,她的那些冷门但被部分人称道的小说,就是证据。是啊,梵高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黑格尔有强迫综合征,拿破仑和孟德斯鸠都有癫痫,就拿写小说的世界奇才来说,精神有问题的,也不乏其人,同样是受癫痫困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经衰弱的安徒生、有歇斯底里症的巴尔扎克……安倪越想越觉得可怕,越觉得可怕就越失眠,越看不到光明。她想象自己患了精神病后的样子,那一定是非常耻辱的。真要沦落到那种地步,她行动不受思维控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太吓人了。想想街上那些衣不蔽体却一脸得意笑容的疯子,要是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岂不是奇耻大辱?
这么一想安倪就觉得自己前景凄凉。怎么办?要杜绝成为一个他人的笑柄而当事者本人却无法感知的疯子,最妥善的方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还有能力决定自己言行的时候死掉。死掉?天哪!她怎么真的想到了这个,像海明威那样用手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砰的一声告别这个痛苦的世界,像芥川龙之介那样才三十五岁就干掉自己?喔!我的天!救救我吧!安倪小声在心里呼喊。有时候,她特别想把这些欲自杀却不敢的恐慌写出来,像她以前当作家时常干的那样,进行一番渲泄,尔后换取到些许内心的平静。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去写。写给谁看呢?这个社会并不欢迎、鼓励她这种文字,到处都是泛泛的、表浅的对平面生活的解说的故事,好像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最大概貌,好像全天下的人都是一沾枕头便呼呼大睡似的,事实呢,据她所知,许多作家都在失眠。去死吧!这些该写的不能写、不该写的却呈铺天盖地之势的所谓文学,她早就烦透这玩意儿了,还写它干吗?可问题在于,现在不是要她去充当一个文学的前锋、杀手,而是,仅仅只是,她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该怎么办?如何避免疯掉的结局,真的去自杀吗?天哪!不要,坚决不要,她不能,不要去做那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