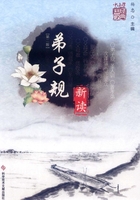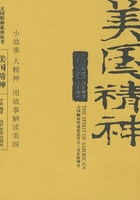纠偏·开创·深化——评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
罗执廷
这些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制度、文学生产体制这样的研究角度已经颇成气候,产生了不少学术成果,有效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这方面的先行者和较突出的成果有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杨匡汉与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孟繁华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洪子诚与刘登翰合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王本朝著《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2011年4月,中山大学的张均同志也出版了他数年钻研的结晶之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均这本书虽为后起之作,甚至书名都与先前的某著作雷同,却绝非对前人研究的简单因袭与低效重复。认真研读此书,并与其他同类著作细加比较之后,我确信,张均此书不仅是目前有关1949—1976年间中国大陆文学制度(或体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锦上添花之作,更是一部具有观念“纠偏”、思路“开创”和整体“深化”价值的精品力作,是对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整体推进与突破。我相信,它的出版将有助于学界反思目前同类研究的偏差与局限,有助于人们对目前盛行的机械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警惕,它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会日益凸显。我预测,它有望在当代文学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纠偏”,即对此前有关1949—1976年间中国大陆文学制度的许多不正确、不严谨的认识或结论的纠正,以及对这些不当结论背后的某种“认识装置”的纠正。正像张均所指出的,“文学制度作为一种事实上由多重观点、利益博弈而成的事实规则”,其本身是复杂的、动态的,甚至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但此前同类研究的诸多结论都有“简化”的毛病。笼统、简化就难免不合历史事实,难免有谬误。通过翻阅大量的原始资料及回忆录,张均发现“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类盛行的判断大多并不合乎实情,而是“含有较多想象成分,某些结论甚至不能成立”。比如,时论以为1949年全国出版资源被统制以后,党通过“行政与半行政的手段”,禁止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出版,所以“不仅‘鸳鸯蝴蝶派’,所有以旧式的传统章法、语言写作,缺少新思想新气象的通俗文学,都一起结束了它们在祖国大陆上的存在”。张均却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残存”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前鸳蝴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努力模仿“人民文学”,出版、发表不少新作,直到60年代鸳蝴派作家才彻底从文坛消失。张著还发现对鸳蝴文学进行打压并非党的政策,而是以丁玲为首的延安文人的自作主张。强调“改革”旧派文学,不全部否定而是承认鸳蝴文学的部分进步因素,留下调和、改造的余地,是中宣部定下的认识基调;但丁玲等个别文艺官员却明显违反这种基调,彻底否定旧小说,其私人意见通过其掌握的《文艺报》表达,对鸳蝴文学加以排斥。张均发现,此前的许多研究者都以后设视角来反推历史,或是带着某种先入之见进入历史,所以经常误读材料,倒果为因,将某项制度或政策运作的结果当作最初制定制度或政策的动机。有的研究者则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以历史抗议者的身份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视为应该否定的对立面,于是很自然地将本来复杂、动态的文学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简约为与国家权力、主导意识形态完全“一体化”。这种“认识装置”的偏差或曰“意图谬误”是造成将历史简化或理念化,导致认识与结论违背历史事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著之所以能够屡屡发现和纠正此前研究中的不当说法或结论,主要得益于重视“史料发现与考订”以及注重历史细节,坚持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著者说:“我并不反对‘一体化’等结论,但疑心甚重,且对历史沟壑和细节充满好奇,也许文学现场告诉给我的东西,会大有不同吧。故而所谓‘研究’,在我主要变成了找材料。”“几年下来,日记、书信、交代材料之类,让我对很多文学史‘基本事实’与‘定论’失去了信任感。”通过大量的资料发掘,他发现“文学制度在运作中遭到抵抗、挪用、歪曲乃至消解之现象”在1949—1976年间是普遍存在的。由此他对“一体化”等笼统而简单化的结论发出质疑:“这类判断是否过度放大国家权力?中国社会运作极其复杂,在历史上,国家权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宰制’社会空间与民众思想,极为可疑。”为了防止“历史的多重面孔”被“单面化”,他特别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梳理,这表现为对具体文学制度、政策的形成、演变过程(包括其中的折冲、迂回、反复)的“还原”式的呈现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比如他发现,这一时期的稿酬制度几经反复,在动荡中变来变去,其间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如周扬等文艺领导人和“群众”势力的反复博弈,作家群体内部因道德境界的差异或实际利益的分化而导致的分歧与争议,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等政治领导人的不时介入及立场、动机的差异,等等。作者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尊重材料,尊重事实,尽量还原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复杂性。
张著的另一突出贡献则是其开创的文学制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对此,於可训教授已做了精准的评价:“与此前学者所做的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不同,张均博士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旨在论析当代文学制度的发生,揭示在这个过程之中,种种社会政治力量(权力)的作用,以及因这种作用而导致的文学内外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正是这些势力集团(包括其中的个体)之间的博弈,使当代文学制度不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仅仅是一些无生命的机构、规则和政策条文,而是一个个‘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恩格斯语)的个体或集团活动着的历史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均是人化了文学制度研究,或曰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究,即构建制度、操作制度和被制度所构建、所操作的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这是张均博士的一大发明,一个创举,也是本书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确实,“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究”正是本书的特出之处与高明之处。近些年,文学研究界兴起一股“外部研究”热,文学的传媒研究、传播研究、文学制度、文学生产体制研究都是其类,这类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与弊病,比如片面、机械地看待各种外部环境、条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外部的环境条件因素当然会对文学的创作、出版、接受等产生影响甚至是制约作用,但外部因素首先必须通过文学活动的主体“人”才能起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勃兰兑斯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张著通过分析当时文学场中不同行为主体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文化心理、文学理念、个人性格、行为动机等的深入剖析,来呈现各项文学制度或政策的生成过程和具体实施状态及效果。这就比笼统、机械、客观主义的外部扫描更贴近历史实情。张均认为习见的文学制度研究模式或思维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假设”,即文学制度是独立的行为主体,它一旦形成,便会自动作用于作家,按照预设指令实现相应功能。他认为真实的情形是“在中国,任何公开规则,同时又与人有关,由人制定、为人所用。制定者、使用者不单纯是执政党的预设意图的机械执行者,作为活生生的个人,他们也生活在不同观念、利益与情境之中。作为制定、运用制度的人,他们才是主体。制度达成怎样的状态,发生怎样的功能,与制定它、执行它的人希望它成为何等状态,发挥何等功能实在是大有干系。而观念、利益与情境的混杂性,决定了制度状态与功能的歧异性与不确定性。同一执政意愿,在不同制定者掌握下可能形成不同的规则。同一条文,因运作者的不同目的、不同解释,亦可能生成差异性功能”。确实,中国传统上就是个“人治”的文化体,即便到当代,规范化的现代制度运作体系也依然没有建立或虽立而不行。注意到这种历史因袭的“潜规则”,无疑避免了书斋式推演的单纯与不切实际。
由于注重史料发掘和历史细节的梳理,以及新的研究思路的开创,张著得以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这一课题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这首先表现为它所关注的对象的扩展,比如它对鸳鸯蝴蝶派作家、对私营书局的文学出版的关注,对50年代的“同人刊物”问题的挖掘,对民间通俗(章回戏曲)读者的注意,对知识分子阅读在50年代的失败的考察等等,都是此前研究者较少涉猎或涉猎不深的领域。即使是习见的研究对象,张著也往往挖掘出了新的内容或得出了新的认识。比如在第一章“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之第一节“文艺机构的设置”中,就不是单独地考察一个个重要文学机构,而是从“单位制度”的视角做宏观和整体的考察,并指出:“单位制度及其运作,在有效地将中国带向现代化的同时,亦使文艺机构重蹈古代官方学术机构相类似的处境:‘自汉代经学与利禄结合以后,学术思想的领域便很难维持它的独立性,而成为通向政治的走廊。从博士制到后来的翰林制,传统的学术机构是附属于政府的’,‘没有自主的力量’(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新中国的文艺机构复活了这种‘走廊’现象。”这种认识不仅辩证地分析了单位制度的正反两面性,还在历史的纵深中加以审视,这就将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同时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维度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维度掘进。另外,张著视野开阔、架构周全,它的上编分别考察和梳理了文学组织制度、出版制度、批评制度、接受制度的生成和建立,下编则以更大的篇幅深入论证了上述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可以说是体大思精而又重点突出,相较此前零散或平面化的文学制度研究,有更宏观的驾驭和更深入的开掘。比如它有关“人民文学”、“新文学”、鸳蝴派和革命通俗文艺四分的看法,对自由主义文学批评与通俗批评(又分为鸳蝴型、革命传奇型批评)、政治批评(社论、编者按、工农兵评论和写作组)的区分,对知识分子阅读与大众阅读的分别考察,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细化与深化。尤其,张著对研究者自身的“认识装置”的反思,对文学制度中“人”的因素的揭橥,对当代文学制度与传统文化、历史之间深刻的“血缘关系”的发现,都体现了对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整体推进和深化的努力与成效。
当然,百密一疏,张著也存在少许薄弱点或盲点。比如,它对“文革”十年的研究就有些薄弱,远不及对“十七年”梳理全面和分析细致。“文革”期间的具体文学政策、制度当然与“十七年”有所差异,可考察与分析的对象也并不少,比如“文革”期间的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如红卫兵小报、厂矿、学校等单位的自印刊物等,它们是后来《今天》等民刊的滥觞,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关联意义)和内部出版物(即供批判用或专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欧美文学出版物,如作为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的重要精神食粮的所谓“黄皮书”与“白皮书”)是否应该纳入“文学出版制度”之中来考察呢?“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和地下诗歌的传播与阅读现象,作为统制化的“文学出版制度”的后果与对立面,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本书中“接受制度与阅读秩序”这样的章节中去讨论呢?似乎都不应该忽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