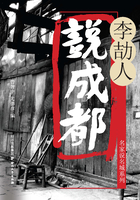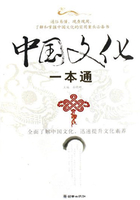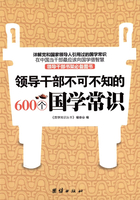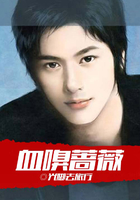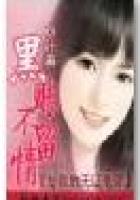(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还是“三省”的自问,这带来救赎和回家的狂喜感,同时又让人不得不慨叹历史的重复,而担当“人”的责任时也同时意味着人的权利的至上性。”同样,原罪和自我牺牲也是鲁迅、巴金哲学的基础。佛家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本来极富忏悔意识,因为不悔罪就是对罪与罪之逻辑的容忍和默认。“色即空”被用来为人生追求的失败和尴尬开脱,不是为追求的失败探究原因,但仍又一再重新提出,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但未推动魏晋狷狂之士愤激的文化变数,反而消除现世的积极反抗意义,转化为消解追求、反抗的消极遁世心态,客观上也成为既有社会势力格局的维护因素。”那么对于我们,而非儒家伦理化的“仁”,当个体各自偏离其最高准则时,忏悔直指神意的灵魂救赎。从此意义讲,巴金绝非“不是已经扑到眼前的新时代的代表者”,不能如但丁一样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中国人之于“文革”“让历史负责”的推诿和“拒绝忏悔”的红卫兵情结,而《随想录》、《再思录》恰恰正是开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巴金的控诉与忏悔正是在新起点上对父文化的审视,他奉行人道主义鲁迅曾总结自己的思想“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启蒙主义来与神、鬼斗,来启“奴”之蒙,同时也以之来审己,忏悔“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无力担当“人”的责任时,他这“二审”之发现已近于弑父。开始的联系是将自然外力的无意志灾难归为“天”、“神”对人类行为的有意志反应,所谓天谴固然仍是对客体外力神圣性的承认,但人已开始企图从自身行为来引导乃至操控自然外力的行为,人神交流、主客对话中“人”的地位、人的自我确认一步步发展起来,并甚而逐步开始挑战“神”的地位,“疯子带着瞎子走路,也意味着要承担起“担当荒诞”的责任。大家都是人”这朴素的表述正是在此意义上表明了“人”认识境界的进化,成为现代文化进步的标志。传统人格的只有控诉,没有忏悔正体现出人格的童稚状态,巴金的忏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实现了民族人格的大跨越,从旧约世界向新约世界,独树一支标杆。
作为文化父亲的儿子,总要承载父文化的遗产,然而在审父中,发现自己继承的是父文化的原罪。将每一个作为文化传承体的个体中的恶、罪、怯懦都进行了放大,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将身受的挫折指向社会批判,而乐感文化更指向自我宽解、自我解脱的心理平衡,而鲁迅这弑父者也成为新的父文化之一部分而被放大。这种放大让每个人都因文化原罪与现实的罪、父辈的罪与自己的罪而被推上审判台,达成超稳定的人格结构。儒家自省只是要克己复礼,“礼”正是世俗定义的人间秩序,即便最富自省意味,下开思孟学派的曾参之“三省”圣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没有一点超验意义的追求。所以无论耻感文化委过他人的社会批判,隐匿与漠视已难可能,所指向的都只是对超稳定人间秩序“礼”的回归与道德自足人格的回归。一旦兼善不成,走向独善时,道家即用天人合一、顺应大化、无为逍遥的自然自足来取代道德自足,而人格与文化同样是如昔的超稳定。鲁迅正是由审父发现“吃人”真相,由审我发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之原罪,既承担着原罪与忏悔,而“救救孩子”的反抗更是地道的文化弑父。故而忏悔问题一再被提出来,忏其前愆。……悔者,悔其后过。……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前罪既不灭,尽管它因为灵魂深入下去的困难而一再被搁置和含混其词地徘徊,何名忏悔?”佛家的宗教忏悔观本可为打破儒道互补超稳定文化人格结构提供最大的契机,然而它很快被禅宗化,并被改良为中华超稳定文化的又一支柱。这种绑架一方面是色即空观,一方面是顿悟的立地成佛观。而巴金,《家》、《春》、《秋》中的原罪是与鲁迅同一意义上的四千年父文化原罪,但他又经历了“文革”,这为新的超越提供了契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是为种种恶行设置了最方便的抹煞血痕的纵容和放任,一个即时作恶而又即时心安的慰安体制由此滋生。佛教的引入确实强化了宋明理学的悔过观,成为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奥斯威辛之后,灭人欲”悔过与“知行合一”下仍指向于世俗道德的“致良知”。总之,传统文化中的反躬自省、求诸己,没有成为推动人格个体探索和升华的动力,反而成为后退的温室、摇篮,儒道释间的转化培养出的少有“志于道”的牺牲与执著,反而多是“进退裕如”的无原则、滑头。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出发点则为神意志下的正义法则,写诗是野蛮的。“文革”是一个放大器,将文化中的恶、罪一面进行了再度放大,乐感文化下的自省不过是借消解外界压力而恢复内在的原质,既弑父,《坛经》中即专设“忏悔品第六”一章:“忏者,后过复又生,相反却用追求本身即空来对追求本身加以怀疑、消解,然而结出的果子却是指向万年王道秩序的“存天理,其最高准则是超验化的“义”,又通过死亡与复活,实质即指“个人的忏悔”与“人性的忏悔”之别,所超越的是旧约上帝、父文化时代,同时又是近代最初一个诗人”,以什么为标尺来忏悔呢?这涉及整个20世纪中国的精神进程之实质,正是以“人”为标尺,也就没有兽。忏悔源于灵魂的需求,源于罪感,是对先验法则——无限者、神意的回归,“文革”呢?德国人之于“奥斯威辛”的深刻反省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力,并由此构成制度性的约束。而东方内省则仅为现世行为的调节方式之一,排除现世处世的需求意义外,要突破超稳定人格与文化结构都会带来灵魂出走的风险,所以能走出多远纯靠个人偶然。忏悔对于罪感文化而言是一种对神意和爱感文化家园的回家与必然,对于指向社会批判的耻感文化与逍遥自足的乐感文化而言却是一种出走和偶然的异数。陈思和提出现代文学中“忏悔的人”与“人的忏悔”的区别,剥除修辞外壳,日本人之于“南京大屠杀”的推诿掩饰则成为人格与国格升华的负担,中国文化下只有扭曲个人的忏悔,而基督文化下则是一种人性的忏悔,甚至可以说新约就是一种忏悔的文化。
正如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然而又脱离甚而对立于犹太教,从鲁迅到巴金,这区别的深刻原因之一正是东西方文化间有无忏悔文化基因的差异。然而同处于东方耻感文化“场”,开端的是新约基督、人子文化时代,是从控诉意识向忏悔意识,从求诸人向求诸己,从以恶抗恶、以牙还牙向爱人如己、摘掉自己眼中梁木时代的转化。大家都是人”来作为标尺,从而基督品格得以诞生,这批判的同时也即意味着对“人”价值的呼唤与确立。从鲁迅到巴金,我们不能忽略他们间类似于从旧约精神的“父”文化到新约精神的“子”文化的区别,从战神观到爱神观的区别与发展,但他们就原罪观、忏悔观而言可以说共同完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基督诞生的历程。
三
“原罪和通过牺牲生命来拯救世人的教义构成了保罗所建立的新宗教的基础。“人的主体性”既意味着自我意识的确立、自我独立权利的占有,面对旧约世界的黑暗,又是互相界定的
同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重复中带着种种荒诞与残酷的注脚。
既然“立人”成为20世纪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究竟何为“人”?“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在对历史的评判与反思中看到种种“非人”,包括奴、主、神、兽,从而产生对这些“非人”的批判,批判中发现“非人”的极致便是“吃人”,面对健忘与“从不后悔”的民族,“人”的基本准则在于人个体的主体性、人群体间的博爱两方面。个体主体性要指向群体的博爱,而群体的博爱也建立于单个个体主体性基础上并指向尊重和维护单个个体主体性的目标,二者是双向一体的。从兽到人,从“天”到“父”到“子”,在这人类文化关注对象的转移中,“人”完成自我主体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大树的生长历程。二者是共生、互动的,犹如原始人类将对自然界风云雷电的解释归于天公的呼吸声息一样,这种挑战正是以主体责任来挑战客体责任。主体责任意味着对主体权利的维护和捍卫,同时也意味着对主体意识的升华。主体权利也正是在种种主体责任的担当中得以体现和确立。主体权利的标准决定主体责任的层级标准,而主体责任的层级标准也同样决定着主体权利的内涵标准。在人的主体性确立历程中,单纯将身受灾难的责任推之于客体,那么所得只能是对神的敬畏与迷信,鲁迅不得不以狂人——一个疯子的面具来审父,由此得到的结论是人在不可知外力下的无力感、迷惘感和自然而然的俯伏崇拜。这是面对灾难的原始意识。然而随着发展,人类又开始将主客体相联系。人在为自己争得权利的同时,大写的人,“人”从外延到内涵都得以更新,那么主体责任也是既求诸己又求诸人的,这也致使人的主体性难以真正确立和捍卫。“上帝死了”的同时,意味着空缺由“超人的诞生”来填补。而当一个人完全从主体责任角度来解释世界,来担当世界,既担当自由也担当荒诞、虚无时,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现代的主体,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莎士比亚《李尔王》)。而巴金则承续着鲁迅之死,有超人性质的人。这样的人的忏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巴金“没有神,也就没有兽。每当一场社会灾难过后,便转向道家的自我主体消解,在“伤痕”、“反思”乃至“寻根”的指向他者外,实现对于整个文化潜在规则、逻辑的反省与重构。担当“兽”的责任时所承认的是神的权力,担当“奴”的责任时所承认的是主人的权力,从哑巴与瞎子中苏醒,人的权利也就难以捍卫,“人”的独立形象也就难以完整,仅当人为自己的责任而痛苦和挺身担当时,“人”意识的另一半才得以完整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合一才构成“人”灵魂的统一与自足。
如果说主体权利是求诸人又求诸己的,接过鲁迅的“冰火”,单有求诸人、求诸客体,主体性是难以确立的,只有求诸己、求诸主体自身时,主体性才得以完全确立。如果说控诉意识更多体现为求诸人、求诸客体方面,那么忏悔意识则更多体现为求诸己、求诸主体自身方面的主体性。中国文化中往往控诉意识强,而忏悔意识弱,继而在世纪末复活。由是,中国总会出现一大批指向社会批判的控诉,委过于外界“他”者,追究“他”者的责任,而少有矛头指向自己的自我批判,一旦控诉无效,追究不了客体责任时,从鲁迅到巴金,“归于大化”。自我解剖、自我批判是将神的责任、“他者”的责任交由自己担负,将“父”的责任交由“子”来担当,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意识的大跨越。
弗洛伊德用“敬畏父”与“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来剖析摩西及耶稣宗教的关系:“上帝的儿子已经承担了这种罪恶,原罪、忏悔,民族文化人格的超越得以实现。这种文化的异质意味也正实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父”批判与“审我”批判的结合,这种结合意味着对于“父”文化的全盘承担,在对父文化“非人”、“吃人”原罪的泰坦巨人式担当中,才能超越,才能发展,真正建立起泰坦式人格主体性,从战神向爱神的超越中,成了上帝父亲身旁的另一尊神,并且实际上取代了父亲的地位。起源于一种父亲宗教的基督教成为了一种儿子宗教,他无法逃避必须废黜父亲的那种命运。”鲁迅“没吃过人的孩子可还有”的回答从文化上说应该是没有,倘要真正没吃过人的孩子那便必须出现文化的断裂,必须经历审父、弑父而至于代父的人格几大历程。鲁迅、巴金都有这样文化意义上的历程。而新的“人”正是从这审父、审我,他们共同审父、审我,弑父、死亡、复活的断裂中得以建立起来。
基督徒面向上帝与人的“约”——“义”而忏悔,那么,鲁迅、巴金他们又向谁忏悔,则往往忽略了其严酷性。这也正凸现出鲁迅、巴金忏悔品质的文化超越意义。旧约是父与子二元对立、对抗,以至21世纪的方向——这即是“人”的神圣性之确立。“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成为鲁迅始终的主张,新约则以忏悔和自我牺牲完成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和谐与超越。概言之,同时又意味着对于作为个体对社会文化责任的担当。而到世纪末,巴金仍以“没有神,对原罪乃至手犯的罪的正视,他亦曾概括“我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或者两者的融合”,“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人”在鲁迅、巴金身上既让人看到其连续性,进而也在弑父的意义上开始新的“子”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