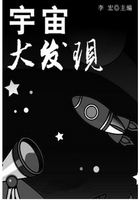我起身,向里间走去。经过苏二小姐身旁的时候,她哂笑道:“同我姐姐一起抚琴,你只会是自取其辱。”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我本就不如大小姐。这般打算,正是为了保全面子。
从里间出来的时候,楚殇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要说话了。我率先开了口:“大家不如将答案写在纸上,这样更能考验真功夫。”
苏夫人遂遣下人送上了笔墨,她说:“我倒是没有听出琴声里头的玄机。就姑且当个看客吧。”
此时,云大哥坦然站起身来,说:“我不会笔墨。”
透过他散垂的黑发,我可以见到他深邃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那神光透着些许冷意,如黑夜中的月光一般,虽发光发亮却给人落寞遥远之感。
大小姐眉眼盈盈地说:“能将自己的不能之处,说得如此坦然,可见云公子是真英雄。清韵佩服。”说完,朝云大哥的方向微微福了一下身子。
我从未见过我的白衣公子笑,但此时此刻,我分明见到了他的笑容——微不可查却曳人心旌。我的心一漾,尔后一沉。她懂他。
楚殇一边在低头写字,一边说:“刘备初投袁绍时,便将织席贩履、屠酒卖肉说得坦白淡然,云兄心胸可见一斑。”
苏夫人建议说:“不如等楚公子和小女写罢,再来听云公子的见解。”
此时此刻,苏二小姐已经被我拖下了水。她不通乐律,却又不肯认输。只贼头贼脑地越过我,向她姐姐求救。大小姐此刻有些心不在焉,自然听不到那微如蚊呐的求救声。我得意洋洋地冲二小姐做了个鬼脸。她瞪了我一下,便低头咬牙将答案写了下来。
楚殇与二小姐俱已停笔。云大哥便站起来,说:“第一位抚琴的是苏小姐,第二位是妙双姑娘。”
苏夫人问:“她们既然是弹的同一首曲子,你是如何分辨的?”
他忽然看向我,眼光淡淡的,说:“以前曾听一个人弹过这首曲子,所以能分辨出来。”
“云公子果然天赋凛然。”苏夫人又问,“你只听小女弹奏一遍,竟能辨出她的琴音?”
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尔后点头,坐了下来,目光浸没在夜色中。
我手中拿着二小姐的墨宝,正准备念。她仓惶地站起身来,说:“本小姐写错了顺序。”她将双手迭抱在胸前,说:“第一句说的是你;第二句说的才是姐姐。”
我看了半天,终于将那一团团的字认了出来,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因为这两句诗实在是很经典。
苏二小姐等地不耐烦了,大声说:“你倒是念啊!难不成不认识字?”
既然你让我念,那么,我就念了:“二小姐觉得我的琴音是——艰难晦涩强入耳,三月不知肉滋味。”我咽了咽口水,继续念,“觉得大小姐的琴音是——君王若能闻此曲,从此君王不早朝!”
念完,我就将手摊开。意思是:这事儿跟我没有半分关系,我就是个跑龙套的。
楚殇毫不客气地捂着肚子大笑起来;苏大小姐用帕子掩着面;云大哥倒是处变不惊,浑若无事;苏夫人已然涨红了脸,大声呵斥:“我请了师父教你琴棋书画,你却不学无术!平日里只顾着舞刀弄枪!你看看你,你哪里及得上你姐姐、及得上妙双姑娘半分?”
苏二小姐虽耷拉着脑袋,拳头却握得很紧。此时此刻的她一定很想将我碎尸万段。但是,在将我碎尸万段之前,她的手可能是要废了。因为苏夫人罚她将《诗三百》抄五十遍,并勒令她两日之内交货。
我同情地看了她一眼,听楚殇的答案去了。他亦写了两句诗,第一句是: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第二句则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楚殇解释说:“清韵的琴声停得恰到好处,是情深而停。好就好在熟能生巧,琴音如一位深谙世事的美妇。妙双却恰恰相反。她应当是初次尝试这首曲子,探一步走一步,顾忌自然就多些。琴音似一位情窦初开、涉世未深的少女。”
大小姐接口说:“楚大哥的解释可谓精辟。妙双姑娘也的确厉害,只听我拂了两遍琴,便能将曲子记下来。”
我说:“还是大小姐琴技卓绝,妙双不及。”
我的琴技本就不如大小姐,若是用我拿手的曲子,万万占不了上风。桃子姐以前教我抚琴的时间极短,我听曲的时间比练曲的时间多得多。日子久了,便练就这么一手本领——曲子只要听上个两三遍,就能知道个大概。再者,听曲的人见不到真正抚琴之人,他们若在我抚琴的时候,将抚琴之人想做苏小姐,那入耳的琴音自然也就婉转流畅一些。
晚宴散去,楚殇问我:“你真的不认识云淼?”
“假的,我以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