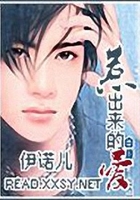何曾料公主归画卷◇空伤情御史会良娣
话说天枢与众姐妹在宫门前别过后上肩舆各自回殿,天枢正巧与妙柑同途,不免再宽慰她几句。妙柑因得了新华相赠的乌木镂花宝月匣,一直捧在手里笑吟吟的,天枢见她情致甚好,便也渐渐宽下心来。来至后殿,大家分路走开,妙柑一行自回芳菲苑去,不在话下。
蘅芷苑处派来迎天枢的婆子见她回了,忙凑上来悄悄回道:“方才有三公主那的几个宫人来,还有些个东西,底下人也不敢随意启了瞧,正等公主来定夺呢。”
天枢唔了一声,径自往月洞门里来,守在殿外的宫女忙打起帘子,随行的宫女手里提了十几只灯笼,将中庭里照得十分真切。天枢吩咐攸伶去打了水来栉沐,自个儿却想也不想便进了书斋,一进门就见绿茵正候她,拿手指了案上那几个大大小小的盒子,竟是哆嗦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天枢取笑她:“亏你平日还算是个伶俐的,这会子怎又笨嘴拙舌了?”说完,上前掀了那几只盒盖,看罢却不由皱眉。除了给妙桔退还来的那幅芰荷图外,其余不过是香料、药饵同些个精致衣料。绿茵捧了匹鹅黄缎子连声说极配天枢的一件葱绿色绣袄,天枢摇着头命她搁下,又吩咐不准动这些盒子的任何一件。
攸伶捧了金盘琼酥进来,天枢略吃过点糖渍蜜饯,便盥梳过睡下。卧在衾内却不得成眠,辗转了半晌又听水钟里叮咚起响,竟已是二更时分了。衾外守值的宫女睡得酣甜,她便不由轻叹了口气,摸过搁在枕边的一根花签与一张芙蓉笺来,抚着签上青莲更是愁思百结。那墨漆上的字迹峻拔,天枢默念着那句“一寸相思一寸灰”,不知为何竟牵扯得心口撕心裂肺地疼痛起来。
到了后半夜,天上又落下点雨来,清华坐在床沿上翻书,门前七彩金丝盘花帘垂地,将那淅沥沥的雨声拦断在外。新华立在碧纱窗前,与清华隔着一层软烟幔帐说话:“依你的主意,南诏祈雨之事让我同君儿去?”
清华合上书页,说道:“不是你同君儿,只你一个。”
新华不禁啧啧两声:“你倒还真舍得我,偏又是极宠君儿的。”
清华听她埋怨,思忖半晌,乃说道:“依你说的,我反倒该是不宠君儿才叫正经?南诏那鬼地方这会子正是旱得天人共怨着呢,你执意领着君儿去,不怕她耐不住暑气?况且依我看,你此番去南诏不过是应个理儿,若真能求得雨来,倒是真真滑稽了!”
清华听她话里大有文章,不觉也吃了一惊,忙摞下手头理着的匣剑,急问道:“怎么说?你可是听着阿祈那透出的风声了?”
清华却轻轻嗽了一声,说:“倒也没什么,你且跟太师走一回便是。”新华见她再不肯说,遂掉转脸去望着窗外,那卷雨楼前簇簇的蓼花给雨打了一地,有风卷了过来,卷起几圈落红旋儿,转得几转便又缓缓坠下了,碾在尘里躺着,再也没能起来。
新华想起曾有人对她念过这样一句诗:“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她素来只贪爱骑射,不懂这些愁人的诗词,那人也说若她知晓里头的愁意,便不得这般欢愉了。转念又道:“今日我领了六公主往观风堂去,她抓着有些个荷包扇套的不肯放手,我想着也不过是二哥哥旧时的玩物,便随手都送了她。回头二哥哥若要问起,你也替我遮掩遮掩。”
清华嗯了一声,喃喃只道:“莫说他如今也没个要回来的讯儿,便是日后真回了,他也早不记得那些了。”
翌日又是响晴天气,天枢是黎明前方睡过去的,偏又得例行早起请安,不免有些起床气。攸伶上来服侍她换过衣裳,天枢取了青盐漱过口后,燥热得连粥都喝不下。到了正午时分,地底下像是能窜出火来似的,膳房里送来的羹汤动过几勺便搁了,直恨那毒辣的日头不懂体谅人。
绿茵的嘴唇上烧得紫绛皲裂,其余小宫女也大多东倒西歪的,苑里唯有攸伶若无其事般里外忙进忙出。天枢看了会她与下头宫女校口,又听她骂过几句后稍有心软,撵了那宫女下去又亲自舀过水来浇花泼地,不觉暗叹数声。攸伶拾掇完廊前盆景,进来劝天枢再睡,天枢摇了摇头,只肯倚在榻上看书,静了片刻又突问:“你再着人去瞧瞧,三姐姐可从皇后娘娘宫里回了?”
这里正说话,忽见妙椋领着桑琼进来。甫一进门,妙椋就拍着手笑道:“咱们宫里也就阿枢有诗书风格,外头宫女们拌嘴,她也能照例看得下去。”
天枢只道:“我倒是没听见什么,不过是允了稍歇歇,她们便嬉闹着玩耍罢了。”
妙椋忙劝道:“你是天生的好性儿,又怜香惜玉,可见是由着她们胡闹惯了。若要真闹出些个幺蛾子来,大家都没脸面。”
天枢闻言,放下书坐定了,道:“阿姐说的是,可巧我正有话要问呢,阿姐若无旁的事,只管也坐下听听。”说着,便命攸伶过来跪下,问:“昨儿个夜里在楚府,绿萼姑娘同惊鸿姑娘究竟是为着何事厮打?你且一一与我说一遍。”
攸伶当即黄了脸,搪塞道:“左右不过是嘴里有个三言两语的,一时说得不上道便争起来了。”
天枢道:“我知道你们私底下爱拌个嘴的是常有,但昨日是在楚府上,况且有几位公主在一边瞧着呢,竟也能争闹起来?我只问你,你可曾掺和到里头了?若无,这话便撇过了不提;若有,我得依着你到底说了什么,再来断你可恕不可恕。”
天枢尚未说完,攸伶急道:“奴婢自始至终都只一个劝字,未曾插过半句闲话!”
天枢神色渐转和润,亲手搀了她起来,道:“那就好,你再说说,到底是因着何事?”
妙椋坐在一旁也没了言语,只听那攸伶跪着再道:“昨儿在河边,几位公主跟姑娘们放着莲灯本是好好的,偏生惊鸿姑娘说了句:‘红山宫里也满是珠光宝气的,可怜绿萼姑娘没福分,怕是看不着了。’绿萼姑娘气得不行,一把揪住了要打,幸亏婉柔姑娘劝住了。惊鸿姑娘却不肯饶人,拉扯着也抓了过去,奴婢想公主们都在呢,我还能袖手旁观不成?便也跟过去劝了几句,说是何苦来呢,犯不着为着一句两句的大动干戈。”
听她说毕,天枢沉吟半晌,道:“难为你竟能记得这般齐全。”
妙椋也道:“你这屋里也就属这姑娘说话伶俐,是个极难得的。”攸伶因见妙椋在此,忽又不再出声,只站起身子来退立一旁。
天枢却蹙眉再问:“既这样,那六姐姐又为什么哭了?单只惊鸿姑娘提了句红山宫?”
攸伶目光微垂,不敢与她对视,想过一想才道:“因着惊鸿姑娘又说,绿萼姑娘背弃了主子投靠了公主您,赶明儿得了高枝,好嫁到楚府里当姨娘去,倒是比主子更好命了。六公主听说,一发动了气,煽了惊鸿姑娘两句骂她浑说。绿萼姑娘也骂她败坏公主您名声,便又上前去同她动起手来。”她说时边拿眼角余光斜瞥天枢,却见她神色如常,瞧不出脸色来。
天枢心下纳闷,微一踌躇方道:“与我什么相干,你们几个爱搬弄口舌,倒拿我来垫背不成?我倒是不知,母妃几时跟楚家结了亲的?”
攸伶不答,只拿眼看向妙椋,妙椋便绞着手里帕子冲桑琼扭嘴儿。桑琼会意,忙扯开话头去:“我们公主今儿个来,是想请十三公主一同到太后跟前尽孝道呢。眼下外头天晴得透彻,整好去上恭殿里请安。”
天枢已知攸伶不肯说定与妙椋有关,不觉冷笑道:“这会子正是皇阿奶困倦时刻,我们干巴巴地跑了去,少不得是要给拦回来的,阿姐何必偏要赶这点子功夫?”
妙椋强笑道:“妹妹说的是,阿奶才从佛寺里回来没几日,晌午前事又多,这会子定是不喜人去打搅。咱们若去了,只怕她要烦腻我们的。”
天枢这才道:“阿奶怎会烦腻阿姐?等日头下去些,我陪阿姐定省去。”她一面心头冷笑,一面回过头去又问攸伶道:“我问你话呢,你怎又傻住了?”
攸伶心头乱得紧,慌乱得没了主意,只得回道:“是五公主先说,新华小姐跟见君小姐待各位公主皆是一视同仁,惟独清华小姐对公主您另眼相看,怕不是要请您去给她当嫂子……”她是未出阁的姑娘,家里头门第虽微但也是教养得当,此番转述起这般的闲话来,早已是羞红了脸。
天枢不知众姐妹看她与清华交好竟是这等考量,当即煞白了脸,口气里也愈发冷言冷语:“我才想起,三姐姐那打发人来让我去坐坐呢,这会子正闲着,想去枫霜院走一趟,便不留姐姐吃茶了。”
妙椋听天枢如是说,知她生恼,暗道今日来问之事想来是不成了,也就顺水推舟,道:“那我同妹妹一块儿出去,也好再闲磕两句。”说着,她立起身来,侍立在后的桑琼过来替她整饬裙摆。
天枢由得她跟着,吩咐攸伶去取了妙桔处还来的芰荷图,也不顾烈日正毒,打了伞就往枫霜院里来。妙椋与她闲扯过几句后,便在含凉殿外分了道,天枢二人踏进垂花门时,惊鸿正坐在廊下摆弄针黹,见她来了,忙起身笑道:“我们公主才说十三公主定要来,我还不信呢,这不,可就来了?”
天枢问:“三姐姐歇了午觉不曾?可有起了?”
惊鸿答:“午膳吃了点子酒,竟是有些醉了,才睡下的。”
天枢点头,随着惊鸿入了侧殿方坐定,却听里间有人大笑起来:“我就猜着你该来了!阿枢进来吧。”
天枢本是憋了一肚子气,既瞧她爽快,倒也不再见外了,挑起帘子进去问候道:“惊鸿姑娘说三姐姐又吃酒了,太子哥哥可是千叮万嘱过太医叫你忌口的。”
妙桔并未躺下,正立在书案前提笔,几副和田白玉腕镯套在她臂上一晃一晃的,相互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来,见天枢又带了卷轴过来,不禁失笑道:“我既还回去了,你便不用多心,原本就没曾想要夺你爱画,不过是惊鸿那小蹄子平白给我惹出点事来罢了。我已叫她好生立着规矩,你不必放在心上。”
天枢见她如此说,便探她口气说道:“惊鸿姑娘那日来时,我说了是送三姐姐的,哪有再讨回来的道理?”
妙桔见她这样,知她心疑,登时摞下脸来,嗔道:“赶紧打住!我这明眼人一瞧就知道,定是她那会子与你说了什么,你才让她将画带给我。”她搁下了手里玉杆狼毫,过来伸指在天枢额角一戳,虽未用力,但那尖锐的指甲也刺得天枢星星生疼。天枢无奈,只得再跟她说了会子话,说到妙桔乏得醉眼迷蒙了,方才告过辞后退了出来。
中庭里的石榴已渐渐败落,只余了一两枝。那紫薇与朱槿却是开得正盛,如艳霞含蕊,照得那花边廊庑一带满是彤红之色,绚烂至极。风过南墙,落红丛中伫立着个容长脸高挑个儿的年轻女子,天枢欲从她身旁悄悄而过,却不想给她叫住了:“十三公主。”
天枢苦笑:“冯良娣近日安好?”
她是太子宫中清凉殿里的姬妾,会在这里撞见倒是不奇怪,只可惜天枢身负天命,不免对她心存芥蒂,口里也只淡淡敷衍了她几句,正要极力寻个借口脱身,忽听身后有脚步轻响。天枢只道是太子宫中人,忙转过头去看了一回,却不想是位身着绛红色曲领大袖公服的年轻公子,腰间束一枚银绯鱼袋,正是四品官员的制袍。
天枢素来不见外臣自然不识,依她的身份也不好随意让外人窥见,当下皱过一回眉头后,拔腿就走。那公子却失魂落魄般唤了一声“小珠”,惊得天枢又回头瞥过一眼,只见他站在阶前苍松下,身形也恍若松柏一般清隽挺拔,面容俊秀眉眼磊落,神色间却混了三分愁苦与三分惊喜,直盯着天枢身后猛瞧。
这一面瞧清楚了,天枢胸口的震荡不啻五雷轰顶,心头跳得像是心窝里的血都要涨破表皮迸发出来,仿佛是适才妙桔握住的那根玉杆笔上的凝墨,蘸饱了清水便一滴一滴地滴到青花瓷水盂里,搅上一搅,那墨汁缓缓地洇化开来,慢慢在水里恣意扩散。
天枢已是红了眼眶,情不自禁地唤道:“四弟……”话一出口,她已是悔得茫然失措,只好呆滞着瞪着那公子。
他似是才回过神来,不敢再看天枢身后的冯良娣,疾走两步到跟前,行下礼去,道:“臣褚凡,请公主安,请娘娘安。”天枢只觉脑内訇鸣一声,耳里不断回旋着他喊的那声“公主”,那声音叫得她耳朵疼得半边脸都要烧起来了,眼中更是痴望着他,不舍得眨上一眨。
是天权啊……那是她的四弟天权啊……
事起仓促,接连窥得两位宫闱女眷尊容实在是大意,褚凡像是才透过气来似的,赶紧道:“臣请告退。”说完,急于撇清关系一般要从天枢身侧擦过,那绛色袍角落在地上的影子忽的就移过去了,鱼袋上的流苏也是丝丝缕缕都飘过去了,天枢的眼泪也像是掉了线的珠子一般淌了下来。
褚凡顿觉尴尬,愣在当场不知如何是好,冯良娣却已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庭中只剩天枢二人。天晴得人燥热,寂静无风,天枢无声无息地落着泪,任凭攸伶递上来的白绢怎样的擦都擦不尽。攸伶几时有见过天枢哭成这等模样?心下大疑,便狠狠剜了褚凡两眼,手里一面卷着帕子替天枢掖着鬓角泪痕。
过了好一会子,天枢才稍稍缓些过来,不由腼腆道:“让大人见笑了。”她舍不得走,只好再同他有一句没一句问着,褚凡恭敬地一一作答,也不敢再抬头看她容貌,只能在心头纳闷不已,竟不知自己是何时与这十三公主扯上了干系,居然能令她一见着面便哭成个泪人儿。天枢恋恋不舍再问过他几句散话后,心知此举着实不妥,少不得还是命他退下了。
院中极静,天枢的脑中却如有雷霆万钧般的嗡嗡铿鸣,掩埋在心底多年的记忆由模糊转而清晰,前尘往事尽皆纷沓而至。她像根木头般呆呆立了好久,立到双足软绵无力,立到攸伶在耳畔急切叫唤她,她才渐渐从心底里涌起阵阵寒意,哆嗦着抬起了步子。
地下的两道孤影斜斜延伸至东边的紫薇花丛中,天枢怔怔地看了会那团韶华盛艳,灿烂得似是要灼痛她的眼。她动了动唇欲言又止,攸伶见她这般形景,只好抽出帕子来再替她拭汗,又好生劝过几回,天枢才道:“你替我收拾这花儿放到香囊里去,赶明儿我好送十二姐姐礼。”
正是:斜阳残照,紫薇朱槿。看朱成碧愁眉聚,多情争奈似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