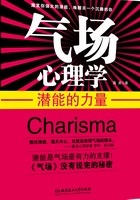娇绿茵绵绵娇嗔意◇妄褚凡切切妄言语
再说天枢满心皆是银饷不足的事,恨不得一改素日癖性,将那些输光的金叶全讨回来。妙椋笑得直嚷“千载稀逢”,文贤妃又道:“那会子你父皇不知为何,偏要给你起个‘枢’字,我不好说个不好,可也不愿说好。要真是这字害了你,那我就真罪过了!”一面说笑,一面向北告过罪,终究还是掌不住,跟着妙椋一齐大笑起来。
天枢任她们取笑,只推说身子沉得厉害,头疼目眩,要回苑里去歇息。贤妃忙笑道:“等一齐用过膳,再走不迟。”天枢只道“捱不住”,贤妃便只好命攸伶扶她回去,又嘱咐说:“等药煎好了,同膳食一起送过去,你盯紧她喝了,再让她躺下疏散疏散。你再过来回我。”攸伶连忙应了。
暂且不说那母女二人在殿中讨论天枢的婚事,只说主仆二人回去,天枢用过膳后仍是长吁短叹,闷闷不乐。攸伶实在不知出了何事,也不知怎样劝好,便也只能随了她去。绿茵见天枢嘀咕着翻小柜子里的碎银锞子,疑惑道:“公主要取什么钱?只管问奴婢,哪样搁在哪里,奴婢都知道。”
天枢听说,就问:“咱们有多少银子?”
绿茵便取过柜中的檀香木妆奁盒来,打开一看,多是天枢向来不用的头面首饰。金簪银镯自不消说,那翡翠石在光照下愈加通透碧澈,猫眼儿滴溜滚圆,泛着绿幽幽的光华,珠子里倒像是有一泓水在缓缓流淌。天枢摇头道:“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银钱,那些好拿来花的银两钱。”
绿茵见说,忙将那盒子塞回柜中,另从底下格子里翻找,翻出了好些旧物。天枢取了些小时压岁用的紫金如意锞子来,暗想成色虽不足,可到底还是金子,一时就放在荷包里。绿茵再找出十来贯清钱,天枢便问:“这能值几个银子?”
绿茵却道:“于公主来看自是不值钱,不过也能算是奴婢几个月的月例了。”
天枢一呆:“就这点?”
绿茵笑道:“就这点子,底下还有人要眼红呢!这些是平常用来赏小丫头们的,娘娘说了,公主月例不多,不好随便拿银子赏下头人,所以叫咱们备下这些钱。要哪个规矩了,攸伶姐姐就赏一串下去。”一面说,一面将那些钱都放在簸箩里,天枢见另有用途,便不好再多说。
天枢奇道:“那该用来赏人的银子又花哪里去了?全给母妃说免了,你们就真免了?”绿茵更是笑,再打开格中抽屉,天枢见里面排了整整齐齐的整锭元宝,便知这才是赏外头人的,因问:“你们先前怎么个用法?说来我听听。”
绿茵道:“有别个宫里的姐姐送大宗物件来,咱们就赏来人碎银子,又托她谢殿中掌事的姐姐,这就要给大锭子了;平常小厨房里有孝敬汤药的,咱们也只赏碎银,但要是娘娘殿里的公公跟嬷嬷来了,又端着娘娘赐下的人参、燕窝,咱们自然要给整银,不好给戥过的,他们一准看不上眼;还有一宗,底下人聚在一起吃酒赌钱,被攸伶姐姐抓着了,那钱台子上的都充公不说,还得回了娘娘罚去月钱。可一罚就是几个月,他们平日也没点积攒,攸伶姐姐心倒又软了,偶尔见他们差事办好了,也便赏两个。”她一股脑儿都顺嘴说来,停也不停,将自己也说笑了,又道:“真要都数,连奴婢都得好好想想,再翻翻账本子。不过宫里大多是赏的青铜钱,不比市面上的毛钱杂乱,咱们给的虽少,就那么一吊两吊的,可要真拿出去用,也好换一石两石的白米。”
天枢一听好换大米,更是听得专注,又问:“一两银子好换几石米?”
绿茵想过一想,方道:“奴婢在家时听阿娘说,她还在家里当姑娘的时候,半两银子就能买一石了。后来她跟了我爹,又养了我,米价渐渐涨到一两银子一石,等到我进宫时,已经要二两了。”她说着,偷偷瞟了天枢一眼,怕说错什么话,又见天枢神色间并无异样,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天枢想不明白此中缘由,只得再问:“那攸伶一个月的利钱有几个?”
绿茵亦是笑道:“先前她是二两,这会子已加到四两了。”
天枢正要再问为何,攸伶已走进来,点着绿茵额角骂道:“还不去将嘴上的胭脂擦了,下去吃你的饭去?!就会在这里教公主浑话,我拿几两银子,你就眼热成那样?”绿茵撇嘴一笑,收拾好匣柜就退下了。
天枢见她端来的是药碗,不禁又是掩鼻,攸伶忙劝道:“喝了才会好,等你好了,才不用再喝这劳什子。”天枢听了这话,方才屏住气几口灌下。攸伶替她擦了脸,再问:“好好的,说那些米啊银啊的作甚?”
天枢却问:“先前二两银子的时候够用不?怎的又凭空涨你二两了?”
攸伶道:“够了,够养活一家人了。”说毕一笑,再朝外殿回望一眼,见宫人们大多下去捧饭置菜了,才道:“真当那二两是赏我的?一样是伺候公主的人,只升了我的银子,别的宫里人还不要闹去?”左右复看一看,又压低声说:“是因绿萼姑娘没了,咱们娘娘可怜她,拿自个儿的体己钱另置一份,就是我每月多出来的那二两。我也只敢说收着,还真敢用了它去?少不得等绿茵那小蹄子再大些,往后出去时,我一并还她就是。私吞个死人的钱,旁人说不说闲话我不知道,到底我是不得心安的,花了还怕夜里做噩梦呢!”
天枢见她回得有趣,便道:“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我做主,大头都给绿茵留着,好让她回去安慰她娘。多了的你就拿了去吧。”攸伶只顾叹气摇头,也不答她,天枢知她心肠好,断不肯贪图这点子小财,便也就收了玩笑话。
攸伶这才道:“刚才的缎子里,最名贵的是那三匹金绒蝴蝶缎,我想你过两年要及笄行大礼,准有些个正经时候,便先收起来。其他的六丝纱、八丝缎倒还平常,你喜欢哪个花样子?我让十二公主苑里的婉柔姑娘来给你挑,她见识好,眼光与旁人不同。”
天枢侧着头想了想,先问:“这缎子拿去卖钱,又值多少?”
攸伶吓了老大一跳,惊道:“这都是上用宫缎,也只有咱们宫里有,要不就是宫里赏下去的,谁敢拿去换银子?”
天枢坚持说:“不管那些,你先估一估,我自有主意。”
攸伶犹豫了两回,方道:“兴许是一匹二十两,三匹就是六十两,足够买两个我了。”说到这一笑,又补充道:“只怕我还说低了,我没见识,更何况有谁卖过这个?”她一面说,一面连连摇头,满眼皆是不以为然的神色,再笑道:“只怕一匹就抵得上我家整栋屋子,连家什都要算进去了。”
天枢又问:“那上回皇后娘娘多赏我的,又值几个银子了?”
攸伶瞪大眼道:“那些虽不及这些精巧显眼,可也都是苏素缎、苏花缎,是极素净的,公主也喜欢,你也舍得换它?还有的紫荆花绢子跟小花钱缎子,我都已经吩咐人裁了去,不成匹了,你也别再打那个的主意。”
天枢闻言,连连摇头,因道:“咱们苑里就属绿茵嘴快,也属你最是手快!”见攸伶扑哧一笑,既不慌也不辩,想来是文贤妃授意,便也不好再多说。因天枢实在乏倦,攸伶就服侍她歇觉,好不容易等她阖眼睡着了,等细心盖好丝绵绣被,再熄了内殿灯,方才退出殿去。又去下房里抓了绿茵来一一盘问过今日之说,听天枢问的皆是银钱之事,实属罕见,只是当下也不好多作细想,只当是哪个人在天枢跟前讲了宫外琐事,引得她起了兴致。攸伶将诸事都慢慢收拾妥当了,才靠在床上,想着明儿个该去问问清音,没准她能晓得些个头绪。这般想着,直到后半夜,才困到不行睡了过去。
第二日照例阴凉,日头也极好,挂在天上晕出一圈淡淡的白光,落在树梢丛中,洒下来的零星斑点亮白如银,天枢一路往太裳殿来时总是猛看地上。今日攸伶虽未跟来,但绿茵追随其后,见天枢发怔着朝下看,因问:“地上有什么好东西呢?还是公主丢了东西?告诉奴婢,奴婢给您找。”
天枢发呆道:“要都是银子就好了。”
绿茵一听,吓得再不敢多言,暗道:攸伶姐姐说得不错,公主果真是哪里得了魔障来?今儿更得要好生伺候,万事小心谨慎为好。
正想着,二人进书斋来,见褚凡候在那,正端了手中一方石砚看。天枢便问是何砚,褚凡笑道:“是才得的天砚,殿下赏的,也不知因着什么由头赏我。我说不敢受,他又说要亲自派人送我家去,我只得接下来,回去供着吧。”
天枢凑眼过去一看,见那砚石赤比玛瑙,莹润如玉,背面隐绕五色细丝,正面是夔纹细篆,便也道:“一看就是好的,倒是拿来磨一锭墨试试?”褚凡见说,忙取过松烟墨来,用银匙子量了水,墨胶慢慢化开,有墨味清香沉沉烟起。天枢又以笔试墨,那墨落在纸上,字迹光润饱满,着墨时静淡无声,只听得到窗外的秋风悉索作响。
褚凡笑道:“纸上瞧不出好坏,要取那夷墨来试过竹简,方才雅致。”
天枢不禁叹道:“就你考究。”又向一旁静立不言的绿茵道:“这里头怪闷的,你出去逛逛,别走远了就是。”绿茵的心思早飞往外边,因天气凉爽,更是不愿守在屋中,想去庭园里舒展筋骨,见天枢这样说,便欢笑着道过谢,脚不沾地的去了。褚凡见她故意使走跟来的人,心知她有话要问,便静等她先开口。
天枢也是直截了当,道:“昨儿我听了个大学问,说来给你听听,让你替我评断评断。”说着,就将绿茵的银钱米价之说复述一遍,乃问:“这会子银子究竟价值几何?粮价长得那样快,难道父皇不知?百官不知?你不知?还是说你们都是不管事的?”
褚凡遥望窗外的绿茵正逗着架子上的鹦哥玩,道:“那姑娘不过十来岁年纪,她娘说养她时米价翻了一倍,倒也情有可原。那会子正是北疆战乱频发,先皇在世的末年几乎连年灾荒,有米商哄抬米价,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天枢冷笑道:“那这几年又涨了一倍,算是什么事?”
褚凡拍案道:“那就更不奇了!这两年市面上平空多了多少白银,你可知道?”
天枢皱眉道:“多了银子?哪里来的银子?那银价不是得跌了?”
褚凡摩着手中墨砚,缓缓道:“朝中都说是西夷跟北蛮子撒了白银进来,但银矿向来是南诏多,又多与锡矿相连,西北边要稍少些。官府不准民间采银,可真要去采的又谁管你说的?照例开采不误。如今早已是贫矿多,富矿少,连朝廷都要省着用,也不知他们从哪里寻来的积银了。”
天枢不知怎样回答是好,只得再问铜钱如何。褚凡因答:“铜钱也是不让人省心的。先祖女皇定下一贯换一两的规矩,可近百年过去了,民间早不是这等用法。先皇在时,据说铜钱是不值钱的,一两银子倒能换个上千文;可到了当今手上,这会子一两银子倒只有几百文了。虽说皆是些小钱,未必及得上先前那个兑法。”
天枢忙问:“什么小钱?还有大钱、小钱了?”
褚凡笑道:“你不谙世事得也太过!”
天枢苦笑道:“我从没使过银子,更不用说铜钱了。赶明儿有机会,一定要去市集子上花掉几千几百文,将新鲜东西都一个个玩过来。”
褚凡又是摇头:“你如何能出去?就是领你去的人肯,贤娘娘也定是不肯的。”见天枢咬着唇不语,他也只笑道:“说是小钱、大钱的,也不过是民间说法。”说着,他从怀中摸出两枚模样差不离的铜钱来,排在桌上,指着其中一枚道:“这个要重些,应有一钱四分,百姓就称这是大钱。”又指着另一枚说:“这就只有它的一半,是七分重的,就是所谓小钱了。”
天枢大是新奇,忙将两枚铜钱都放在手中掂量,果然有一侧的要沉甸甸些,不觉问道:“官铸的铜钱还分大小?难不成是想学那吝啬鬼,一个铜钱掰成两个用了?”
褚凡笑骂道:“你又糊涂了?既知有官铸钱,那也定是有私铸钱了!这一吊大钱原是好换一两银子的,可要是掺了小钱进去,那就得打折扣;要整一吊全是小钱,就只值七钱银子,更何况市面上还有些前朝旧钱,闹得古今兼容,又禁它不得,便只得照单全收了。”
天枢想过片刻,方道:“看来也只有宫里是用无杂掺的清钱了?”
褚凡也冷笑道:“恐怕在你见不着的地方,照例是厚薄不一、鱼龙混杂的。你要不信,别只顾着问大宫女们,等得了空偷偷问两个小宫女,一查便知,准有毛钱!更何况……”他不觉顿上一顿,天枢忙问是何,他才犹疑道:“官铸也有偷工减料一说。铸钱的官员手脚不清,也是有的。”
天枢忙问:“那可有法子清肃整顿?”
褚凡忽又笑道:“要问我,我自然是有的。只是要看你爱不爱听,又要看太子殿下肯不肯采纳去了。古来纳谏逢着这银钱铸币之事,多芜杂繁乱,敢直言的官员个个不讨喜。只怕朝里除了我,也只有我恩师肯发这话了。”此言说得虽狂妄,但天枢极为爱听,便要与他再商量这事。
具体商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