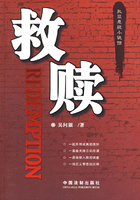闻良聘攸伶藏私心◇听闲言褚凡隐妒意
话说天枢酡红了脸,又故意作出那害羞不已的模样来,贤妃见她欲语还休,情态好不青涩,只得暂先放过她。说闲话时余人都识趣退出,只有那老尚仪从旁伺候,捧了一碗墨绿的汤药盯紧贤妃,直到她将那药汁都喝干净了,方才放下心来。
话说毕了,殿外有攸伶进来献滴露茶瓯,贤妃因笑道:“这孩子实心眼,到了我这里连个懒都不偷,哪用得着你来上茶了?”又命去叫殿中宫女来,喝道:“可见是我太娇宠你们!”
有宫女委屈不过,回了两句:“茶水上的如烟姐姐给太后娘娘宫里人叫去了。奴婢是做粗活的,不敢进来端茶侍水。”
贤妃惊道:“太后传她作什么?”
那宫女慌得连喊不知,贤妃惊疑不定,一时按捺不发,只先吩咐攸伶领天枢回苑去,再打发人到上恭殿外听动静。天枢侧身退出,攸伶笑意盈盈地跟了出来,随在背后说:“齐公子、褚御史,公主您说说,觉着哪个好?”
天枢回头戳了她一记额,骂道:“又给你不留神地听进去了?还来同我磨牙!”
攸伶笑得眼如月牙,一个激动,上来搂住天枢的胳膊。天枢鲜见她这样不庄重的举动,又见她扭着帕子连道:“奴婢错了,求公主饶了奴婢吧!”言笑晏晏,关切情态亦真,遂也同她挨紧了身子,趁着夜色窃窃说了几句私语。
绕过中庭水井,左厢的芳菲苑中灯火已熄。自洛阳公主出阁后,此处就只剩些守值宫人,日常打扫,夜暮闭门。那月照下的殿宇只有屋顶上是亮的,琉璃瓦片如水光粼粼,檐下俱是漆黑一团,不见人影,不闻人声,只听得几株落光了叶的枝桠在风中簌簌轻响。
天枢只得再叹一口气,携了攸伶向蘅芷苑中来。只见绿茵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她俩回了,顿时满脸堆下笑,抢先道:“皇后娘娘宫里送来了今年的贡缎、云锦,比往年多了三倍还不止,连花样也多了三成;昭阳殿里的英姐姐送来了好些橘子,奴婢说咱们苑里也有了,英姐姐又说‘八殿下都搁着不记得吃,还是送这来给十三公主慢慢用的好。’奴婢这才接了,好几只大匣子呢,大都储到地窖里去了,再挑了些黄澄熟透的,这会子都放在书房里的玉盘子上。”
她素来伶牙俐嘴,只是因着年幼贪玩,故而当差时总不尽力。今日这样一番话急急说来,转得天枢一阵头晕,扶了扶额,道:“我不吃那个,你们拿去分了吧。”她并非不爱橘,只因此时一见橘就颇伤情,因而早没了胃口。绿茵见她锁紧了眉头,只当是自己又说错了什么话,吓得惨白了脸,忙朝攸伶使眼色。
攸伶看她慌得像只小兔儿,也只得叹气,摸了摸她头:“你去睡吧,叫她们也去睡,横竖这里有我呢,不碍事。”说罢,入内殿来替天枢散了钗环,将头发梳成一条辫子,细细理好了,服侍她睡定稳妥,方再往下处房里来,一般捉住绿茵,笑骂道:“你个蹄子!平日里见你最是有眼色的,这会子倒糊涂起来了!”
绿影给唬了一大跳,忙问:“我不明白,姐姐赶紧教教我。”
攸伶坐在她床上,靠着她的铺盖,笑道:“今儿个你是给吓糊涂了!那昭阳殿的英姑娘也不知着了什么魔,竟是送橘子来。你就不知,‘橘’字正冲了三公主跟洛阳公主的名讳,咱们公主听了能高兴?”
绿茵恍然,赶紧扭上来捏着攸伶的手,逢迎道:“好姐姐,我就知道你最疼我!每回我出了事,也只有你肯来帮我。别人都是嘴上说得甜,平素亲亲热热、姐姐妹妹的,叫得好听,今儿个我给公主训了,一个个都不曾来替我赔上一句好话!”
攸伶心知天枢今日不是真恼她,乃劝道:“像我们这样,好在公主跟前露个面的人,好让正殿里嬷嬷照应的差事,底下哪个不眼馋?你心善,不去挤兑人,那旁人还要寻着法子来挤兑你呢!可你倒好,不仅不守着规矩,还总爱跑出去逛,跟之前越王殿中旧人混在一处。便是你没有那说嘴的心思,可这口里一不留神,给有心人听了去揣摩着,总也能猜出些咱们苑里的究竟来。”
绿茵红着眼,搂紧了她腰身,哭道:“好姐姐,我知道错了,今儿个公主罚也罚了,一整日都不肯多理会我一句。连往园子里去玩时,也没说带了我去,往日可是最爱领我逛园子的。你说,公主不会是再也不疼我了吧?”
攸伶拍了拍她双颊,骗道:“别胡说,哪会不疼你?公主要是不疼你,你犯了那样的事,她还不撵你到掖庭去?”
绿茵一听去掖庭,果然吓得再不敢说。攸伶笑着哄她入睡,心下怜她年幼,又实在是不谙世事,心想:这丫头说话冲归冲,可也就是心直了点,肚肠倒是不坏的。也就得她这样心直,当初才会跪到公主跟前,求着公主救下绿萼姑娘。念及绿萼,她又唏嘘了两声,再回过头去看绿茵,睡得还极不老实,两只臂膀子都露在被外,眼角尚含着泪珠子。
攸伶只好苦笑,帮她把被子盖好,又坐在她床头发了会呆:绿萼姑娘虽没了,可肚里那孩子到底是谁的?三公主说,不是贤王殿下就是七殿下,可冷眼瞧着,又总觉着不太像。如今死无对证,实在是可悲可叹。
她想了会,等绿茵睡熟不动了,才回自己屋子里去。卧在衾里,一面忖着适才文贤妃所言,既惦记齐祈公子飘逸若仙的气度,又赞叹褚凡御史锦心绣口的才华,少不得也要替天枢白担那一分心思。她想到半夜尚不得安宁,翻覆了好几遍,还是不曾入睡,只好坐起身来,裹着毯子在窗下靠着,窗外月色涟涟,淌在那一格一格的青砖上,拼连出千条万线的双丝网。
月光落在紫烟罗上,好似撒了一层银粉,帐上的弹墨竹叶纹也一星一星闪烁。天枢坐在书案前理画,适才待攸伶一走,她就起来将素日收藏的轴卷一一展开,仔细重阅过,题跋、赋诗等处看得尤为细致。览过无异常的,就连同锦匣一起归置在案上,案边还搁了一盘木樨糕,一块未动。
她怕朝中贪墨成风、吏治腐败,献进来的卷册中有过于名贵之物。往日只是随搁随放,这几日听多了政事,方觉一器一件皆大意不得,倘或真有,莫若当先呈入图画阁中去。所幸检视过后,大抵是些当朝俊才绘的山川花鸟,其中虽有些也价值不菲,但尚在情理之中。
天枢且将旁的画都随手搁着,只痴看了半晌那幅芰荷图,画上碧清溪澹澹,粉芙蓉亭亭,荷尖上的那只玉蜻蜓几欲破画而出。她蹙着眉,胸口疼得锥心,心口一抽一抽的,似是在提醒天帝曾赐她肉身仙骨玉肌、诸事心透眼明……独那一件不如意的,便是心肺生来俱损,不可习武修道,纵有那使力的心,也无那遂心的力,好命不得长久……
这般神魂逗萦到天亮,第二日精神还尚好,是以晨省过后,遂还往太裳殿中上学。入了书斋竟不见褚凡,问过宫人才知他在病榻前议事,天枢只得再往松露院中来。可巧翠小姐也在,正在廊下教授小宫女园艺与花道,又说要采了菊蕊来制作香丸。天枢坐在石凳上,听她说得眉飞色舞,语笑嫣然如春日里盛开的碧桃花,忽的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那些宫女见她来了,也只再围坐过一阵后散去,翠小姐便坐到她身侧,微笑道:“你先生在里头说话呢。什么‘朝政繁忙、战事稍定、见驾出京’的,我也听不明白,所以出来透透气,再寻姑娘们一起玩儿。”
天枢听她如是说,便道:“朝中事我也听不大懂,也就不进去凑热闹了。”又问:“一直没问过翠小姐芳名,今儿个可得要告诉我了?”
翠小姐面上一红,犹豫道:“是真俗气,倒不是自谦……叫翠微,小名唤作翠君。”
天枢不由夸赞道:“哪里俗气了?雅致得很呢!”想一想,又道:“已有个君姐姐了,我还是称一声翠姐姐吧。”
翠君也点头,再问过天枢名讳,二人从此姐妹相称。天枢因问她长于何技,翠君起先只笑不言,待天枢闹得她痒痒了,才笑喘道:“世人说我擅岐黄,实是名过其实。我素日所学的,也不过是晓得些个‘哪样花儿何时开,哪样树儿几时种,哪样根儿可入药’罢了。”又问天枢学里念的是哪一科。
天枢只说:“我没翠姐姐那样的天分,只好请褚先生随便教些四书,明白些事理。”心下暗道:我长于何艺?我若说我熟晓星象筹算、运势命卦,岂不得吓着她?
她俩言笑正欢,一时妙樱也来了。外头落了雨,随行的人都有打伞,唯独她穿了身松蓬蓬的草绿蓑衣,头上又顶着莲青箬笠,手里还提一盏透亮的玻璃球灯,一踏上廊阶,就忙不迭地摘了顶戴甩着微润发丝。天枢抬眼一看,竟是钗环全无,不禁指了她冲翠君道:“这宫里独有她爱在衣衫子上下功夫,描出纹样的,吩咐宫女们针绣的,都是别样精致。”
翠君尚未答,妙樱先嗔道:“可不,过会子你还得跟翠姑娘揭发我,咱宫里姐妹独我最爱擦那蜜儿粉儿的。等回头你们的胭脂膏子用完了,可别再来求我,都去用内侍局里配的吧!”
天枢才不怕她:“那我求翠姐姐去。”
妙樱讶异道:“我说今儿个怎的底气足,原来是寻着能人了?”又向翠君笑道:“让翠姑娘见笑了,阿枢其实不爱花儿粉儿的,方才是跟我拌嘴玩儿呢。”
翠君忙道:“十二公主慧心别具,终是我不及。”
正说着,太子送褚凡出殿来,尚殷殷关照几句,天枢三人忙也站起身来,未及行礼,忽又听背后有人进来。褚凡稍稍觑得一眼,竟是冯良娣,顿觉周身不自在,那太子也不招呼理会她,反倒是妙樱迎了上去。天枢冷眼望着她,见她也尴尬不安,不免又要冷笑一声。
殿外宫眷云集,褚凡连称告退,妙樱却道:“阿枢的先生难得一见,不如再陪着坐坐,我们也好沾了阿枢的光,听听学问。”话语中竟是将他当作尊者长辈一般敬重,让褚凡听了很是局促不定,天枢更是要啼笑皆非。
于是众人复回殿中坐定,冯良娣见翠君在嘱托太子用药事宜,二人言辞有味、谈笑默契,褚凡却陪着天枢等人立在另一侧讲经,不免觉着坐如针毡。这正是那:左也不忍听,右亦不愿闻,左右皆欢笑,独她清寂寂。
这边妙樱正领过翠君来向褚凡介绍:“她是救了二哥哥一命的翠姑娘。”褚凡早有耳闻,忙对着她作一长揖,臊得翠君直往太子身后躲。
太子一面笑,一面道:“御史多礼虽好,吓着我的恩人,可就不好了。”
褚凡却道:“不光要谢柯小姐,还得谢引了小姐来的越王殿下。”听得天枢顿一皱眉,忙推了他一搡,他却装作不知。
进来撤药碗的清音又嘴快:“那还得谢请得动柯小姐的齐二公子呢!”
天枢闻言,心头冷笑不止:那俩旧主仆倒实在情深,多琐碎的话都说一处去了,想来这姑娘还能有什么是不知道的?思及此,侧目清音,谁料翠君也饶有兴味,两眼盯住了她。清音这才觉察不妥,回望太子一眼,青白着脸退了下去。
太子释然道:“我跟齐公子虽有过嫌隙,可也不过是口舌之争,你们但说无妨。”
翠君含笑道:“公子是放荡不羁之人,且爱臧否人物,见了我等俗人,多以白眼对之。那会子也不爱搭理我,后来有一回,我送了他两瓶芙蓉清露,他才算给点子好脸色。可见此君可恨!”她虽言“恨”,但话语俏皮,又是笑着说来,诸人皆让她引得一笑。她遂又比着手,摇指太子道:“连我也猜得出他俩能起什么口角,左右不过是一个求贤若渴,一个誓死不从罢了!”
这话说得众人又一哄堂,翠君乃判曰:“仙骨铮铮,不类凡俗。这等人物,闲云如陶令,野鹤似嵇公,可访,可遇,却偏不可求也。”
众皆称是,天枢也服了:“我表哥那狂狷的性子,我道是他能结交哪个呢?原来他是推崇姐姐,对姐姐青眼有加的?可见座下诸人唯姐姐是真名士,我们都是俗人,不入他眼的。”
妙樱笑得捧脸直喊“嗳唷”,太子也掌不住,笑道:“不怕不怕,你必是能入他眼的。昨儿个八弟还同我说,算来算去,也只有把你嫁去他们家才妥当了。”
天枢不想他说得这样直白,登时咬着唇再不多话。翠君回头见褚凡忡然变色,不免猜出九分来,忙岔开了话去。太子虽知造次,却兀自不察这厢小儿女心情,仍对清虚之才赞不绝口。
褚凡起身说要回避,冯良娣闷坐了三刻,亦起身说要走,急得天枢喊道:“我送御史出去!冯姐姐再同太子哥哥说两句吧。”她情急褚凡,这会子倒又不介意冯良娣跟太子接近了,也早将怀珠之事抛于脑后。
是故俩人出殿来,雨势依旧绵绵,滴在石砖上印得鞋袜寒凉,天枢见褚凡神色不愉,只当他又惦念冯良娣,又气又恨又不忍心说他,便随口说些“我看太子哥哥挺喜欢翠姐姐的,究竟是一命之缘,也算是聊慰苦闷了。”之类的闲话。一抬眼,见褚凡照旧不乐,不禁要恼:“这会子我拦着你,不让你私会心上人,你可是怨我了?”
褚凡未料她有这番念头,当即一怔,才道:“岂敢。”静了片刻,又道:“公主在学中从不叫我御史。”
天枢没好气:“我也不唤你先生的。今儿个我樱姐姐给你脸面,连累我也叫了你好几声先生呢。你可是得意了?”
褚凡也冷笑道:“若为帝师,倒还罢了,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天枢给噎住了,怒目他两眼,他却再次冷言:“是小臣失敬了。公主有八王贤兄、齐氏姻亲,又岂是我能高攀的?”
天枢听得一愣,只当这几日妙玫代为理政,怕是严待了他,惹他恼了,方才有此狠话,故劝道:“你也不好这样说我八哥哥,他这会子帮着父皇跟二哥哥办事,对哪边的人都是软不得、硬不得。他若得罪了你,待你偏颇了,我替他赔个不是。”
褚凡见她全不解风情,更气道:“臣岂敢拿八殿下的错?就是齐府的公子,也不是我好说来挑刺的!”
天枢又是一傻:“他是我亲姨娘家的表兄,小时亲厚,那会子八哥哥就拿我俩调侃。这两年大了些,倒也不太相见,他也不好来我苑里寻我玩儿,只昨儿个在昭阳殿里碰着一面,竟又给八哥哥拿去嗤笑了。”
褚凡一听他二人昨日方见,更嫉恨道:“可见并非空穴来风?恕臣不才,忝为乃师,故而提醒这一句:清者自有修身法,望公主珍惜芳名、注重清白!”
天枢闻说,哪还能再忍耐下去?也愈发刻薄起来:“我哪里不清白了?先生不用多虑,女学生我必不辱没先生清誉,只求先生好自为之吧!”
此话复又指冯良娣,倒让褚凡恼羞成怒了,乃道:“许你有两小无猜,就不准我有青梅竹马了?公主不用介怀,小臣从未与她有过婚娶之约!”
他这一番话说得又快又急,听在天枢耳里又极是没情没理。因天枢不知他怒在何处,恼在何地,便只觉此人实属无理取闹,着实言语可憎,哪里是当初她那个清隽优雅、才华出众的天权四弟了?只怕已是遭了凡尘,蒙了凡心,且这一切一切,皆因那朱姬而起,还牵连了一众仙友。如此想来,天枢更觉冯良娣是那罪魁祸首,心中对她的忿恼遂更进了一层,举头复看天幕上飘洒而下的淅沥雨丝,落在檐头籁籁有声,那滴滴答答的轻响好似永无止尽一般。
正是:点水蜻蜓,难觅梦魂。双丝网缠千千结,桃花开尽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