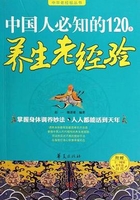回到钱塘,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找鲍仁。
我领着善檀,左拐右拐来到鲍仁所在的书院。书院并不大,处在一个很是偏僻的地方,进门便听得到朗朗的读书声。院中的杂役正在扫地,他低着头,我的脚步声又被读书声遮掩了下去,因此并没有看到我进门。
我便走上去对他说:“打扰了,我想找一下鲍仁公子。不知他在不在?”
杂役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正要说话,却突然张大了嘴怔住,呆呆的看着我,半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苏小小之容的影响力,我早已深谙其中。初时只是似莲花初绽的清丽,经了岁月的沉淀,现在已是不精雕琢的惊艳。这情形我便早已见怪不怪,可善檀却瞪了眼睛,狠狠剜他一眼,道:“我家小姐问你话呢!”
那人仿佛这才惊醒,看着我不知所措。我轻斥了善檀一句,复又转回向他,尽量和缓了声音,重复道:“我想找一下鲍仁公子。不知他在不在?”
小杂役这才真正的回过神来,一叠声的结结巴巴的说:“在,在……鲍先生在,他在教书,我帮你叫他出来。”说完就往书房跑去。
我忙叫住他,道:“不要打扰他,我在外面等一等罢。”说完对他笑笑,说,“你有事就去忙,我随便找个地方坐着等等就好。”
小杂役依依不舍唯唯诺诺的走开,我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站着等了一会儿,便觉得腿脚有些酸,胸口也开始发闷。近来身子越来越不好,只是站站,过了十几分钟就会开始不舒服。若是立刻休息还好,但若是强求自己多站片刻,立即就是排山倒海的痛苦病症。
善檀看到我脸色不大好,忙说:“小姐,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鲍公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教完呢,再站下去,你的身子就……”
我伸手抚了抚额头,执起纨扇挡了太阳,向一旁走去。
书院里人很少,也找不到个人能问一问哪里是待客的地方。可脚下的酸软却让我不能再多等,便随便挑了间可以自窗口看到鲍仁教书地方的屋子,在地上寻个地方坐了。
善檀立刻尽职尽责的跑出去给我找水喝。
我在屋子里坐了好一会儿,胸口间的疼痛才缓和了一些。正低着头暗自调整呼吸,忽然眼前一黑,一个人影罩下。我抬头望去,那人背光站着,一个剪影修长精瘦。头发全白,蓄着胡须,全然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
我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眼熟。皱着眉在记忆里思索了半天,突然一个灵光乍现——这不就是!那个谁谁谁么!
立即脱口而出的惊呼道:“张真人?!”
居然是一年多以前我陪贾姨去灵隐寺礼佛的时候遇到的张真人!
此时我已不再是当年那般,日夜闷在家里和西湖风景里的小姑娘,常日游走于形形色色的人中,自然听说了很多事情。张真人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这一年来,我偶尔去灵隐寺里,都只见慧明和尚,没有见过他。若是对和尚问起来,他都只说一句“道长云游四方,此时人在哪里,贫僧也不知晓”。
一个道行极高、云游四方、世人皆以见其为荣的半仙。他怎么会在这里?!
张真人和缓的对我笑了笑,手中的拂尘随着他的动作抖了抖。我这才缓过神来,忙站起来让位给他,对他道:“真人快坐。”
他却只是站着,依旧笑着道:“施主身子不好,还是坐下罢。”
我笑了笑:“真人怎么知道我身子不好?”
张真人还是坚持让我先坐下。我推辞不过,只好先坐了。他却依旧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道:“慧明前几日圆寂了,施主怕是还不知晓罢?”
我被吓了一跳。自入冬以来,我因怕冷便没怎么出过门。接着就是给萧长懋治病、我也去了建康,一呆就是一个多月。算起来,真是已有三个季度没有去过灵隐寺了。可是上次见面的时候,明明还身体硬朗的慧明,怎么会突然圆寂了?!
张真人拿拂尘略拂了一下我身边的地面,直接席地而坐下来。对我说:“贫道此次前来,便是为了这件事。多年好友,他却先一步走了,终归要来见一见。”
我恍恍惚惚了一阵,才问:“慧明大师可已经……已经……”
“已经”什么,我说不出口。张真人却了然于心的对我道:“舍利已供奉于灵隐寺塔中。”
没有说出那个词,可意思已然明了。我心里叹了一口气,张真人还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却连遗容都见不到了。想着慧明平时那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以前虽然恨的牙痒,可现在想起来,只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慧明和张真人是唯一知道我来历的人,其中一个就这么去了,心里真是空落落。
一时间两人都无话。张真人闭目了半晌,我低着头想事情。突然听他在一旁悠悠的来了一句:“施主在建康御前献舞的事,贫道也有些许耳闻。”
我知道他肯定还有话说,便立即正襟危坐收敛了思绪洗耳恭听。可他却缄口不言,我等了半晌,也不见他再说话。便只能说:“我所做之事,在旁人看来必然无法理解。可世上想阻我路之人何止如此?我愁过苦过,气过喜过,可如今看开了便也觉得没什么。我所为种种,但求一句‘无愧于心’罢了。”
张真人淡淡点头,道:“贫道初次见到施主之时,实则已听慧明讲起过施主的来历。彼时相见,只觉施主将一切看得淡然,并不放在心上,也将自己所历所受当做身外之物。可此次再来,慧明与贫道说,施主早已取走当日求的那枚签。贫道便已知晓,施主已将此间之事当做了自己之事,不再是置之度外的态度了。”
我怔了怔。
张真人眸光深深的看我,道:“施主也许并不自觉,或许心中尚且想着,不过是在这里走了一遭,待时辰到了,自当返回原路。可是扪心自问却会发觉,实则这里的人和事,早已是融汝之血,渗汝之骨,割舍不得。为何会有喜有忧,有痛有怒?唯有真正在乎,方才明白其中滋味。”
我心头一震,整个人瞬间愣住。
融汝之血,渗汝之骨,割舍不得。
短短十二个字,却诠释得如此透彻!我真的将苏小小当做是自己了吗?不,我一直知道我不是她,她也不是我!我是苏小乔,我只是因为时光机的错误来到这里……可是……
可是慧明却对我说,我是天女,来到此间完成使命。如果我是来完成使命的,那我就不是因为错误才来到这里。这个说法我早已接受,可是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我却又想要推翻它。
我苍白着脸颊,一字一顿的对张真人说:“不……我不是苏小小,我不是她……我不是!”声音出来却又发觉,原来自己的喉咙已经开始发颤。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真正接受这里的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将苏小小当做自己的去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我是她,她是我,我们彼此渗透,彼此互为一体的生活。
我冲口而出:“不……!”
张真人淡淡看了我一眼。
“可苏小小……”我发觉自己的声音还是在颤抖,便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尽量平稳下心绪,缓缓道,“这根本不能解释。若我是苏小小,那真正的苏小小呢?她去了哪里?难道她能够去我的地方,取代我?!”
张真人静了片刻,方才开口道:“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脸又白了几分,问他:“你什么意思?”
“贫道的意思是,”张真人转目凝视着我,道,“你在之后的时间出生,却回到了之前的时间——这是命运。你以为自己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抑或说……你知道在苏小小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你守着不能改变之前时间的事情的原则,因而逼迫自己去做苏小小该做的事情。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苏小小,苏小小就是你。”
你就是苏小小,苏小小就是你?
“贫道既可以看出你并不属于这里,那便与你透露几句天机——苏小小的命格,在九岁时已是终结。彼时她香消玉殒,灵魂消散,属于她的时间本该结束,可你接替了她剩下的时间。你以为自己在做苏小小未完成的事情,其实不然。你现在在做的,只是你自己的事。”
我惊的完全说不出话来。
张真人又恢复了淡然的模样,眼神也变得清淡,对我说:“施主乃是聪明人,无需贫道多言,自当清楚其中缘由曲折。”
我是该清楚。可是……让我如何清楚?
兜兜转转转转兜兜,苏小小就是我?
我正低头想着事情,忽的又是一个人影欺近。我条件反射的抬头,却见鲍仁一身书生的装扮,站在门口低头看我。脸上的神情满是喜悦,松了一口气说:“苏小姐!我还当仆役在跟我说笑,没想到真的是你!”
我被张真人的一番话说的脚下虚软,想站起来却有些使不上力,刚撑起一些就又跌坐了回去。鲍仁见了,扶着门框脸色大变,道:“难道外间传闻说你身体欠佳患了重病……竟是真的?!”
外间已有了如此的传闻?倒是我不知晓的。
便抬抬手唤他走近些,鲍仁皱眉看了我半晌,方才抬步向我走来。我正想着该如何跟他介绍张真人,忽的张真人眼中一闪犀利,眼光如电的射向鲍仁。我皱了皱眉,鲍仁愣了愣。张真人却捋着胡须点了点头,转回向我,笑着道:“施主现下应当明白贫道所言何意了。”
鲍仁更不明就里,我却明白了他的话。想来他真是半仙,看一看鲍仁就知道他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便恍然对着张真人道:“是。”
张真人拂尘一甩,人已利落起身,道:“施主应当知晓自己的路已所剩不长,就此一别,想来不会再见。请施主好自为之。”说完已缓缓抬步向外走去。
我的生死,在他说来不过只是这么轻飘飘的一句“所剩不长”,不得不让人叹息。我抬头示意鲍仁扶我站起来,努力稳住了脚下,对着张真人的背影郑重的一拜,提高了声音道:“钱塘苏小小……拜谢真人出言点拨。今日一别,万望真人珍重己身!”
我低头行礼,再抬头时,张真人已不见了身影。
鲍仁扶我坐下,道:“他是谁啊?”
我喘息几口,抚了抚额头。方才一站一坐,又俯身下拜,此时眼前便有些黑。缓了缓才道:“游离四方的道长,说是有通天的本领。我只知世人都称他一句‘张真人’,也不晓得他到底道号是什么。”
鲍仁“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也算是熟谙历史的人,来这里之前也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张真人的名号。师父是现代人,虽长于历史,但也不可能每一个名人都知道。更何况他常年呆在这书院里,自然比不上我消息灵敏。
我问鲍仁:“贾姨说你登门三次要求见我,却并不领她给的银钱。可是出了什么事?”
鲍仁却堵住我的话头,反问我说:“你先跟我说,你的身子到底是怎么了?”
因了鲍仁是我的师父,即使是年轻时的他,我对他也自然包含了一层敬重。他对我亦是,自烟霞岩奏琴之后,便认定我“才华若此”,自是带了尊敬和珍视。两人出发点不同,可态度相仿,在相熟的朋友间已传成了一段佳话。
便笑道:“也没什么。我自小就身子骨不好,莫北说是肺里发出来的病,在建康时不慎落水,激发了病症,近些日子就有些虚。你不要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调养一阵也就好了。”
我想师父是知道苏小小的事迹的,听到“肺里”两个字,他的脸色明显变了一变。
他是知道我避不过一条思路的,就像我也知道自己终究要死一样。我所能做的,无非只能是静心等死罢了。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看着我等死而已。
我维持着脸上的笑,无懈可击的一副面具,对他说:“怎么了?真的不用担心我。我最近吃着莫北给的药,身子已经好了很多。”
鲍仁欲言又止的看着我,眼里满含了痛惜。我何尝不明白他这份痛惜是从何而来?可是我却什么都不能说,只能问他:“你到苏府去找我,究竟是怎么了呢?”
鲍仁又看了我两眼,方才收回视线低了头,默了一会儿,再抬头时也已换上了笑容,道:“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就是两件小事。想着该跟你说一说,就去找你了。没想到你一直在建康没有回来。”
我笑着静待他的下言。
鲍仁道:“自你上次烟霞岩奏琴,你我相识后,我便一直用功读书,一年来已有小成。想着你曾经对我说过的那句,‘应先有为民做主的心,再取用武之地,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我想参加今年秋末的科举。”
这句话说的如此郑重,我却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鲍仁莫名其妙的看着我。
我忙收敛了笑意。“科举”这个名字,是从隋朝开始才取的。师父这个笨蛋,居然犯了这种错误。可是我看他一张纯真的脸,竟是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的。便没有出言纠正,只是说:“如此很好。真是恭喜!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鲍仁知道我的性格,明白我的笑声并不是在嘲笑他,便也没有过多在意,爽朗笑道:“是!还需多谢你一直相助。不然我鲍仁哪有今天?”
两个人就这件事情讨论了许久,方才告一段落。我坐的双腿有些发麻,便想起身走一走。恰巧善檀端了水进来,嘟囔说:“找了水又找厨房,半天才找到!”
鲍仁一拍脑门,道:“我竟是忘了给苏小姐倒水了!”
我忙止了他,看了看天色,居然已经不早,便道:“不必麻烦了,我身上有些乏,回去歇一歇。你好好读书用功,我改日再来看你。”说完让善檀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拿出来递给他。鲍仁自然是百般推辞,我却硬是塞到了他怀里,说:“你拿着!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参加考试,路上的行头总要置备一些。你记得我的话么?改日你金榜题名了,不要忘记钱塘尚有知己一人。”
鲍仁立刻摇头:“我怎么会忘!”
我便笑了,说:“既然如此,还推什么?快拿着!以后还我也不迟。”说完塞到他手里,跟着善檀往外走。
走到门口,善檀扶着我上了马车。我掀开窗帘,看到鲍仁站在书院门口呆呆的望着我。便笑道:“快些进去吧。”
鲍仁点了点头,我放下窗帘吩咐车夫回去。可马车刚刚动了一下,我却突然叫道:“停!”
车夫忙用力拉了缰绳,两匹骏马嘶鸣了一声停了下来,我掀开车帘让善檀扶我下去,鲍仁也已经跑了过来,说:“怎么了?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我笑着摇摇头,道:“你不是说有两件事要告诉我的么?要去赶考是一件事,那另一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