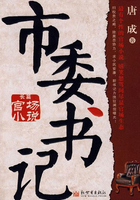莫北亲自送我到渡口。
墨阳先走上船,然后转身伸出手准备扶我。我伸出右手搭在她的掌心,左手提了裙摆,正要迈步,忽然耳边传来一个细微且低沉的声音,说:“索酒这件事,你不要再插手了。”
我一愣,回过头去,却见莫北站在离我四五步开外的地方负手立着,一双眸子深深,视线胶着在我身上。见到我望他,他似乎对我微微的点了一下头。
我不禁伸手摸了摸耳朵,这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功夫来着?什么音什么密?
墨阳见我一直不动,有些疑惑的叫了我一声:“苏小姐。”
我回过神来,再看了一眼莫北。只见他依旧那副样子站着,仿若什么都发生一样。若不是我万分确定刚才的声音定是莫北,也许此刻我也该怀疑自己是幻听了。
可是,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让我再插手索酒的事?
有一句话,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抵说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情况。
南木和阮郁相对坐在苏府大堂的东西两边,一个摆弄着棋子,一个饮着热茶。看似平静和谐,可是偶尔对视一眼的眼神,却蓄着火焰般,一触即发。
善檀在苏府大门边等我,脸上的表情看着都快哭出来了。见到我,就一溜小跑的过来,连行礼都顾不得,哑着嗓子说:“小姐,您可算是回来了!”
我一声“别急”还没说出口,善檀已在旁掉了眼泪:“南公子和阮公子打起来了……奴婢没拦住,奴婢该死,请小姐治罪!”说完就“咣”的一下跪在地上磕头了。
我那声“别急”立刻被我咽回了肚里。
打打打……打起来了?!
我立即就急了。一把将善檀拉起来,没顾上“治罪”就往里面冲。一进大堂就见到他们两个人那副样子的坐在那里。倒不像是刚刚打过架的样子,不禁就“呃”了一声。
南木先看到我,放下茶盏站起来,一脸无害的笑容,看着我说:“小小,瞧你,这么急干什么?头发都乱了。”
我的嘴一下子长大了。这算什么?咱俩和好到这个份上了吗?便一个白眼抛过去,语气不善的道:“这是我们南齐流行的发式,你当然不懂了。”
阮郁已走至我身边,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呵呵”的一笑,对我说:“小小。你这床真舒服,我很久没睡的这么安稳了。”
我斜眼看了看阮郁,这句话虽然挑不出来什么毛病问题,可是听在耳朵里,却是怎么听怎么觉得暧昧。我和他向来没这样讲过话的,虽不知是什么原因,可到底觉得外面已流言满天,我实在不愿再描黑什么,便笑道:“怎么?我这里的孤枕却比你家里的温柔乡舒服?这算是怎么个道理?”
阮郁碰了这么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便不多说,呵呵笑一下算是揭过。
我捧了一盏茶走到里面坐了,歇了歇,问道:“我听善檀说,嗯……你们两个,好像有点什么事?怎么了?”
南木阴郁的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阮郁倒是依旧笑得让人如沐春风,道:“只是与南公子发生了些误会,无甚大碍。”
我听他这么说,想是应该不至于打的有多厉害。更何况,看两人也都没有什么伤,走动之间也都挺轻便的,也就放了点心。想着等一下再问善檀。
阮郁开口问道:“你方才去哪里了?”
我缓缓饮了口茶。我带着墨阳一起去的莫北家,就算我不说,墨阳也肯定会说。我自问自己和索酒的关系并没有阮郁和索酒那般的亲近。
便淡淡道:“我去找莫北了。”
阮郁的手一颤,手中的一颗棋子“啪”的一声应声而落,摔碎在了地上。我的心顿时剧烈的一抽,抽的我差点晕过去。那可是夜残音给我的棋!
阮郁说:“你去找他干什么?”
我伸手抚了抚胸口,端起茶杯猛灌了几口茶,有气无力的说:“找他还能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索酒的事么。”
“索酒的事我已经寻到解决的途径,你不要再去找他了。”
我抬了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阮郁怔了一下,把手里的棋子放下,连忙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小小!”
我吹了一下水中的茶叶,淡淡道:“你怪得着我么?”
阮郁脸上的笑容褪了褪。
我把茶盏放下,想了想,说:“我去之前,你告诉我说你辟了门路,只是‘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等我回来,就变成了‘寻到了解决途径’。阮郁,你和索酒不想让我涉险的心情,我可以懂。但是你要知道,我想救出索酒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
阮郁愣了一瞬,旋即点了点头,道了声:“我懂。”
我没有说话。过了半晌,阮郁忽然皱着眉头,举起一枚棋子,问我说:“这副棋是谁给你的?”
我升调的“啊”了一声。
阮郁继续道:“我送给你的那副棋已是极品,这一副却比我送给你的更高一个级别,已不是‘千金难求’的材质了。你向来不在意这些珍玩,定然不会是你自己打造的。刚才我摔你一个棋子,你的脸色都白了。”
我先是佩服了一下他的宝石鉴赏水平。这个时代,没有现代那些仪器的辅助,他却能认的如此准,果然不愧是自小见惯了珍品的宰相公子。可到了最后,却有些头痛。这副棋果然太招摇了。
阮郁顿了顿,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这该不会是莫北送你的吧?”
我眯了眯眼睛,淡淡说:“不是。”
阮郁停了停,见我没有继续说下去,便也不再问。再坐了一阵,南木对我道:“小小,你……上次那件事,身子好了么?”
我点点头,道:“好了。”
南木勉强笑道:“我上次有急事,一直没过来看你。中间也回去了一次……师父那边。一切都很好,你不必担心。”话语间,特别强调了“师父那边”这几个字。
我自然懂得他的意思,但却提不起什么兴趣,只说了句:“我没担心。”便不再多话。
三个人对坐着,多多少少有了些尴尬。谁都不开口说话,屋里一时间安静的有些让我不舒服。忽然善檀奔进来,急急对我道:“小姐,白公子来了。”
我愣了愣,没反应过来“白公子”是谁。
旁边阮郁已经“唰”的一下站起来,对善檀说:“人呢?”话音刚落,已经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小跑进来,就地单膝跪下,低声道:“公子,苏小姐。”
阮郁伸手虚扶了一下,语气急促道:“起来回话。”
那人闻言站起身来,一抬头,同阮郁说话。我这才看清楚,原来是这么个“白公子”——阮郁的贴身近侍白羽。
白羽说:“公子吩咐属下办的事情已办妥,那位也马上就到。狱里上下俱已打点好,请公子过去那边一趟。”
阮郁闻言立即笑开,脸上的阴郁总算是一扫而光,带着白羽就向外走去。刚走了两步,又顿住,转回头来看向我,张了张口,却没说话。
我看了一眼他的神情,电光火石间思量了一遍,心中思绪万千,脸上却努力保持神情不变,对他笑道:“快去吧。”
阮郁像是舒了一口气般,对我点点头,道了句:“你不要担心,在家等我消息。”
我笑笑,摇了摇头:“我去红袖招等你们罢。你快过去,别耽误了。”
阮郁想了想,点头道:“好。”便带着白羽和另一个随侍出了门。
阮郁一出门,我便坐回椅子中反复理这整件事的头绪。从莫北到索酒,从索酒到阮郁,从阮郁到所谓的“那位”。想了约半盏茶的时间,我抬了抬眼,缓声吩咐道:“备车。”
有小厮闻声出去。我又坐了一阵,方才站起身来向外走。
一站起来,忽然发觉——南木还坐在屋里,正看着我。
我“啊”了一声,问他:“你怎么还没走?”再愣了愣,说,“你没事就早点走吧,再晚些,恐怕天就黑了。”
南木的眸子沉了沉,对我说:“你没什么话要对我说么?”
我被他问的诧异,皱眉反问他道:“我有什么好说的?”
南木也皱眉,看了我半天。我也皱着眉看了他半天。两人对视许久,我心里本就有些急,此刻有点不耐,对他道:“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南木显然愣了一下,半晌对我摇摇头,站起身来,低低对我说了一句:“南某告辞。”便先我一步走了出去。
我也有些愣,可终究时间不允许我做太多停留,带了善檀,便向红袖招而去。
已是桑榆。红袖招内的人渐渐忙碌开来。我和善檀一路进去,并未受到太多阻拦。一直向索酒的小楼走去,刚至她的小院门口,一个身着红褐色衣服的男人伸手拦住我的去路,一言不发的看着我。
我愣了一愣。这人看着眼生,也并不是红袖招仆役的打扮。可他一言不发,倒是让我有些诧异。
我这厢正在想该如何应对,那人却已开口。对我道:“九姑娘今日已有客在,不再见客了。这位小姐,还请回吧。”
我皱皱眉,对他道:“索酒刚刚回来,如何就有客了?你去通报一声,就说苏小小在此。让她无论如何见我一面。”
那人先是一怔,旋即上下打量我一下。我被他探究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舒服,正待开口,只见他弯身对我恭敬行了一礼,低声道:“属下未曾见过苏小姐,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说完,向后退了一步给我让开路,“九姑娘吩咐,若是苏小姐来,直管放行。苏小姐请。”
我道了声谢,向内走去。整个院子平日一直是仆役来往十分热闹,今日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再走几步便到了索酒的小楼门前。
门未关严,我一路行去,便见到里面人影晃动。索酒端坐在正位,正端着一杯酒饮着。下首两个男人,其中年轻的一个扶着老些的那一个在索酒面前立定,然后便退到了里间。那人仿若身体很不好,低着头佝偻着身子,偶尔一阵剧烈的咳嗽,却一直恭恭敬敬的对索酒说着什么话。
索酒不置可否的饮着酒,转眼已喝下三四杯,却一直一言未发。
我思索着,已见到索酒平安无事,是否在外等等,不要打扰了的好。可这念头还没转完,便见到那男人突然对索酒跪了下去,一丝不苟的叩了一个头。
我微微皱了皱眉,直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索酒又饮了一杯,那人又说了一句什么,索酒突然面色剧变,豁然站起,拂袖而走,走上了楼。
我微诧的皱了皱眉,只见先前那个年轻些的男子快步而出,欲将那男子扶起。后者却执意不起,佝偻着跪在地上,竟突然捂着脸,肩膀抖动,居然痛哭出声。
我看着他那般样子,一瞬间也有了些怜悯。正想着,只见他抬头向旁望了一下。我一瞬间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全身顿时虎躯一震。
那人……竟然是南齐的当今皇帝——萧长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