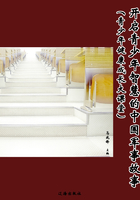人的机遇就是如此重要,如果林语堂不遇到赛珍珠,有可能他的后半生就要重写。赛珍珠(Pearl S.Buck 或Pearl Buck)(1892-1973),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是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四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先后在清江浦、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十八年。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值得一提的是,从幼年起,她就在鼓励声中开始写作。
十七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来到中国。1917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婚后随丈夫迁居安徽北部的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日后闻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1921年秋,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至南京。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自1921年至1935年,她与布克(J.L.Buck)长期居住在所执教的金陵大学分配给他们的两层楼房里。在这里她写出了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等作品,并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1934年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华尔希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庄里从事写作。
赛珍珠精通汉语,对中国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年)。赛珍珠翻译《水浒传》还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当时南京出售着《水浒传》的好几个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长达一百二十回。赛珍珠选择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因为较长的版本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则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
林语堂抓住了赛珍珠给他的机遇,其结果改变了他的一生。赛珍珠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大3岁。赛珍珠的父母和林语堂的父亲同为传教士,不同的只是赛氏父母是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人,而林语堂父亲则是在中国传教的中国人。赛珍珠和林语堂都十分热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也很乐意陶醉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赛珍珠一直想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始终不能如愿,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发现了"林语堂"这个名字。她觉得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经过几番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于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在林语堂家里见面。当时林语堂住在忆定盘路,话题自然谈到了写作问题,赛珍珠认为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方面的书,都是外国传教士出于对中国的猎奇,或者是对中国人小脚、辫子之类的丑恶大展览之作。
如美国传教士A·H·史密斯写了《中国人的特性》,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42)在1894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素质》等。书中竭力丑化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容貌丑陋、长辫小脚、不守时间、不懂礼貌、爱好嫖赌、不讲公德、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虐待动物、麻木不仁、心智混乱、因循守旧、遇事忍耐、漠视精确、知足常乐、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柔顺固执等等,都是中国人的天性。甘露德的《中国的毛病何在》一书中,竟污蔑中国及中国人民......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外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的想法如此相近时,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追求赛珍珠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知道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出这本书。于是,一个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从1933年冬着手写起到1934年7、8月间,林语堂用了10个月的时间进行创作,最后在庐山避暑时全部完成,这就是《吾国与吾民》。
八、《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引起轰动
关于《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写过一篇说明文章,叫《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文章说:"《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海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
'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于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鞵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