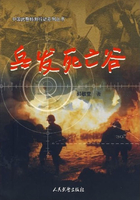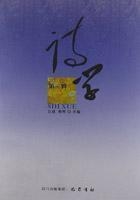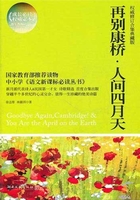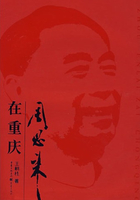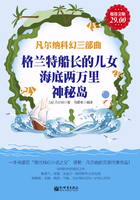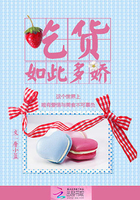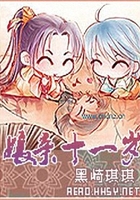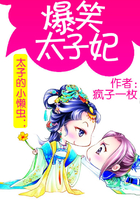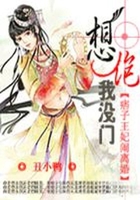新的社会制度性机制,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媒介或其他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又是它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公共空间。现代知识分子、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前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领域。不管是在政治性报刊、商业性报刊还是思想文化启蒙性报刊,都活跃着一大批从传统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传统权力之外寻找新的人生支点,在封建庙堂之外开辟新的社会空间,为现代社会培育新质。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也渐渐从传统的庙堂理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权力的迷梦中省悟出来,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报刊领域,各种形式的报刊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并诞生了一大批优秀报人,在推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闻报刊功不可没。
从文字到书籍,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阶层的重要思想传播媒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嬗变的过程中,部分有识之士在丧失功名的荫护之后,发现了舆论的力量、大众的力量和报刊的力量,在救亡、富强的历史使命召唤下,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刊传媒化转型,将毛笔书写的墨迹变成了报纸上规整的铅字,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责任载上了大众传播的快车,不断影响着社会与中国历史和未来的走向。
二、电视媒介化转型
第一节 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的两次媒介化转型 (2)
中国电视事业诞生于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最早的固定观众是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视机在中国长期并未普及,而且,由于"文革"时期的破坏,中国电视事业真正的春天应该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到来。
1.80年代至90年代初知识分子对电视的拒绝
早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传统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亲密接触。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些知识分子可以被称为早期的电视知识分子。但是,当时电视仍属于高档消费品,并未走进千家万户,而且电视函授教学仅仅是一桌、一人、一叠讲稿的固定模式,这些所谓的早期的电视知识分子远未达到今天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
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在知识分子世袭的印刷媒体领域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读物的畅销和流行,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出现了某种失守的状况。而在电子媒介领域,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分子,除了给电影以适当的命名和承认之外,对于广播电视,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嗤之以鼻。对于介入和参与电子媒介的知识分子,视其为离经叛道。由于对于电视媒体缺乏了解,甚至是在长期政治迫害中养就的怕出名的避祸心理影响,在知识分子人群,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更多的态度是拒绝上电视。其中,钱钟书先生对于电视采访的回避可谓是个代表。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1991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专辑《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名列其中。摄制组几次与钱先生商议,均遭拒绝。后来,摄制组了解到,只要能做通杨绛工作,事成大半也。他们给杨绛打电话,一打便是一个多小时。可时间再长,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两个字--不行。组织者在电话中说:"被录制的文化名人,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钱先生立即从旁插话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这钱吗?"甚至一些文化气息浓重的节目,钱钟书也拒绝参与,例如他始终拒绝上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这个节目。对于电视的躲避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一次夏衍生日,夏的女儿给同住一个医院的钱钟书送来一块蛋糕,钱先生脏器衰竭症状刚消失,病情缓解,胃口大开。他坐在床上边品尝蛋糕,边与人谈天说地。突然发现被记者的摄像机捕捉,钱老先生一撩被子,连人带头带蛋糕就捂了进去,全然不管白、红奶油弄得满头满身满被子。
当然,钱先生坚决地拒绝上电视,也跟他"默默者存"的处世哲学有很大关系,但毕竟这种不为金钱和名声而动的精神令人敬仰。不过,无论如何钱先生与电视还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余秋雨先生说:"在前辈学者中,钱钟书先生我倒是不认识。有一阵子很多媒体以钱钟书为例论证学者必须拒绝电视,我就觉得缺少根据,因为在钱钟书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还没有电视。后来我的朋友黄蜀芹、孙雄飞要把钱先生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我有机会读到钱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好些通信,发现他不仅没有拒绝电视,而且还兴致勃勃。可见,说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伪造的。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本文系摘编整理自2006年年初余秋雨在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的《秋雨时分》的第一部分,重点解析人们关于文化的一系列误区。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余先生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钱钟书先生拒绝电视,主要是拒绝自己上电视、被采访,谨防媒体吹捧自己,这和《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是两个意义层面上的事,他给自己制定了三不主义,即一不接见访客,二不接见新闻媒体的采访,三不参加一切会议;另一方面,《围城》的被改编,钱先生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在给改编者的信中谈道:"看来剧作家要编戏,正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也是没有法儿阻止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同志曾写信要求改编《围城》,我不支持,但不阻拦。我很惭愧,也很荣幸。
"而且,之所以同意黄蜀芹改编《围城》,是因为钱钟书、杨绛同黄蜀芹有两代人的交情,四十年代杨绛的成名作《称心如意》就是由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导演获得成功的,而且这笔稿费对于当时身陷困境的钱钟书夫妇可谓是雪中送炭,钱钟书也说:"我们两代人有这个交情,这交情我一定要强调,表明人是不能忘本的嘛!对上海的几位同志来这里,我要是不识抬举是不对的。" 如果仅凭余秋雨先生所说的情况就认为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个伪造的形象是有失公允的,毕竟钱先生并未成为一个"电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拒绝电视媒体的例子还有一些。王选院士在一个题为《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的演讲中曾说过一段话:"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
2.90年代中期至2003年,第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介入电视
20世纪90年代前期是中国电视进入市场的又一个新高潮,中国电视的体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至1994年底,全国有电视台766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38917座,卫星地面接收站73337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3.4%。全国有电视机27487万台,平均每百人23台。电视媒体在这个时期迅速普及,立刻便展现出电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逐步取代报纸在中国新闻传播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第一媒体的地位。
同时,90年代以后,伴随着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消费文化的市场却大大扩张了,文化公共闲暇时间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需要出版业、报业和休闲杂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产品。于是,在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诞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有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电视媒体在社会中的强大舆论影响力不得不让知识分子侧目,而熟悉、适应消费文化的媒体知识分子开始迈出了新步伐,在电视媒体内部知识分子的介引下逐步接近电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媒介化转型也悄然展开。通过这次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向后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从思想启蒙中的"立法者"向媒体化生存的"阐释者"转化,从引导大众的精英立场向捕捉大众趣味的跟随态度转化。
尹昌龙先生谈道,在1997年,其实,像名人一样风光的,不仅仅是影星和歌星们,一批文化人也带着自己的声音和形象竞相登场了。在文化日益扩张的今天,文化人成为名人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了。就在文化界竞相讨论"电视知识分子"这一新概念的时候,一批文化人已在媒体上频频露面了。面对观众,他们讲述着太多的事情,除了人文精神、商业道德、环境保护等专题之外,计划生育、偷税漏税、非法同居等等问题,也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视野。
一些知识精英从鄙薄电视到参与电视,立志改造电视。如钱钟书般拒绝上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北京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等陆续参与到电视节目的策划活动当中。1999年,海南以文化品位著称的刊物《天涯》约请电视人时间和学者杨东平,探讨了一个多少令人欣慰的话题--电视与知识分子的"联姻"。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电视业中来。他们看重难得的发言权和面向公众的机会,当然也有私人利益的润滑。杨东平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参与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自己的性格倾向、兴趣倾向有关,比较关心社会问题,愿意面向公众发言。我深感我们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种发言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充分地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拒绝大众媒体。"电视人时间认为,不能不承认电视工作者从总体上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要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给观众的话,存在知识、修养和阅历的不足。如果希望节目内容深刻,增加电视的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就需要借助学者的智慧。若把社会精英、社会智囊调动起来,一同做电视的话,电视节目的质量会好得多。电视业需要知识分子幕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