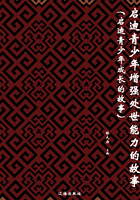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在谈到自己上电视的情形时说:"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的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陈力丹先生这段颇具代表性的总结用事实证明了笔者上述的论断。电视知识分子能否在电视场域中充分表达知识分子观点,是个值得怀疑和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借助他们魅力,的确为电视场域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和知识浓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
第三节 电视知识分子与学术场 (1)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由于多来自学院派知识分子,其身份多为大学教授和学者,所以,社会舆论中对他们诟病最多的,是其行为对于学术场域规则的扰乱。处于媒体场域和学术场域中间位置的电视知识分子,不仅在媒体场域获得利益,同时在学术场域也饱受批评。
一、学术场域的自主性
布尔迪厄在解释场域的逻辑时谈道"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社会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与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摒弃在外的。
"也就是说,在社会不同的场域中,都存在着各自作为内部法则的"自主性",在其他场合,他还详细解释了"自主性"问题,"'自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如数学场,是这样一个场: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竞争对手们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发现他们所介绍的成果要获得自主性,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同时,他也认为知识文化活动有其自身特有的"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s),并对其他场域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场域保持相对的自主性。笔者认为,有关"知识场域"的观点同样适用或类似于中国的"学术场域"。
应当明确的是,现代社会的学术场域自主性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专家托马斯·班德在《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关于美国学院知识分子的社会史论稿》一书中谈到,在19世纪早期,业余研究者和公共学术讨论乃是美国各城镇"知识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业研究者或艺术家则在当代的公共文化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随着"学科职业化"(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ism)的出现和"大学时代"(the age of university)的来临(1876年,位于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院。这一事件标志着"大学时代"的来临和美国现代学术体制的确立),业余研究者和公共学术讨论便逐渐被排挤出了美国现代学术体制,而丧失了其在学术领域或"知识生活"中的合法性地位;与此同时,专业研究者则凭借其日益严密的"专业话语",逐渐确立起了"专家权威",并逐渐退出了"对公共问题的公开讨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学科职业化"所伴生的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日渐疏离的倾向,这就产生了学术场的区隔,知识分子在以大学为主的领域中营造起属于自己的学术场域和学术话语,从而形成了学术场的"自主性"。
当然,中国学术场域与西方学术场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在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皮毛论"的认识,使得权力场和政治场对于知识分子场域和学术场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政治权力的涉足让学术场严重缺乏自主性,与政治结合紧密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场中获得了优势位置。改革开放以后,学术场受政治场域的影响逐渐减少,恢复了部分自由的学术氛围。8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文化热"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翻译引进了一大批当代西方学术著作,使封闭的中国学术界了解到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水平,注入了现代学术气息,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出现了一批用新观点、新方法剖析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进入90年代,中国出现了-些用现代学术方法扎扎实实分析中国文化的学者,他们提倡一种科学严谨的学风,提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口号。
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开始走向成熟,走向自律。但是,9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又使经济场又成为另一个影响学术场的重要因素。陶东风先生这样谈道:"在中国90年代的文化市场化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确较之计划体制时加强了,甚至出现了像自由撰稿人、书商、文化经纪人、新式记者之类的新文化人类型;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看到,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依然生活在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夹缝中,而不是在国家(政府)之外。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其他市场中政府的影子无所不在一样,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也时时可以见到政府那双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请不要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上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混淆)在起作用。
所谓的'新文化人'阶层既不是什么对于权力说'不'者,也不是什么对市场说'不'者,而是在权力与市场中间周游,其中的高手们在权力与市场这两个婆婆之间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他们是权力与市场结合产生的典型结构。"改革时代中国知识文化场域的最大困扰所在,也是造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诸多尴尬的根本原因,因为改革意识形态的强大正当性压力往往使许多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无法辩护自己的文化主张以及对改革的某种深层困惑,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极为疲软是个明显的例子。虽然,有学者认为,正当的知识评价标准首先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商谈、对话与竞争的产物,而不是"钦定"(state-designated)或"钱定"(market-dominated)的结果,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学术场域与外部场域的关系。但是,中国学术场域的现实情况是,既受到政治场的制约,也受到经济场的影响,同时也有来自于媒体场域的引力和干扰。
二、电视知识分子对学术场的影响
电视知识分子既存在于学术场域之中,需要学术场域的认可来完成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又通过媒体场域对学术场域进行形塑,巩固或颠覆学术场域规则,以达到自身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或者改变它们的兑换率以谋求自身利益,并间接担当了媒体场域干预学术场域形式的"中介人"。在这种场域的实践中,造就了电视知识分子特殊的"惯习",并由此产生对学术场自主性的影响。对此,布尔迪厄在论及新闻场通过知识分子记者影响其他场域来行使权力时,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的论断,比较适用于审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行为。笔者在此认同中法间存在着国情的迥异,而强调的是具有普适性的批判方法的借用,而且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陶东风、金元浦、陈力丹、黄顺铭等都曾利用布氏理论对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进行过精辟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示范。
1.有限生产场域与"赢者输"逻辑
布尔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域具体区分为(1)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及其为了自己的再生产而对教育系统的依赖;(2)"大量受众"(mass audience)的生产场域。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是高度专门化的文化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什么是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标准而斗争,其努力的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市场常常围绕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资本的符号资本的专门形式而得到结构。它们是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市场。相反,布尔迪厄认为不那么专门化的符号生产场域则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和大众趣味等外在的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东西。这种文化生产场域表现的不同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其重要根源来源于有限制的生产场域本身内部,在那里,布尔迪厄发现,在那些占据了机构的位置并试图在符号领域保存与再生产现存秩序的人与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资本形式挑战这个秩序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击。
按照布氏理论,文化生产场域可以划分为两个有明显区别的场域--有限生产场域和大规模生产场域,具体到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学术场与大众媒体场域的对立。这两个场域的不同体现在对于符号资本认可方式的差异和自主性的强弱。学术场域内,"高度专门化"的符号认可方式为"同行认可",也就是说,要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在学术场内拥有较高的位置,决定权在于同领域内研究者的共同确认,通俗点说就是"口碑"和"声誉"。在大众传媒场域里,确定一个人或作品是否拥有优势符号资本,决定权在于"商业成功"和"大众趣味"。
电视媒体场域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域,在其中评价知识分子是否"知名"和"流行"的标准与知识分子来源地--学术场有上述的不同。处于两个场域交界处的电视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符号资本,既有来自学术场内的,也有来自电视媒体场域的,但是,这两种资本形式在对方场域内所遭受的待遇却是迥异的。来自于学术场内的"同行认可"可以为电视知识分子在电视场域内实践提供"肯定性"的符号和文化资本,但也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大众(不了解也难以了解学术符号资本)的认可则是最重要的"认可"砝码。相反,在学术场域内(出于学术严肃的态度或者可能的嫉妒或不屑),对于电视场域的大众认可则往往给予"否定性"的评价。
陶东风先生从布氏的文化生产理论角度分析于丹现象时谈道:"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门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逻辑或'颠倒的经济'。我认为,布迪厄(布尔迪厄,笔者注)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这种"赢者输"现象从中国学术场开始遭遇经济场和媒体场"侵犯"之初,就已经逐步显现了。例如,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于王朔现象和余秋雨现象的"炮轰",甚至有人以出版批判余秋雨现象的书籍而牟利。
文化场域的裂变与知识分子分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不断有知识分子从学术场中"逃逸",寄居于大规模生产场域,而退守于学术场核心地带的知识分子则对于这种行为给予严厉的批判。不过,这种矛盾在中国学术界的表现略与西方不同,在学术场域中仍然有许多肯定电视知识分子的声音。依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西方学术场域中批判这种现象的知识分子多是"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但是中国学术场域中的学术权威对此"沉默"或"默许"的态度居多,反而是一些处于知识分子场域底层的青年学者发出最激烈的抨击,如所谓的"十博士批评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