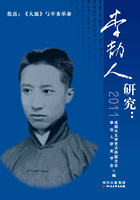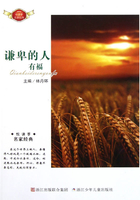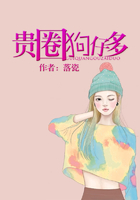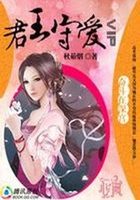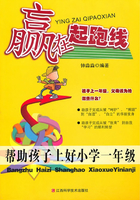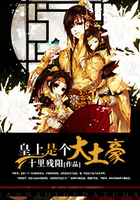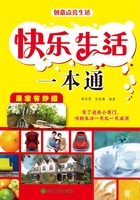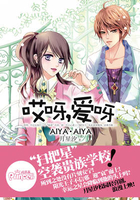从于丹现象来看,就有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和以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十博士联名支持于丹,这里虽然有正常的学术争论,但也存在着个人感情化的批判,可能存在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也难脱"哗众取宠"的俗套。从知识分子自身发挥正面社会作用上看,根据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在传媒中发挥批判作用的情况来看,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面前,常显得微不足道,只有联合起来的声音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合力和共振,从而在社会舆论中占据强势地位,这就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团结和整合的要求,因为经常处在激烈地内部争辩和相互攻击中,会失去解决问题的宝贵时间和热情。
二、有中国特色电视体制的影响
研究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体制,因为不从媒体体制的差异来分析,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布尔迪厄能够在法国的电视中批判电视,如果按照商业电视媒体逻辑来思维,这样的行为难道不会因为电视媒体投资人和电视广告商的反对而禁止播出吗?其实,同一质地的媒体,在不同的体制中往往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和态度。知识分子搭载于不同体制的电视媒体中,也必然受到传播平台的约束和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西方主要的电视体制和产业形式
由于广播电视所需的频率为稀缺资源,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在任何国家都受到了比报业更加严格的控制,也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国家的广播电视都带着鲜明的本土化色彩。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体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重点体现在广播电视的所有制问题、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及管理等诸方面。其中又以所有制问题最为基本,它制约着问题的其他方面。不同的广播电视体制又相应地影响和决定了相关国家广播电视的现有状态和发展趋势。广播电视特征最为鲜明的三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公有制、国有制,分别形成了三种最主要的广播电视运作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化广播电视模式;英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以及日本现行的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主的双轨制模式;在少数欧洲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政府控制的国有广播电视模式。所有制的不同表现了电视传媒与国家和政府的不同关联,直接影响媒体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面前的选择。
具体在产权形式上,电视产业的经营主体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三种: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机构、公共或社会法人团体和自然人。与之相应的电视机构组织形式就表现为国营电视、公营电视和私人电视(其他形式如合营或股份制都是这三种基本形式的变种)。从维持运营所需的收入状况和赢利模式上看,国营电视主要靠国家拨款运营;公营电视主要靠收缴法定的电视收视费生存;私营电视主要靠广告和订户费过活。在少数国家,国营或公营电视机构具有一定的特权,既接受政府拨款,又收取广告播出费。
不同的经营形式也决定了在电视节目内容上表现出的差异。被称为公共电视的公营电视和国营电视,其电视节目比较重视社会效益,注重节目的教化功能。由于"通过一定制度的设计,以公共视听费、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盈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社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广播协会(NHK)就是典型代表。BBC是根据"皇家约章"特许经营广电的公共企业,最高领导是董事会,其成员包括各政党和社会各界代表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地区代表,由政府提名,国王任命。董事会决定公司的方针、政策,并任命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政府内务大臣受议会委托监督公司的经营政策和节目内容,向公司签发执照,但公司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和业务上的独立性。NHK是依据日本广播法设立的特殊法人。
最高机构为经营委员会,其成员由首相经国会同意后任命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经营委员会任命会长,并由他组建理事会,负责日常业务工作。政府责成邮政大臣监督NHK的活动,但是NHK在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同时,享有编辑自由、表达自由,其业务活动不受任何非法的限制和干涉。杨东平先生谈到,国外有一些公共频道,它会满足各个层次受众的文化需求,会保留那种虽然小众但有品位的节目,会保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也会呈现主流文化、严肃文化的价值。而又称商业电视的私营电视,由于收入渠道主要为广告和订户费,对于大众口味和受众市场的依赖较大,电视行业内部竞争也相对激烈,所以其电视节目内容以谋求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例如在美国,这种私有私营的商业台要占全国广播电视台的4/5以上,它们在商业运作中激烈竞争,不断兼并集中,其电视节目制作标准以注重收视率为主,媚俗倾向严重。当然,一个国家也可能存在多种电视产业形式,例如美国广电业基本上是商业台的天下,但是美国也还有300多座公共电视台,这些公共台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为公众提供教育和服务,其创办者有州政府、地方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社会团体等。
2.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体制
中国电视传媒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历了重要的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化改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体制过渡,由单纯的事业性质到在保证事业的前提下,承认和发展传媒的产业功能。
当前,电视传媒的"双重属性"论,即电视传媒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两大根本性质得到了广泛承认。其形象化表述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划分,其定义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据统计,21世纪初我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家,职工总数近3000万人,资产近3000亿元,仅2002年国家对事业单位的预算拨款就达6590亿元,占当年GDP的6.9%,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改革文化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历史任务,并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了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并将当年定为广播影视的"产业年"。中国电视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同时电视传媒的经济属性又是电视传媒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需要追求经济目标和经济利益。当下,中国电视传媒表现为公共电视之名、商业电视之实,这种模糊和混合的身份,使得电视节目既有严肃、负责的宣传和教化功能,又有轻松、甚至媚俗的泛娱乐化之风,这既是中国电视体制改革的过渡化表现,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运营模式。虽然近年来有学者也在呼吁建立中国实质意义上的公共电视,但是已进入瓶颈期的电视体制改革,目前尚难以改变电视媒体双重属性的现状。
3.电视体制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影响
有中国特色的"双重属性"的电视体制也对介入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一方面,电视媒体的事业属性为其提供了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的电视媒体是党的宣传事业的一部分,各级电视机构是同级党委的宣传窗口和平台,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甚至具有比权威的《人民日报》早一天发布重大新闻的权力,这种深厚的政府媒体、党台和国家台身份是一般其他国家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所不可企及的。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电视台发言就为发言者直接贴上了"官方认可"的标签,所以,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在拥有大众媒体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以外,还具有媒体背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权力。可以这样说,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较之西方同行,在电视媒体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力。
当然,这也对他们如何谨慎使用这种权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电视媒体的经济属性,使得其必须面对广告收入和收视率的压力,对于"衣食父母"--电视观众,它们少了些公共电视引导芸芸众生的勇气,倒添了些追风跟潮的态度:在中国的电视频道中,最严肃的国家宣传工具之一的《新闻联播》也会被商业广告包裹得严严实实;在普天同庆的国家仪式--春节联欢晚会上到处可见广告商的利益;得不到大众青睐的文化电视节目总是面临"下课"的窘境等等。如此的电视环境中,知识分子在参与电视节目时,常为了迎合社会潮流而自觉改造学术话语模式--讲故事、揭谜题、说笑话......双重的电视媒体属性也给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带来了双重的特性,既有官方认可和知识权威的背景,又要讨好普罗大众的审美品位。
第二节 类型与风格 (1)
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方式是复杂多样的,在排除把电视行业作为自己终身和唯一职业以外的知识分子以后,我们可以将他们区分对待。有学者在梳理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关系时,归纳出"节目专家"、"传媒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节目专家"参与新闻节目、频道策划及评审,每月或每季度一次,以不定期、非公开的方式,起到提升节目品位和增加专业含量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出现时不定期、公开地参与社会问题讨论,充当意见领袖,扩大社会公平;"电视知识分子"以学者和专家的名号,公开、频繁地参与专业问题及各类问题讨论,是在制造知识英雄并造成节目的另类庸俗。笔者不完全认同以上的分类方法。基于前言中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语境下"电视知识分子"一词从诞生起就拥有比较宽泛的外延,本研究中把非终身电视职业身份的业外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行为,都纳入到"电视知识分子"的考察范围。笔者区分是否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是:一、"知识分子"身份的社会认可来自于电视行业以外;二、通过"知识分子"身份介入电视运作;三、从电视媒体获得利益。通过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的不同而区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两大阵营。
一、"内部人"
此处的"内部人"并非指电视业界的知识分子,而是指以其他职业身份进入电视行业内部运作并深度影响电视节目的知识分子,他们参与电视运作的"游戏规则"制定并协助完成。电视媒体向这类知识分子"借脑"以提高节目水平和文化品位。具体而言,"内部人"也可以分为"幕后谋士"型、"幕前主持"型。
1"幕后谋士"型电视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