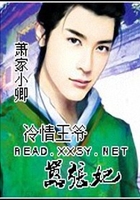"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老四,你这句话可没说到我的心里去。我早看出这步棋,不论你是贫农、中农,都得走社会主义,只有走社会主义才是奔铁饭碗,活的才有味!"
在浩然的文本中,我们看见了各种语言,果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既有民间俗语"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又有农民口语"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也有"只有走社会主义才是奔铁饭碗"这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话语,三种不同路数的语言奇妙融合在一个文本中,既满足大众文学趣味,又符合国家意识形态。浩然创造出了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语言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语言本土化。
在1962-1967年的第二个阶段,浩然迎来了文学生涯的高峰期,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紧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文艺创作方法,塑造出第一个完全符合党政需求的工农兵阶级英雄形象萧长春,并运用本土化语言,有机融合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表达。浩然此阶段的成就来自于对文艺政策的准确领悟,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三)1967-1976年 (1)
1966年,对于中国是一段狂乱记忆的开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众多文学艺术者被迫停止文学创作,从生活到创作,甚至生命都受到严重威胁。浩然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对比鲜明地成为为数不多保持创作并成为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与"文化大革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依然保持高度一致。
值得讲述的是,在这段文学创作期间,浩然的创作演变就是一部微缩的文学史,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文学,从主流文学由极"左"政治发展成"阴谋文学"的过程中,浩然的创作是一个重要过渡,《金光大道》既是浩然个人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由十七年文学转向"文化大革命"文学的转折性代表作。浩然创作成为重要转折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既有代表性,又有独特性。他的创作具备两种文学形态自然过渡的特征,所以有代表性;他能成为这个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人物,原因在于他能准确把握主流文艺政策的走向,并且比之前更激进,这就是其独特性。《金光大道》的创作正式开启了"文化大革命"文学"三突出"、"主题先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等创作手段的运用。最早把农村阶级斗争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大概是浩然,最早成功使用"三突出"、塑造无产阶级典型英雄形象样本的还是浩然,这些"最早"、"最成功"、"独特"、"转折性"都来自于浩然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准确入微的贴合把握。
"文化大革命"文学一开始就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求作家根据典型化原则,在实际生活基础上集中概括,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文学中的典型化原则,已远离典型最初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的概念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典型就是要求文学创作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作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制,而必须对生活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能动反映,目的是用创造出的各种人物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求无产阶级文学根据实际生活塑造艺术典型,又要避免直接表现真人真事呢?从根本上讲,要求避免真人真事,是由于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有局限性,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就可以从许许多多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身上进行典型概括,塑造出符合历史期待、高大丰满、光彩照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典型化原则,重要的不在于塑造典型本身,而是为了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树立典型形象,是为了改造现实人民。由十七年文学向"文化大革命"文学演变的过程中,文艺政策愈加党政化、扭曲化。
主流文艺政策的阐释者利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进一步阐释发挥,认为"毛主席的上述教导,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典型化原则,论证了文艺创作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概括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精髓,是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理论基础",认为塑造比真人真事更突出革命意义的英雄形象即是革命典型化原则的精髓。
随着"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势的激进化演变,70年代的文学创作由强调"塑造无产阶级典型英雄形象"为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其内涵迅速升级为"努力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开始了十七年文学向"文化大革命"文学的转变。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浩然的《金光大道》以准确的政策把握能力,快速地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多重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作出反应,不但成功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高大泉,还在作品中体现了党内走资派与革命势力的斗争,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从单纯反映党外阶级斗争路线"深入"到党内阶级斗争,准确贴合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政策的要求。
1975年,浩然在《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一文中提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是,社会中的-切现象不一定都能变成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典型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对这个问题做到真正的理解和接受,又确信不疑地加以坚持,是能不能写出革命文艺作品的根本条件。"毋庸置疑,浩然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深刻"、"准确"的理解。他说:"在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在写《艳阳天》时候,对这个问题开始觉悟;经过党内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通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还有无情的事实教育,在动笔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我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那么,浩然的进一步领悟和提高在创作中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我们来看浩然自述他对政策理解的"提高":"在写《艳阳天》的阶段,我的注意力只在基层,或者说较多地看到下边问题的严重性。
对上边,尤其高一层领导,只注意到党外的右派,没有多考虑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这种状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改变。所以从写《艳阳天》的时候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写《金光大道》时候,我进一步认识到'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这种认识的发展,写第二部的阶段,比写第一部的阶段又有所加深。"说到底,浩然对"这个问题的觉悟和提高"都是围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创作的。
从浩然自述可以明确看到《金光大道》追随政治时局变化而变,紧扣党内走资派斗争路线构设故事情节,首先创造了芳草地这个包含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里展开两条路线错综复杂的矛盾,既表现贫下中农同地富农的矛盾,以高大泉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与被打倒仍不死心的地主歪嘴子、漏划富农分子冯少怀之间的斗争,又展开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表现高大泉和走资派干部张金发之间的斗争。
对小说中后一条路线斗争的情节设计,浩然是有充分现实"依据"的,"写第一部的时候,从我们党内揪出了一个窃取一部分权力的叛徒、内奸***,这个事实,在写《艳阳天》的时候没有,我对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极重要的理论理解不深,没有想过我们党中央还隐藏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的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我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理解了在我们党内有一条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它代表着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我认识到,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地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本质地反映时代,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除了围绕两条互为表里、倡导现实的政治路线设计小说情节外,如何具体展示斗争路线,还需要切实的人物形象塑造来实现。
为此,作者塑造了代表党性、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高大泉的形象,进一步成熟地运用"三突出"手法,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为此,浩然改进了《艳阳天》创作中对文艺政策贴合还不够准确之处。《艳阳天》对反面人物马之悦描写过多,其心智和谋略甚至高出萧长春,这显然不符合三突出要求,改进后的《金光大道》极力突显正面贫下中农力量,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反动势力歪嘴子和冯少怀显得十分弱小,张金发也不过是一个摇摆可怜的胆小人物,尤其突出了高大泉的形象。所以,我们在《金光大道》里看到高大泉比萧长春更"成熟",在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斗争方式上,高大泉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萧长春仍需党组织的指引,身边还有不少有丰富人生经验的老一代贫农出点子,而高大泉似乎天生就是革命领袖的料子,一切困难在他面前迎刃而解,在发家竞赛、秦富告状、邓九宽闹退社等斗争事件中,高大泉都表现出优秀果断的政治事务处理能力,事事独当一面,成为芳草地生活、生产中不可缺失的一位英雄领袖,真正成为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更加明确地突出英雄人物中唯一的典型形象。
由十七年文学过渡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代表作。"文化大革命"中,浩然反复研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断深入研究怎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据他自述,他认真地、有计划地学习了样板剧本,同时把介绍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文章归纳为若干专题,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深入研究怎样在一切人物中突出塑造好英雄人物、怎样写矛盾冲突等等。直到晚年,浩然口述的自传里仍颇自豪地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我。这个路是我蹚出来的。"这种准确研究主流文艺政策"精髓"的创作能耐,虽然成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青睐,却推着作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创作上越走越远,70年代的《百花川》、《西沙儿女》就是证明。这是两部失去艺术性,延续政治话语教条式书写的小说,它们的出现使浩然小说几乎走向"阴谋文学"的边缘,加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后浩然毁誉参半的命运。
(三)1967-1976年 (2)
不管怎样,从浩然初登文坛领悟到创作的"奥秘",到写作《艳阳天》到达文学生涯高峰,再到进一步深入主流文艺政策"精髓",创作出《金光大道》,成为"文化大革命""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浩然,他与众作家的不同在于,准确贴合主流文艺政策。这一点同时造就他成为50到70年代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变迁的最佳样本,成为每个文学转折点上记载历史的记忆,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史样本。我想,造就浩然独特性更隐蔽的原因,是他"准贴"主流文艺政策的个案文本无形中明确演绎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学的构设。从延安文艺时期开始,毛泽东对于新中国文学就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认识和构想,但由于知识分子骨子里的不羁和时代自我政权的不稳固性,在策略上无法"一刀切"地对待文艺问题,而是循序渐进,一步步迂回地实施着他对中国新文艺的构想。
比如,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初步完成,到1943年正式发表,再到1953年确定其文艺地位的唯一性,三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之间的延宕,就是毛泽东迂回实施文艺计划的一个典型例子。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口号的提出、稳固,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事实上,知识分子在经历延安审干、抢救、整风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批评运动后,大大"收敛"了文人的自由行,无论何种创作心态的文艺人,经过一宗接一宗的文学事件后,大部分逐渐收归到党政领导的文艺体制下,然而,文人的意气与天真总会时不时流露出来,并与毛泽东的文艺理想形成冲突,部分知识分子借文章隐喻性地发表对文学真挚的看法。而浩然在这个复杂、庞大的文艺政治背景下,果断、准确地独尊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政策,丝毫不走"弯路"地成功占据文坛一角,天生的政治敏感在特殊时代成就了他的"与众不同"。
三、"钩心斗角"与"集体精神"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