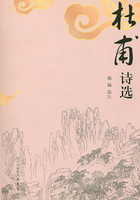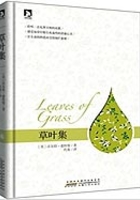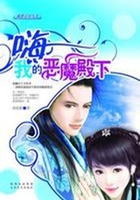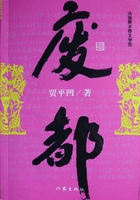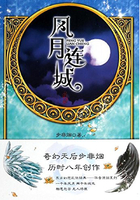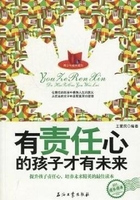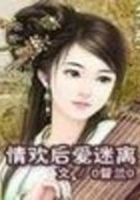王金环呆坐着很久,更加痛苦和茫然。她的思路越缕越乱,她的路子越找越绝。不知道为什么,她想念起生她养她的酸枣沟,想起那儿重重的高山,条条的沟岔,层层的梯田,丛丛的树木,一排排的石头房子和石头墙。她也想起那儿的人,想起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还有他们各自的脾气和说话的声调。图钱财给她包办婚姻的老爹先死了,照老礼儿帮着苦害亲人的老妈,也跟着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哥有了一群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自己都顾不上,就是想惦记别人,也力不从心。二哥当了几年兵,在大西北一个荒凉的大沙漠边缘地带驻守,后来在当地转业,在当地讨了个老婆,安了家,一直音讯皆无。他也许不记得泃河边上还有这么一个受罪的妹子。三哥倒是个讲外场,待兄妹亲的,可惜不走正路,跟几个村干部大伙偷盗了分销店的东西,给公安局逮去判了刑。......王金环活这么大,没走出过方圆三十里的地盘,也没念过地理课本。她知道中国很大。她常听下乡的工作人员讲中国有八亿人民。八亿,这个数目字可真不小:就是八万万!在八万万人里面,谁能跟寡妇王金环亲近?谁是寡妇王金环的亲人?只有一个,就是闺女。
闺女小妞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一口水一口饭喂养大的。不仅是她在没有亲热和乐趣的家庭生活中挣扎到今天的精神支柱,也是她再接着挣扎下去的奔头和指望。倘若跟这个独生闺女也闹了生分、绝了情,那么,孤苦伶仃、苦难重重的王金环哪,活在这个人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呀!她想到这儿,感到心头发紧,浑身发冷,仿佛要地陷天塌,使她无比恐惧。......小妞显然是听见妈妈的喊叫了。她虽然没回头,却迟疑了一下。可是她立刻就抬动脚步,迈出大门。一切一切希望和乞求的窗口,都在这一刹那间对王金环关闭了。她眼前一阵发黑。
她那本来就虚弱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地楸了一下。然而,她没有掉泪,更没有哭泣。直到此时此刻,闺女在她胸膛撩拨起来的那股子小火苗儿,不仅没有因为前思后想而熄灭,恰恰相反,她越对自己的处境悲哀而绝望,就越增加对死鬼男人的怨恨。今天,这个怨恨必然地蔓延扩散到闺女的身上。在绝大伤痛中,那火苗子就一拱一拱地猛烈地烧起来。她活了三十四年,尽管一直在委屈掺着愁苦中腌泡过来,但她血脉潜在着的那种不肯示弱、争强好胜的素质并没有泯灭。她若以为有必要,就敢于反抗一切企图逼迫她、扭曲她的势力,包括支付出死的代价。王金环就这样如呆如痴地坐到傍晚时分。
另外,短篇小说《衣扣》意味深长地体现了浩然对80年代农村社会的思索:男婚女嫁、男欢女爱是人自然本性的舒展,但是,逐渐扭曲的社会风气、人的金钱贪欲,使人自然美好的情感受到污染,衍生了罪恶的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农村女人独自在家务农,遭到小偷奸杀的噩运。耐人寻味的是,从女人被奸杀的起因和贼人犯罪的理由看,都是人的本性遭到社会压抑的结果。女人为了赚钱,苦口婆心送丈夫进城打工,独自一人辛苦操持家务,毕竟人非圣贤,也有耐不住寂寞的时刻。贼人当兵复原后,因社会上向钱看的风气,他只能打光棍,在饥饿和性本能都得不到解决的情形下,走上贼路。但可悲的是,他把仇恨的对象发泄到个人身上,同样可悲的是,女人让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最后不幸地遇见另一个被压抑得更深的男人。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表现了80年代浩然对改革中农村的新思索,一篇篇独立思考、不同于以往创作风格的小说,把作家的创作推向深入的艺术境地。
在新时期浩然的小说里,小说布局、情节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中篇小说《能人楚世杰》在描述楚世杰与农村不正之风做斗争时,采用辗转迂回的情节,把一个严肃的普遍现象写得讽刺、有趣。楚世杰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个认死理的朴实农民,与时下送礼走后门的关系学格格不入。小说没有从正面写他的反抗,而是巧妙地利用楚世杰也暗合此道,先是送礼给支书让儿子能够外出做工,又行不改名地写检举信告发受贿书记,遇到官官相护、检举不成功时,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受贿的支书吃了哑巴亏。整个故事充满诙谐气氛,在诙谐中显示了楚世杰的正直、能干,讽刺走关系的不良风气。
《姑娘大了要出嫁》写两代人的婚姻恩怨纠葛,批判顽固的世俗偏见。厉秀芳是个被母亲赵淑贤严格管教的文静姑娘,她爱上农民刘永发,但母亲硬要她嫁给靠当县党委书记的老子走运的朱新亚,她软弱地不知如何争取和表达自己的爱情,居然选择自杀。自杀不成,被看管果园的黑石峪书记刘贵救下,一打听,原来刘贵是三十年前和母亲赵淑贤差点因封建包办婚姻结合的"故人"。刘贵好人做到底,面见赵淑贤,终于使她意识到自己也是以反抗家长包办婚姻而争得个人幸福的人,最后皆大欢喜地成全了女儿。同样,《傻丫头》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布局,在嬉笑之间鞭笞婚姻买卖现象。类似的巧妙情节结构还有中篇小说《老人和树》、《乡俗三部曲》等。
尽管艺术手法变新了,但浩然仍然认为在艺术形式上,彻底撇开作家自己已经形成的个性特点,就等于没有了自己。他说:"生活是发展变化的,看作品的读者心理和欣赏习惯也在变化。因而,艺术表现形式必须相应地随着变化。我意识到这一点,尽力地改进和提高。但是,我觉得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基础。"作家对艺术形式力求改进,但仍然坚持不忘"写自己的味儿"。所谓浩然的味儿,就是以民族化、大众化语言和结构写小说。受到民间文学影响,在对大众化的长期探索基础上,浩然坚持用娓娓道来、明净流畅的口语化语言呈现小说故事。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浩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农民文学风格。
综上所述,浩然在接续十七年时期后的十年里,努力迎接新时期变革,在获得重生的视角中保持着作家独有的创作理念。新时期文学里,浩然的"变"表现在:以探寻"人"、写人的心灵和深层意识结构小说;关注农民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批评极"左"思想下变质、扭曲的农民干部;肯定农村经济改革下农民自由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艺术手法的纯熟。浩然的"不变"在于:对传统道德美善的肯定;对平凡农民干部忠诚于党、心系群众集体的"永远歌颂";坚决支持集体化道路以及农民化文学风格不变。观察出浩然的"变"与"不变"并非难事,问题在于从十七年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中,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浩然笔下的农村小说有何特别的意义?与80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学世界相比,他的变与不变有何启示?尤其在"去政治化"后,越来越倾向"纯文学"写作的80年代,浩然内心的坚守折射出的矛盾性表现出的独特性何在?这将成为我们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第四节 浩然"变"与"不变"的启示 (1)
历经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浩然在创作上顺应时代而发生转变,但在这个"变"中,某些基本"不变"的因素使他在新时期文学中与众不同。正是这些"不变"使浩然小说呈现出有意味的复杂性。浩然的"变"或"不变",其交织的复杂性给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特殊的启示。
一、坚守集体化道路的反思
对农村集体化道路的热忱,似乎已成为浩然多年的信仰,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改革,作家始终坚持集体化理念,这里面既有对毛泽东农业集体化思想的认可,也有作家对农村深入观察后的体验。虽然在文学里,我们质疑集体化宣传带给农民生活改变的真实性,质疑这段历史的合理性,但时过境迁,经历"去政治化"、走过轰轰烈烈的经济开放后,当我们再次问询浩然创作时,浩然的这份坚守在当下的意义何在呢?
正因为历史是人的选择,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选择着自己的历史,整个历史是按照所有人的合力选择而成,所以每个人对历史的真诚追求都是有价值的,但他们的选择不能代表绝对的正确。历史,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选择。一个民族经历的历史,不能说绝对正确,但它是现实存在的,其他的选择也未必比现存的现实差,因为现实性不是合理性。历史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的。文学不是给现实提供解决办法的策划书,它只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思索的真诚之物。解读文学,要透过作品,从作者内心显示的力度和真诚度来感受。所以,我们在看待浩然坚守的毛泽东时代精神时,要有这样的客观性。倘若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讲这段历史,它有合理的必然性,解放之初,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合作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生产有明显起色。
与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集体合作化只是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任何一种历史道路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可以不断反复、甚至对抗,正如我们曾经质疑过的农村合作化生产方式在当今重新显现出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单个家庭无力与整个市场经济接轨,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合作化的经营方式才能带给农民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浩然在《苍生》中描绘的"红旗大队"繁荣昌盛的集体化生产、生活美景并不全是作家理想情怀的抒发,他对农村的思考是有真知灼见的。90年代,河北石家庄外50公里的周家庄集体经营模式就是一个证明。1983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独特地保留下原有的集体生产体制。虽更名为周家庄乡,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没有变,并成立了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乡农工商合作社。在全国普遍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时候,周家庄用实践证明集体经济的可行性,并在农村经济中显示出更胜于个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