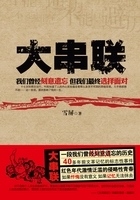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我刚送走他。权裔啊,我知道,关于这种事我已经对你说了很多,可能你也听得有些不太耐烦。我是第一次跟小刘见面,他就坐在你的位子上,他从头到尾都没多少语言,只是一个劲地抚摩椅子的扶手和玻板下你和砚彧的照片,他不抬头看我,我也不忍心看他。权裔啊,我劝你慎重考虑,刘新廷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诚恳、厚道,过日子就要找他这样的人。”
权裔很惆怅地说:“可跟他一起生活,我的心中很苦,很闷。”
“他知道你苦吗?”
“他要懂就好了!”
“那,你该懂他吧?”
“我当然懂,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强迫自己去冰冻、去尘封、去顺其自然!可是我——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忍耐,我不能再因为对他的同情而颓废了我的一生!”
“你认为你那同学就能使你的人生从此变得辉煌?”
“至少我们有共同语言!”
“什么语言?——夫唱妇随地做生意赚钱?我了解你权裔,你不是金钱的奴隶。”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该为谁努力!”权裔无奈地感叹一声,说,“你不会明白的,主任!这一时半会儿我又无法将我们六年的婚姻生活状况诠释于你,总之,我跟刘新廷……我太累了!我不想伤害他,但我已经跨出了这一步,可我又不忍心亲口对他说明这一切,我怕见他绝望的样子,怕见他明明不甘而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沉默,所以我逃避,我横不下心,拿不出勇气去面对他!”
主任深吸一口气,说:“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你说。”
“悬崖勒马,回家,过日子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人可靠,爱情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情绪,它绝不是你所认定的某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把它抓住。也许这段情感让你找到了某种久违的快乐,但这种快乐是不是就能平衡你过往婚姻在心中沉淀的责任?”主任沉默片刻,说,“我懂你,权裔,但很多事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有的人当你得到和占有的时候总觉得无所谓,一旦失去,你才知道他的可贵。我们虽然年龄悬殊,也存在观念的沟壑,但你必须承认我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都要比你多得多。有人说:婚姻就好比是一件瓷器,要做好它,很费事,很艰难,要打碎它,很简单,很容易,但要去收拾那些碎片,又是种让人头痛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用心分析分析这句话的含义,你呀,不傻,就是太执著,爱钻牛角尖。别怪刘新廷,你对他太重要,你也别嫌我多嘴,我是一直把你当我的女儿看待,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女儿半辈子活在悔恨之中。”
权裔眼中升起一层心酸的雨雾,女儿,是啊,自己曾经也是被父亲宠爱的宝贝女儿,父亲的话犹在耳边回响:“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爸爸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的。”
权裔双目含泪,酸楚地想:我不要天上的星星,我只要一个温馨的家,一个知我、懂我的爱人。你能懂我吗,父亲?你不就忘了我的存在!砚彧,你也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儿,妈妈让你失望了,但妈妈绝不会让你的童年像我一样,在企盼、等待、孤独和委屈中度过,请给我一些时间!
Chapter4
刘新廷痛苦地坐在写字台边,手中拿着一份“离婚协议”和一份“起诉书”,耳边回响着大姐的声音:“如果晚上她能回来,证明她对你还有几分尊重,你也别跟她多说什么,把离婚协议给她,看她怎么做;要是她不回来,证明你在她心中狗屁都不是,你也别再给她留什么情面,明天直接到法院把‘诉状’交了,我倒要看看她抛夫弃子的最后下场,其他的事你就不必操心,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老姐不会让你下半辈子打光棍……”
刘新廷望着手中之物,内心绝望地呻吟:“权裔,你也想我走这一步吗?你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明白?这小屋是你最喜欢待的地方,这墙上的每一张画、每一幅字,听砚彧说,都有一个故事,你为什么从没告诉我?还有这些书,这些笔,这些瓶瓶罐罐,你总是人在哪里首先就会把它们带去,记得我们从厂里周转房搬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少了一支笔,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你连夜把它找了回来才心安。权裔,难道我在你心里就不如一支笔?
“你对任何人都笑脸相待,而对我,你却像个严厉的法官。你跟儿子总有说不完的话,斗不完的嘴,而你却连看我一眼都不肯,我是多想你能像砚彧那样在我的怀里撒娇,扯我的胡茬,数我脸上的豆豆,可是,我就连你手上有几个‘钱’都不知道。
“我知道,妈对你有点啰唆,姐对你又有偏见,而我又不能伤她们的心,违背她们的命令。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你有什么传染病,也不介意你在外面做些什么,我只想你能天天回家,哪怕你当我是个仇人,只要看到你在,我心里就很踏实。”
新廷难过地吸吸鼻子,手抚摩着压着百首短诗的玻板,酸楚地想:“权裔,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走掉?姐说这些都是情诗,你们俩是同学,你这是为他写的,你一直都想着他!那个人真有那么好吗?让你忘不了,叫你不顾一切去跟他?权裔,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连狗屁都不如,那砚彧呢,你连儿子也要当包袱甩掉,你太狠心了,权裔。”
新廷悲痛地掉下了泪水,他痛定思痛地考虑:“不,我不会让你如意,你骗我六年,我要跟你耗下去,除非我死!”新廷恼怒地一把将两份材料使劲揉成一团,愤恨地甩手而起。
就在他愤起甩手之际,他不小心将案头的小花瓶碰到地上,然后就眼睁睁看着它破碎了,就像他此刻的心一样。他慌忙蹲下捡起那散乱的花枝和破碎的瓷片,他惶惶不安地看向母亲的房间,他怕吵醒砚彧。
正在他小心捧起这些碎片的时候,里屋传来了母亲的骂声:“你吃多了,半夜三更一个人在这里发疯?有种你去抓她回来,揍她一顿,枉自你是个男人,一个婆娘都管不住。你还好意思在这发闷气,没了她你会死啊!一个不守妇道的烂货,我早就怀疑她不是个好东西……”
砚彧也在叫骂声中睁开了双眼,并且敏锐地翻身下床,问:“奶奶,是不是妈妈回来了?”
奶奶狠狠地答:“你妈死了!”
“你乱说!”见奶奶欲打自己,砚彧嬉笑着慌忙躲开,冲奶奶做了个鬼脸,闪身跑到父亲身后,可怜兮兮地问,“爸爸,妈妈呢?”新廷不敢作答,忙将手中的瓷片放到隐蔽处。
砚彧趴在父亲肩上,探头朝前看,问:“你在做什么?”话未说完,见地上余留的花瓣,慌张地望了一眼案头,顿时惊异而又生气地说:“啊……爸爸?”
新廷有无所遁形之感,他拉着儿子的手,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爸爸不是故意的。”
砚彧一下就不依了,他甩开爸爸的手,哭着说:“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小花瓶是我送给妈妈唯一的礼物,我每天都要用它给妈妈插花,呜……妈妈,呜……”
新廷心酸地:“对不起宝贝,爸爸明天就去买一个同样的。”
砚彧边哭边说:“没有同样的,这个花瓶上妈妈刻了字。”
新廷强忍着心里的酸楚,把儿子抱在怀里,声音有些嘶哑地说:“对不起!”
砚彧更加伤心地双手抱住爸爸的脖子,满是泪水的小脸紧贴着爸爸的脸,抽抽噎噎地说:“爸爸,我要妈妈!”面对儿子的要求,新廷无言以对,他何尝不想要权裔回来,可是他无能为力。
花瓶事件就这样过去了,砚彧也没继续为难爸爸,新廷也就不了了之。这天砚彧黏着爸爸坐在他怀里,专心地看着电视节目。新廷心不在焉地对着电视,看看时间不早了,他催促砚彧,说:“快,去睡了。”
砚彧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不满地从父亲腿上下来,突然抬头望向墙头的石英钟,高兴地叫道:“啊哈,还有十五分钟。”笑嘻嘻地又转身回来。新廷严厉地瞪着他。
砚彧调皮地笑着,说:“做人要有原则,这是妈妈说的。”这时外面传来轻微的塑料袋摩擦的声音,砚彧忙机警地看向门脚,少时,见一个纸包被推送进门,他惊喜地大叫一声:“妈妈!”赤着脚丫就从沙发扶手翻下,一把拉开门锁,打开门追出,“妈妈!”
正想匆匆离开的权裔急忙回头,飞奔上台阶,双手接住飞扑来的砚彧,她心痛而难过地紧搂着他,说:“宝贝儿,你好吗?”
砚彧抱着妈妈的脖子欢喜地说:“妈妈,我好想你,你怎么老不回家。”
“放假了吗?”
“放了。”
“考试成绩怎么样?”
“双百分。”
“乖!”权裔疼爱地亲亲儿子。
新廷按捺着心中的喜悦,捡起地上的纸包,侧着脸伸手将门口的东西拿进屋,坐在沙发上打开纸包。刘妈看过来,见包中有两百元钱,顿时好奇地伸手过来,说:“这是什么东西?”
刘妈糊涂了:“她这又是玩的什么把戏?”新廷没回答,听到母子俩小声说笑着走上来,忙收回那纸包,神情变得紧张而严肃起来。
权裔抱着砚彧站在门口,顿时有些为难地停下了。砚彧催促地摇摇妈妈的肩膀,说:“走进去啊,妈妈。”
权裔稍作考虑,正要抬步进门,见刘妈面无表情地往房间走去。权裔望望沙发上不理不睬的新廷,尴尬地对儿子笑笑,说:“妈妈还是不进去了。”
砚彧撒娇地哼着:“嗯——”
“听话啊!”权裔将砚彧推进门。
砚彧突然要哭的样子拉着她不放,叫着:“妈妈!”
“乖!”权裔哽着喉咙,拿开儿子的手,摸摸儿子的脸,说,“砚彧最懂事,最听话,是不是?”砚彧眼中含着泪水,撅着嘴点了点头。
“妈妈不喜欢看到你这个样子!”砚彧勉强给了妈妈一个哭泣的笑脸。权裔再看眼儿子,心酸的泪水涌出眼帘,她竭力忍着抽噎,笑道,“再见,宝贝儿!”
砚彧苦笑:“再见,妈妈!”泪水滚落而出,权裔立刻将门带上。
“妈妈——”砚彧小声地望着门哭喊,一阵抽噎忙奔向阳台窗口。新廷悲伤地再度拿起那纸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