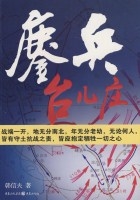弯身帮她拉好锦被,端起水盆起身出门。
“说,人呢?是谁准你们把人放走的?”蓝媚夜总会在离风凛冽的气势里即时冰冻三尺不止。
林爷上前一步,慈目镇定得不起一丝波澜:“大少爷,二少奶奶执意要走,我便没去留下,我看二少奶奶心中有许多东西还要她自己静静思考清楚。”
离风微眯着眼眸,定定的瞧他,薄唇抿成一道利线。
“需要静静思考?你是想告诉我在她受伤的时候需要静静的思考吗?一群废物。说,是谁让她受的伤?”
脚边一个椅子已经在他脚下发出一声破败的脆响。
“大少爷,现在是谁已经不重要了,还是看看二少奶奶是否已经回去离家大院吧。”林爷依旧一旁清声吐字。
“说!”离风额角青筋爆动,完全受够了林爷此刻的云淡风轻,儒雅之态。
“烈人。”
“哦?是她?去,把人给我叫来。”离风眼睛危险的眯着。
林爷深知离风的性情,平日相比而言表面上看着较为冰冷平静,不如离景和离然那么容易燥动噬血,但真若发起脾气,也绝对不容小窥。在离风冷然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和离家另两兄弟一样的岩溶心性,同样的威力逼人。
“去,把烈人带来。”林爷浅声吩咐。
倾刻,身着绿缎旗袍的烈人从门口进来,望向离风的视线微微颤抖不安。就连刚刚推过林妙言的那只手,心态使然下,也颤巍巍地泛起疼意。
“大少爷,我……”
“啪!”
烈人卑微的辩解不待出口,就被离风凌厉的一掌当场劈断。
偏向一边的俏脸火红妖娆,长发随着摇摆的力道乱作一团,纠结嘴角的血迹一并颓然尽现。
烈人头耳轰鸣,灼热漫过半边脸颊,身体微微一阵摇晃,惊恐得再动弹不得。略一垂眸,能看到离风掐住她脖颈的大手,虎口因为长期握枪生起的老茧摩擦着她的下巴,冷硬生疼。
离风惊悚慑人的话语,不掺一丝人性气息再次盘旋过烈人仍旧嗡嗡作响的耳畔。
“你当真好大的胆子,我看你是不怕死了,竟然敢动她,既然不怕死,不防等着看,看看离然怎么扒你的皮。”手上力道骤然一松,没了支撑的烈人身子下意识瘫软无力,潆然滑到地板上。
“走。”
随着离风一声令下,充盈整个房间的低冷气流届时散去,仿佛就连空气都暖了几分。
烈人微微缓和的胸口仍旧杂乱无章地起伏着,惊悸不安的泪水终于夺回一点勇气突破眼眶,肆无忌惮地纵横着。
林爷叹了口气,看也不看她一眼。
“在富家少爷里周旋,就该懂得收敛和隐藏妒意,否则,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次过后就该长教训。”
林爷一撩袍摆,起身出门。
房间内刹时只剩烈人一人,半伏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像一座没有灵魂的雕塑,空灵无边的灰瞳里蓄意凶猛的清泪又连连砸落到地板上,蜿蜒成一条绝望的死海。
离然看完手中的一沓资料,惊讶抬头。
“这就是林阿海的娘托妙言带回来的东西?”
离景眸光一沉,眼中不悦如堕烟海,接着凉凉提点:“她是你二嫂,直呼名讳怕是不妥吧。”
离然嘴角刻着一抹钩子,扬了扬手中的纸张,决定岔开话题:“看来你当初猜测得果然没错,赵景松满门遇害正正是段进民所为,只不过他将这笔帐画到我们离家头上又有什么好处呢?”
离景闲适地倚靠在墙上,轻轻眯着眼,眼神很是慵懒。
“这个段爷还是个情种,据我调查,当年段倾城的母亲是一个叫若莲的女人,和赵景松实则青梅竹马,嫁给段进民后与赵景松旧情难忘,怀了孩子。被段进民发现后枪决了。但段赵两家的梁子算结下了。段进民之所以派阿海当眼线无谓就是找机会致赵景松于死地。后来碾转到我们离家这里,段进民就想借着我们离家对赵景松仇恨的东风,解当年恨意。那时他毒品交易肆意猖獗,张警司炯目盯着不放,他整这么一出也是为了帮张警司认识到我们离家在上海滩的邪恶地位,转移监察视角。而且,赵家大家大业,怎会没有活口?他更怕事后罗乱。”
离然脸上笑意如花似锦,扔下手中的纸张,接着哧哧地笑起来。
“难怪这个张警司整日像狗一样的死盯着我们离家不放,看来是被段进民愚弄蛊惑了。”晶亮瞳孔一收,煞有介事道:“如果我没猜错,赵家遗留的罗乱也被你查觉捕获了吧?”
离景翩然一笑,眸中闪着水钻一样优雅的光。“你不觉得那个凭空出现在蓝媚夜总会,一夜红极上海滩的蓝媚十分蹊跷吗?当年我带人赶到赵家时,赵家老少已经全数遇难,而我特意留意过每一个人,其中那个多年留洋未曾谋面的赵小姐竟然身列其中,我看过她的手掌,纹络粗糙,是个故意穿了小姐衣服的下人。蓝媚倒十分符合这等角色呢。”
这一点颇让离然震惊,虽然明知离景沾染的女人一定事有蹊跷,却没想到竟还是这样一层玄机。
“这个蓝媚好像是英租界的人啊?对了,英租界与离家合作那事你怎么看?”
离景利落起身,满不在乎道:“这个事丢给离风,他才是打理离家生意的正角,英国人和他玩商场战术,还不是自讨苦吃。至于蓝媚,先放着,能救她于迷雾就救,不能就稳着,实在不行就只能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