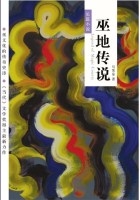响彻云霄的雷鸣掌声和极尖锐轻浮的口哨声响划过光色迷离的厅堂,现下舞台上的歌女一看便是风倾夜总会的顶粱柱级别的一线人物,当初她和烈人也曾激起这样的狂潮。
台上人一曲唱毕,摇曳着身姿下来,林妙言脚上略僵的步伐也开始缓缓向台上移动。
歌曲选定的是胡杨林的那首《是我在做多情种》,伴奏亦如往昔,草草演练,甚至比以前还要匆忙,所以心脏难免七上八下的跳作。
后台通往舞台上的短暂路途上暗暗祈祷,放手一搏了,一切只在今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身着银色洋服的女子往台上一立,台下刚刚还浩瀚如烟海的爆动,瞬息如遇冰点,骤然冷凝,台上人除了气质和脸孔还有点看头外,却是一个见也未曾见过的新人,显然激不起多少激荡的涟漪。
用现代的话来说,没被这种氛围调教过的新人,大抵都是菜鸟,眼见台上人就没有前边几位歌女的狐臊气息和媚骨柔情。
林妙言在台上众多纨绔子弟的冷眼相看中清浅一笑,那笑如风里沾了几分魅骨,飘荡过全场后令所有人方才还冷滞的骨子一阵酥麻,个个如狼的绿眼中微波轻轻荡漾,这个女人并非想象的那么无用,看来还有几分能耐。
音乐在台上人的如波眼神里缓缓流出,是首风格曲调都闻所未闻的古怪歌曲,撞击耳膜了又并不觉得唐突,声丝轻盈,又缓质哀伤。
台下刚略起的燥动又瞬间平息。
台上女子薄唇轻启,执了薄荷清凉意境,声音像歌中所呤,如花,似梦,消散进烟雨中。情感却缠绵着嵌进台下人潮里。
整个夜总会静寂,再静寂,只有心中被台上人掀起的狂热。
林妙言面上的笑意更甚,这就是她想要的结果,初步计划已经奏效,如果那个方庆生真如传言所说色到灭绝,那么南京一夜之间骤然升起一颗冉星,他怎么可能不心动。
台上人一曲唱毕,台下略缓几许,一波又一波充斥耳膜的掌声欢叫声久久挥之不去,毕方想起她就是风倾夜总会广告牌上推举的新人,如花。
人如其名,巧笑如花。
林妙言双手在空气中按压,示意狂燥的人群安静片刻,接着声线再启:“大家可能知道了,我叫如花,我在风倾不为别的,只为寻求良人,所以有意成为如花的良人的,请主动去报个名讳,不过如果不是如花所认准的,日后这种形式继续,来日方长。”也省着一些猴急的登徒子一时猴急,像蓝媚夜总会那会儿,企图霸王硬上弓,来日方长,今天不行就明天,反正方庆生出现也就这两天的事,不待底下人暴露邪恶的本性,姑奶奶也就名花有主了。
不理会台下嗷嗷似野兽的嘶鸣,转身下台。
贴近前台的包间里,隐在暗影下的一双锐目,穿过焦灼翻滚的气流冰眸灿若妖娆水晶,紧紧将台上女子锁在深邃的眸光里,猎取一般。
后台,林妙言皱着眉头看过名单上的所有名字,烦燥的丢向一边,小路安置的人马没有来报说方庆生已经踏足南京,就说明目标真的还未出现,所以看不看皆是枉然。
风倾老板闲适的踱进来,一脸笑意:“如花小姐看来真如老朽所想,明日必会红极整个南京。”瞄了一眼被林妙言丢在一旁的名单,笑意加深:“这么多豪门权贵没有一个被如花小姐看在眼里,看来如花小姐的要求很高啊。”
林妙言回以一笑,对他的赞赏不置可否,上海滩都能一夜走红了,如今道行见长,品级增高,还能突破不了南京城不成。
“择选良人并不完全讲金钱多少,可能还有感觉,只一晚,我想再观望一下。老板,没事我就先走了。”
男子点了点头:“好,你先回去吧。”
上海滩边境小城。
一间与边境富足程度极不相符的豪华厅室内,俊美绝伦的媚态男子听到线人的报告陡然从沙发上立起身来,声音亦不自知地高了三倍。
“什么?那个小女人跑到南京去了?还以自已为诱饵在很多男人面前登台演出?”离然胸中嫉妒的火焰顿时奋力焚烧,荒唐,实在是荒唐,那个小女人怎么又让所有如狼似虎的臭男人见识她迷人的风范,这分明就是羊如虎口吗。
“三少爷,我们坚决反对来着,可是二少奶奶不听劝。”线人表现得十分为难。
离然瞳孔一收,身上凛气迸发。
“把她给我照看好了,要是出一点差子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统统提命来见。这边事情一但处理完,我会在明天演出前赶去南京。”
近日发现有个别逃窜的日本线人,所以阻隔上海零散的日本线人回去报信的任务也非常繁琐艰巨,在确定离景生死之前,这边被死死压制掩盖的段家惨案坚决不能传到南京日本人的据点里去。
“是,三少爷,您放心吧,我们会全力保二少奶奶周全。”
离然摆了摆手,线人匆匆退下。
男子高大的身躯坐回沙发里,思绪又开始漫无边际的游移,那个女人倒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他们极力的保全喝护下懂得安份,非要将他的心脏折磨僵死才肯罢休。
翌日,南京城内,日风和绚。
隐在清暖光色下的巨网线络的一根被拔动挑起,一刹间传染一样,迅速抖动全城的整张脉络,传输得颇为忌惮。
小路一路狂奔,敲响二少奶奶的房门,。
林妙言躺在床上小瞌,一听到房外响动,陡然跳起身来。